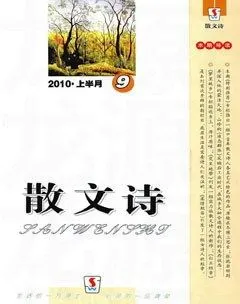蒙洼大地上
樹的濤聲
一棵樹上隱藏大海,每一片葉子都是一朵浪花。洶涌聲擊打黑夜。我斷定這脆弱的村莊要遭遇聲音和沖擊的挾持。
就像我年邁的母親身體里暗藏悲傷和喜悅。白發。腰酸。眼疾。微笑。這暴露在身體之外的芽。這擊打母親一生的浪花。
一棵大樹上的海的流向朝哪?遭遇一次沖擊力是不是就像生命遭遇一次重創?
一棵大樹上停留著海的碼頭,停留著落日,停留著撈沙船。
大樹的紋理多像海的命運。蕩開在大地上的波紋。深入地下的信號。
一整夜,我傾聽:
一整夜,我流淚。
一棵樹上的阿炳和貝多芬。
蒙洼大地上
這被洪水反復蹂躪的土地重新長出麥苗和高梁,像遍布的希望;這跳躍在岸邊的篝火,像這片土地持久的信念和夢想:成群結隊的河鳥成為蒙洼土地的仰望;辛勞躬耕的父母把腰拉成一張張弓,脊背上燃燒著太陽,血管里流淌著堅韌和倔強;親人的墳冢,一座一座,像河流留下的堅定的腳印。蒙洼大地上,露水是農諺的方向。天空是牛羊的故鄉。
洪水沖擊過的蒙洼大地,現在收割安靜和滄桑。這片土地種下痛苦、抗衡、命運和悲壯。種下棉花、槐樹、傳說、豆莢、風情、回憶和夢想。
蒙洼大地上,春風吹綠土壤,雙手勞作的人,我祝愿他一生安康。一百畝田地,疆域遼闊,五谷豐登;一千里淮河,浩瀚博大,源遠流長。
蒙洼大地上,一千棵樹彈奏琴弦,一千只螞蟻建造宮殿,一千株小草點亮燈盞,一千條支流連著春天的血脈和神經。
蒙洼大地上,一千株水稻是一千個勇敢的水兵,一千粒泥土里住著一千個神。
頂禮膜拜的土地,血管里奔涌的土地,月光劃傷的土地,埋葬愚昧的土地,一千年保持的腔調和本色接近燃燒的巖漿或火……
朝著河流的方向
我順著一條河流往前探尋,像一朵堅持朝春天盛開的野花。途經一百個村莊。我的小腳印是更小的河流。
遇上飛鳥。我展開翅膀;遇上蜜蜂,我獻出我肌膚的柔和軟;遇上大雪,我和棉花結親;遇上強盜,像遭遇黑夜,四處碰壁,我頭破血流,像一棵瘋狂開花的樹。
沿途我看見年輕的姑娘,是我從前的母親,她和我互不相識。我有幸看見她瀑布的烏發和矮小的身影。田地的麥子,是農業的火焰,炙烤著鋤頭和一個男勞力的前半生。一棵老柳在向上攀登,它渴望接近云朵和炊煙。沿途我看見那低頭只顧走路的螞蟻,像我逝去的弟弟,他的黑兮兮的脊背上馱著露水和天真。沿途我看見一只老鵝像一只喇叭花,尖銳的叫聲刺疼春天。
我就著星光上路,其實我避不開黑暗。我只是祈求更早地看見光。像一條河更早地看見它的流動。村莊在往后倒退。就像青草快要退回到種子。河流里的魚我敬拜,它們是神留下的光。
我看見的墳冢,有一些是我的親人的,還有一些是我的仇人的。墳頭上盛開著紫色的小野花,像一個個小孩在打著小燈籠。風一吹,快要熄滅。現在,我的胸懷坦蕩了。接納了親人的誤解和仇人的刀子。墳冢的安然和沉默像是一種低調的和解。我的鞠躬是卑微的,卻是高尚的。我的敬拜是嚴肅的,卻是可親的。
我一直往前走,有時也回過頭看看。看看過去的俗事蒙上灰塵。看看另外的自己,也在邁著前進的步子,和我一樣朝著前方走。
我堅信的前方其實很遠,它甚至超出了一條河流的長度。路上,河流告訴我:它的前頭就是大海。
但愿大海不是小河的幻想。但愿凋謝不是盛開的噩夢。
淮河岸邊
我大聲說話,我的聲音漫過土崗上的野花和荒草,最終回歸到淮河的聲音里。
在土崗上自由自在地行走,我不擔心春天或別的什么突然踩到我的腳跟。我一直走,或者漫無目的。最后我在羊群或星群里躺下休憩。沒有什么能跪下阻攔我。莊稼向高處。淮河朝前。我奔向遙遠的天堂。
我不會帶上風,它只會讓我輕飄。我會拔掉村莊的根帶上它。這是我的命。沒有什么比我的根更讓我感到牢靠和踏實。
我還會把盛開帶上,比如一棵桃樹和一棵梨樹,在我的光芒逐漸黯淡的時候,它們給我打起春天的燈盞。我會摸著桃花和梨花的光芒繼續我生活的道路。
在路上,我會放棄虛名和功利,我會愛上貧瘠的荒涼和樸素的姑娘,我會借助萬千露珠的心跳來告訴大地我有多么愛她。我借閃電的琴弦來訴說衷腸哀怨。沉悶的雷聲告訴我,蒼天也有它粗暴的一面。我要匯聚到淮河里去。
順流而下,我就會變成石頭。
逆水而上,我就會幻化成魚。
淮河岸邊。我敲響靈魂的鑼鼓。油菜花敲響芬芳。天空敲響鷹叫。
淮河向黎明劃去,我看見古樸笨拙的木船把太陽拉出,岸邊,濺起生命的脆響。
敘述母親
沒有做過一次生日的母親,我用什么來補償你?你的白發已經為你點亮生日蠟燭。我和時光一起吹。
用你曾經翻犁過數遍的泥土為你唱支生日歌吧。一個音符是一株莊稼。一株莊稼是你的一個好兒女。
你手掌上永遠愈合不上的裂口多像故鄉那些痛苦的河流,流向泛綠的農業和沉重的生活。你的腿疾就像這消散不盡的夜色。黯淡著腿的幸福。你的腰彎得比弓更像弓。你瘦小的影子有可能隨時會被風吹走。
你的聲音在削弱,你的衣物在逐漸樸素,回到粗布,你的個子在矮小,像蹲下的一口井。你的善良在不斷擴大。你的感恩變得熱烈。你吃苦的耐性更加隨意。你的記性越來越糟糕。你的視力讓你看不清錢的大小。你的腳步邁得緩慢。你爬樓很吃力。你照顧孫子很細心。你賣破爛掙分毫。你從老家回來堅持步行,不坐兩塊錢的三輪。你說城里菜貴,在自個家里建園子,把韭菜和辣椒背三十里地。
我的母親她姓苦,一生不曾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