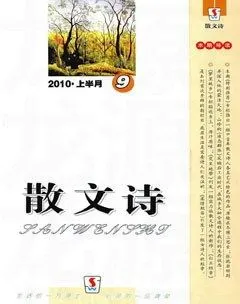張力
2010-12-31 00:00:00龍彼德
散文詩
2010年9期
新批評派理論家阿倫-泰特在《詩的張力》一文中指出:“詩的意義,全在于詩的張力;詩的張力。就是我們在詩中所能找到一切外延力和內(nèi)涵力的完整有機體。”詩是這樣,散文詩也是這樣。菲華詩人云鶴的《墻》,就是一首運用張力十分成功的作品。
出現(xiàn)在這首散文詩中的墻并沒有什么特別之處,百次、千’兜地從墻邊走過的詩人也沒有什么特別的感覺。但在夕陽西下之時,因為對街教堂圓頂尤其是圓頂上的十字架的投影,就發(fā)生了革命性的變化,墻頓時特別甚至神圣起來。“僅這一次。僅僅這一次。”他完全被突然出現(xiàn)的光學(xué)現(xiàn)象怔住了,因為十字架的投影在墻上升高,他舉起雙手的投影怎么也夠不著,即使“躍高得不能再高”,他的投影仍被教堂圓頂?shù)耐队把蜎]掉,“冥冥中忽地傳來”一個聲音:“你是連影子也值不得上十字架!”這就從感性上升到了知性:蕓蕓眾生要達到耶穌的境界是何等的艱難!在這里,感性與知性構(gòu)成了一對矛盾,由情而思而靈性,以求得感知的統(tǒng)一,是作品張力的表現(xiàn),也是作者精神的追求。
張zBAuAbicOnoAHLBaLsvmQQ==力還體現(xiàn)在結(jié)構(gòu)上。墻與人都是實的,十字架影、教堂圓頂影與人影皆是虛的,虛實相生,張力成焉。十字架在升高,人舉雙手欲攀十字架而不可得,墻是靜的,人是動的,物影與人影也是動的,動靜相間,也顯示出張力。動感在加強,以至于由“躍”而“跪”(伴隨著一種敬畏),這戲劇性的沖突更是張力的表現(xiàn)形式。
第三,還有語言。“他怔住。墻怔住。”“他擦身走過墻。……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