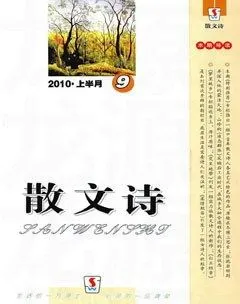從“傷口”中流出的詩
2010-12-31 00:00:00耿林莽
散文詩
2010年9期
一些嶄新的名字登上了寂寞的散文詩壇,他們是散文詩后繼有人的希望之所在。這其中,馬東旭的作品最為醒目地吸引了我。80后,來自河南農村,尚在打工行列中掙扎的詩人,這樣介紹他自己的詩:“讓時間慢下來,寫自己的文字,慰藉忽明忽暗的傷口,讓悲慟一闊一闋地流淌。”這使我感到一種由衷的親切,這是真正來自底層的散文詩,一開始便找到了“為世界喊疼”的出發點,而不是流連于陳舊的因襲和一己悲歡反復吟唱的窠臼。在當夸的散文詩壇,這樣的詩人與作品為數不多,因而更為可貴。
汶川地震已過去兩年了,浩如煙海的詩之祭奠也漸被人忘卻,馬東旭的《祭念泣川》卻讓我仍感親切,這是由于他超越了就事論事的淺層次抒寫,投入了個性化的詩性情懷,便有了藝術的生命力。“取出銀光,和干凈的鈣;取出我囤積一年的淚水,再次流淌。”然后,“我以一支濕潤的筆率領眾文字護送,以骨頭里的十萬個血粒子”。可以說不同凡響。“化為蓮,當您們的座騎”就尤為耀目。詩就是詩,沒有出奇制勝的語言意象,便易淪為平淡。
馬東旭的詩感覺,他的陌生化的語言既簡潔又新奇,而且句式精短,跳躍性強。他很少以沉滯的筆墨,拘泥于一般化的鋪陳性陳述,而是抓住一個細節、一個警句,點擊式地一閃,便轉移方向,跳入了新的句段。這形成了他的語言及抒寫風格的特色,恰是最適合散文詩這一文體要求的。建議他牢牢堅守這一優勢,并加以發展。
《水,或者水》寫得最為灑脫自由,通過水而跨越水,讓親情、鄉情與對于悲劇人間的思考情懷,表達得深刻而又精湛。……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