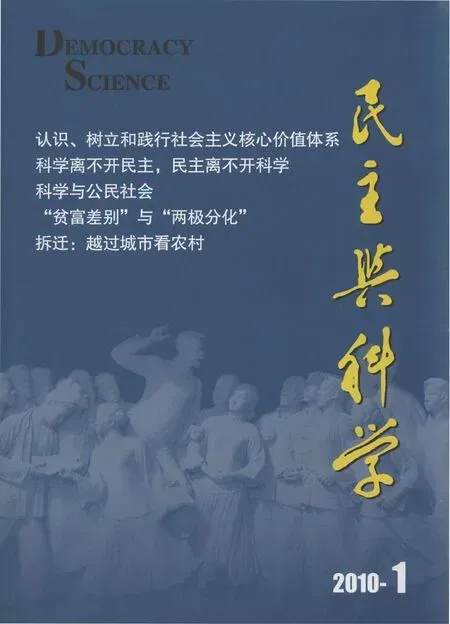拆遷:越過城市看農村
■沈 巋
編者按:2009年12月,北京大學五位學者聯名上書,提出對《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進行審查,引起社會各界的廣泛討論,也推動了新條例的出臺。本刊記者近日采訪了五位學者之一沈巋教授,他對拆遷背后的制度困境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另外,在此前的新條例的意見征求過程中,一位負責拆遷的地方官員對新條例草案提出了尖銳批評,其意見比較有代表性,本刊將他寫給沈巋教授的信以及沈巋教授給他的回信一并刊發,以期對讀者了解不同意見有所裨益。
拆遷:越過城市看農村
■沈 巋
2009年12月7號,我們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對《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以下簡稱《拆遷條例》)的審查建議之后,12月16號,國務院法制辦召開了一個座談會,明確告訴我們:早在2007年《城市房地產管理法》修訂的時候,就已經認識到《拆遷條例》一定要修改。其實,這兩年,國務院法制辦也一直在做這個工作,也召開過兩次專家座談會,不停地征求意見。但是,因為有些問題還沒有考慮成熟,所以,修訂的條例沒能很快出臺。這是12月16號國務院法制辦召開座談會時給我們透露的信息。到12月30號,全國人大法工委又召開了一個專家座談會。人大法工委提到,從2007年開始,全國人大法工委和國務院法制辦始終在推動這個條例的修改,但是面臨很多的問題。自從收到我們的審查建議之后,他們就加快了修改的步伐。2010年1月20號,國務院法制辦再次召集專家座談,把經過修改的《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草案)》拿出來,讓我們討論,并且表示,如果沒有太多問題,在聽取我們意見以后略作修改,就將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了。1月29號,新條例的征求意見稿終于在千呼萬喚之下出來了。
在這段時間,也得到來自社會的反應,包括大量媒體的采訪和討論,以及一些公眾尤其是被拆遷戶的來信和電話。我現在已經收到300多封信件,這些信件可以分成四類。一類是直接表示支持的,這些不一定都是被拆遷戶,例如,有一個95歲的老經濟學家朱紹文先生,他是經濟學家樊綱的老師,就給我們寫了一封信,特別支持我們的工作。第二類是建議類的,其中有法院的法官,也有被拆遷戶,或者普通民眾。他們提出一些建議,認為在未來的征收補償的制度設計中,應該考慮哪些問題。第三類是求助的,這樣的信件占了大多數。大部分求助信件是以特快專遞的方式郵寄來的,他們往往是結合自己的個案,提出希望我們給予幫助的一些請求。看到這些信件,我可以說是比較沮喪的。因為,這些信件確實反映了很多黑暗面,而且作為我個人來說,既不可能一一回信,更不可能像他們所希望的那樣,轉交給國務院和全國人大。我們的書面建議,也只是通過《立法法》規定的一種正常的公民建議渠道進行的。第四類信件帶有一種商榷性質,當然有些商榷是因為他們確實不了解我們,或者準確說沒有了解我們的思路。比如說,我們提出政府應該作為拆遷、補償的主體,一些商榷的信件就質疑道:如果開發商作為拆遷、補償的主體,我們還可以和開發商處于平等的民事主體這樣的關系當中,即便如此,政府還幫助開發商去強制拆遷,那要是由政府作為拆遷主體,把政府推到前臺來,老百姓不是更無助了么?其實他們理解錯了。我們的思路是在公共利益前提下,當然是政府征收和拆遷,而且,公共利益這個前提如果能夠得到保證的話,政府征收、補償這些程序能夠再設計得更好一些,應該不會出現他們所擔心的問題。而至于純粹的商業利益的開發,應該是開發商和房屋所有人面對面地進行談判,如果談判不成,開發項目就不能實施。這是我們基本的想法。在這些問題上,他們并不特別準確地了解我們的思路和設計,所以他們會有一些誤解,提出一些商榷。還有一些商榷意見認為我們沒有切中要害。比如說,一個地方政府的官員曾給我發過一條短信,認為我們提出的審查建議,主要的還是考慮征收補償的程序問題,沒有切中問題要害。他認為引起矛盾沖突的主要原因是補償標準問題,所以,怎么制定一個合理的補償標準才是最重要的。他的商榷意見確實有一些道理,我也是非常重視的。在1月29號國務院法制辦公開新條例征求意見以后,他又給我寫了一封長信,我也在回信中同他進行了深入的討論。社會的反響主要就是這四類信件。
這是我們建議之后,來自官方的回應和社會的反響。通過這段時間的討論和思考,期間,還去了一趟杭州,參加了關于杭州市拆遷安置房建設的會議。現在,盡管新條例征求意見稿已經公開,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的基本制度、基本框架,已經初露端倪,并且和憲法、物權法是一致的。但是,還有這么幾個重要問題值得關注與探討。
第一個問題就是公共利益和商業利益的區分問題。憲法和物權法都規定得非常明確,國家只有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才能依照法律的規定對公民私有財產實行征收并且給予補償。但是,地方政府和官員現在面臨一個比較大的任務,就是城市化;而城市化的發展,就必然涉及大量的征收、拆遷,包括把大量農民轉變為城市居民。這些目標都是量化的,比如說在多少年之內,多少農村居民要轉變為城市居民、城市應該達到多大的規模、應該實施多大面積的舊城改造等等。這些量化指標不是特別精確,但是大致上有這么一個規劃。我國目前就是想通過城市化的發展,來解決城鄉二元化的矛盾。這樣的發展思路勢必就會給地方官員帶來一種任務,就是如何規劃城市的發展,整體上怎么樣合理布局、怎么樣合理發展。而每一次規劃,實際上就有可能意味著土地使用權的性質和功能發生變化,這種變化又往往意味著政府要征收了。因此,只要涉及城市化的發展,就肯定會帶來大量的征收和拆遷。所以,2010年1月10號在杭州的拆遷安置房建設會議上,一位官員告訴我,他們現在堅持兩點:第一,城市化的發展一定要進行大量的拆遷,拆是必須的,不拆是不行的;第二,拆遷一定要依法拆遷,一定要通過公正、公開的民主程序來進行。這樣的表態我覺得有他的道理,但是,問題在于,城市化的發展本身能不能作為一種公共利益?看上去,城市化的發展可能會改變城鄉二元格局狀況,或者說,在城市的發展過程中,更多的人,不管是村民也好城市居民也好,會享受到城市化發展的成果。從這個角度上來講,好像帶有公共利益的成分。然而,如果城市化發展本身可以作為一種公共利益的話,那么就不存在公共利益和商業利益的區分了,這種區分也就沒什么意義了。因為,幾乎所有的商業利益開發都可以被說成是城市化發展的需要。
新的征收與補償條例涉及的公共利益和商業利益的區分問題,與我國目前解決城鄉二元格局的城市化發展思路有關,涉及到國家的宏觀政策。所以,即便新條例征求意見稿明確區分公共利益和非公共利益的需要,在征求意見過程中,已經有些來自地方政府和開發商的意見在強調商業開發在城市發展、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及其“公益性”。
第二個問題,這次拆遷條例修改并不涉及農村,而大量的拆遷矛盾糾紛又發生在農村集體所有的土地上。這是我們感覺十分遺憾的地方,但又是必須要面對的問題。拆遷條例的修改,新條例的制定,涉及的問題仍然僅僅是國有土地上房屋的征收,并不覆蓋農村集體所有制土地及土地上房屋的征收和拆遷。我們提出的審查建議,針對的對象也只是《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這樣的話,我就擔心,我們的呼吁、法制辦和法工委透露出來的修改信息以及新條例征求意見稿,可能給一些不太明了其中關系的公眾一種很高的期待。而一旦新條例正式出臺以后,大部分在農村土地上的拆遷糾紛矛盾,沒有辦法通過這個新條例來解決,公眾的期待很快就會落空。而期待越高,失望就會越大。這是從政治層面上和政府層面上必須要應對的問題,也是我所擔心的。
針對第二個問題,我想再說說第三個問題,即農村集體所有制這種土地制度問題。這其實和第一個問題也是相關的。按照我們現在的土地管理法律規范,包括憲法里所涉及的相關條文,農村集體所有土地在實際運作中是不能上市交易的。也就是說,農村集體土地所有制下的土地只能轉化為國有土地之后,國有土地使用權才有一個招拍掛進行交易的過程。這顯然是不公平的。表面看來,村民享有土地,但實際上并不擁有真正意義上的財產權。因為財產只有交易,才能實現它的價值,如果不能交易,就體現不出它應有的價值來。現在的土地管理法是這么規定的,國家先對農村集體所有土地進行征收,然后對村民進行補償,補償標準是根據這塊土地上的產值計算的。我們知道,農村土地上的產值肯定是很低的,所以這個補償款也就很低了。但是,在變為國有土地之后,政府一轉手出讓,它的價格就成幾百倍地增長。這樣的話,村民心理上肯定會產生極大的不平衡。在現有的土地制度下,有些地方,例如杭州,給予村民的補償做的已經是比較好了,但拆遷戶的滿意率仍然很低。杭州的辦法就是在現有制度之下盡量采取一種“房等人”的辦法。所謂的“房等人”就是先建拆遷安置房,建完之后,被拆遷戶就搬到新房,被拆遷戶的原有房屋才被拆遷,再相應地進行其他建設改造,而且,他們采取就近安置或就地安置,這也比較符合人性關懷。畢竟,村民長期住在一個地方,對這個地方是有感情的。所以,杭州算是做得很好了,但是,從他們所給材料中仍然可以發現,拆遷戶對拆遷安置房的滿意率只有67%多一點。剛剛過了一個合格線,滿意率還不是很高。為什么?我們分析原因,仍然和土地制度有關系。也就是說,政府安排得再好,村民仍然無法接受,他還會認為,我這塊地,政府得了不少錢,開發商得了不少錢,而我得的比較少。當然,政府也有理由,說這塊地為什么能夠增值,開發商為什么能夠以比較高的價格賣出去,就是因為政府投入了,比如說,在周邊地區改善交通設施、開發其它相關項目,才使這塊地的價格增長。這種說法也有它的道理,但是,它無法解決村民所獲補償與政府土地出讓收入、與開發商土地利用開發利潤之間巨大反差的問題。
第四個問題,是城市化的發展和生活方式的選擇。我特別要強調兩點:第一,我們的土地制度,尤其是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一定要改革,要讓農民擁有真正的財產權,而不是象征意義上的所有權。第二,一定要區分公共利益和商業利益。為什么要堅持這兩點?這與城市化發展和生活方式選擇相關。確實,城市化發展了,有人覺得生活更好了,但我們要承認現代社會是一個多元化社會,階層是多元的,利益是多元的,價值取向也是多元的。你城市發展得再好,你高樓大廈建得再高,但我就愿意在一種節奏不是太快的生活方式里生活,不愿意住在鋼筋水泥的大樓里,也不愿意住在這樣一個小區:如果我記錯了自己家的門牌號,就很可能錯進別人的家門。這些都是一種價值取向。如果說不是公共利益,而是商業利益,開發商要買我的土地或房屋進行開發,我完全可以拒絕,因為這是我自己的土地房屋,我愿意按照我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在這里。
我們現在的城市化發展思路,還是一種家長式的思路和管理方法,就是我認為這種方式對你們是好的,你們是我的子女,我就按照這種方式來安排你們的生活。可是,畢竟我們所處的這個社會是一個更加多元化的社會,這種多元化的社會是建立在每個個體都應該擁有其自身權利的基礎之上。如果這些權利都沒有,那這個多元化就不存在,價值的多元化也不存在。所以,我的第四個問題就是:現在的城市化發展戰略仍然是一個傳統思路,盡管聽取了村民的意見,盡管吸收了一些公眾參與的元素,但是仍然是一種家長式治理。這種家長式治理,就等于在否定這種價值多元化,在否認生活方式的多元選擇。我在想,這樣一種城市化發展路徑的結果會是什么呢?到處都是差不多的高樓大廈,農村那種比較閑適的生活方式慢慢被侵蝕掉了。這符合科學發展觀嗎?符合社會和諧發展,特別是人與自然的和諧嗎?當然,近兩百年前,世界工業化浪潮沖擊閉關鎖國的清朝,我國被迫走上了工業化道路,小農經濟生活方式走上了被淘汰的宿命之路。但是,這種宿命并不代表著政府主導型的、高歌猛進的工業化、城市化就一定是對的。讓每個人自己去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這是這個時代最需強調的個體尊重。
第五個問題是在征地拆遷領域中出現的政府公司化傾向。之前,曾經聽說過經濟學家吳敬璉提到政府公司化問題。在這次杭州市的會議上,我切實發現政府在征收拆遷的過程中,存在政府公司化的傾向。政府公司化是什么概念呢?我在這里不做界定,只說一種現象。我們假定政府確實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征收土地或房屋,而且在補償方面還做得不錯,那么,這里面是誰在做這些事情呢?有可能,政府和開發商融資來建這個項目,政府對開發商說,你來投資建這個項目好了,政府給你一些優惠政策。用這樣的方式來吸引開發商投資,這是一個比較合理的融資方式,在國外也有。但是,現在有些政府成立各種各樣的中心,或者說掛靠在政府下面的一些公司。然后,這些中心、這些公司直接做拆遷事情、直接做拆遷安置房建設、直接做土地開發等等,這就是政府公司化的傾向。如果掛靠政府的這些中心、這些公司直接去承擔拆遷安置項目等,這意味著什么呢?這個項目也許是讓被拆遷戶住進來,帶有公共利益色彩,但中間有沒有一些中心、公司自己獲利的一面呢?不獲利他們怎么去做這種事情呢?按照制度經濟學的觀念,政府如果沒有一種獲利的可能性,它就不會承擔更多的事情,它為什么要去多攬事呢?那肯定是有一種獲利的可能性,有這樣一個獲利的預期。
第六個問題就是土地儲備。這個其實和我剛才談的土地制度也是有關聯的。現在有很多地方是以土地儲備名義來征收的,那么儲備起來的土地以后來干什么?怎么用這些儲備的土地可能是若干年以后的事情了。在以土地儲備為名來征收土地的時候,政府不會說這是為了公共利益,它會說土地儲備就是公共利益。但是,土地儲備之后,完全有可能賣給開發商,然后做商業開發。從我個人角度來說,在這次幾乎全身心投入拆遷條例修改的研究之前,我更多是從制度上或者說從文本上考慮相關問題,對于現實當中政府征收拆遷的許多環節,都欠缺真正實地的調研。現在,通過閱讀大量信件以及開會討論,我在這方面的認識豐富得多了,我發現幾乎每個環節都存在很多問題。例如,土地儲備中心把土地征收了,然后土地儲備中心再去招拍掛,招拍掛之后再交給開發商,然后政府就會考慮拆遷安置房的建設,然后又有所謂的拆遷安置房建設中心或者城中村改造辦公室等一批機構來承擔這些事情。就是說幾乎每個環節都是層層相扣的,利益鏈非常之大,非常復雜。這或許就是修改條例阻力大的原因了。這些所涉及的利益層和城鄉一體化、城市化發展思路結合起來,就會形成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迫使”你不能簡單地區分出公共利益和商業利益。甚至,包括我們的GDP增長都可能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所以,我總體上感覺我們現在發展的太快了,快得你無法去應接它快速帶來的問題。比如說,在快速發展過程當中,你看到這個問題,就想辦法去解決,但是在你提出解決方案的時候,可能會帶來另外的問題,這些問題又怎么辦?其實,給予城市被拆遷戶權利也好,或者給農村村民權利也好,或者說我們要強調公共利益和商業利益的區分也好,其實都在于一點:我們要適當放慢一點速度,這個速度太快了!
最后一個問題就是黑惡勢力與拆遷之間的關系。我所說黑惡勢力不是指黑社會,而是指用非常邪惡的手段來對付被拆遷戶,而且,這種手段有些地方政府在用,開發商也在用。政府官員把地批給開發商,開發商就要盡快去開發,每拖一天,他就會損失很多錢,所以他會盡可能讓政府官員出面給他撐腰,他還會雇傭很多社會閑散人員,每天去騷擾被拆遷戶。比如,打碎窗戶玻璃、用膠水堵鎖眼、晚上開著鏟車馬達轟鳴不讓你睡覺等等。這些都是給我寄來的信件里提到的,各種各樣,無所不用其極。我們可以想象一下,這些社會閑散人員還有法制觀念沒有?他沒有了,你政府都讓我這么做,或者說你政府撐腰的開發商都讓我這么做,我為什么還要去遵守什么法制啊?這些都是一些連帶的效應。有一封信件中提到,一塊土地被村長賣掉了,有村民不服,村長就帶著十幾個人晚上闖進村民的家,拿著棍子把家俱都砸了。這個村長還說,我和某某公安分局的局長關系很鐵,你們如果不拆,我就這么砸,看你們找誰啊,找公安局長?沒人理你們。不能說這些信件反映的百分之百都是真實的,但我相信百分之七八十都是真的。沒有人總是編故事,沒有多少人有精神妄想癥。
一個鞍山的人已經給我打了三四次電話了。第一次通話時,他說他好不容易才找到我的電話,好不容易才打通,很激動。他說他現在住在半棟樓里,另一半已經被拆掉了。每天挖土機、鏟土車都在施工,轟隆轟隆地響,他們根本沒辦法休息。他問我新條例什么時候出臺,我說樂觀一點在今年全國“兩會”之前出臺,他說他一定要堅持到那個時候。你看,在這個時候,他已經不相信地方政府和開發商了,有一種非常對立的情緒。黑惡勢力的存在,讓我非常非常擔心中國如果就這么下去的話,將來會怎么樣。
附:某地方官員與沈巋教授的來往信件。這位官員希望匿名發表。
沈老師:見信好!
我是一名基層的法律工作者,近日和全國廣大人民群眾一起關注“拆遷變法”,將心中的憂慮略表,可能不成系統,希望能對您參與立法過程有所“影響”。
首先表明態度,我是您所說的“反彈”的人之一。當然,不代表地方政府,而僅僅是因為我十多年來一直參與拆遷和本地拆遷政策的制訂。總的感覺 是國務院法制辦的草案太草率,法學家的意見不靠 譜(對不起,我不是針對您。相對而言,您是一個更為 理性的學者,比那些“民粹”味道十足的所謂學者更 值得尊敬,否則我不會長篇來信了)。
半小時前我還在一個拆遷現場轉,聽聽人們怎 么議論。我居然發現了一個離我上班的地方步行只有3分鐘的一個“城中村”,十年來我居然從來沒有去過。這個小村子兩三年后將是一個比較高檔的住宅小區。可今天我看到的是一片狼籍:十多戶人家在趁黑夜突擊加蓋房屋,目的是多獲得補償;村子里幾乎住的都是外來務工人員,很多房子被辟為小超市、開水房等等;人們三三兩兩的聚著,商量如何對付拆遷。我想,如果今天拆遷條例的草案就實行,那么這里的拆遷絕對不可能完成。村里的人們可能確實可以繼續獲得相當的租賃收入,然而他們自己還得繼續忍受臟亂差的生活環境。而鄰村的其他人已經住進了漂亮的安置房小區,大多開始獲得安置房的租賃收益,晚上還在小區打“太極拳”。
這里有一個悖論:新的拆遷條例可以保障他們(拆遷戶)的權利,然而他們失去的可能更多。為什么?法學理論中概念化的“權利”在現實生活中是多元的、多層次的。個體的權利也是多方面的,很多時候與集體的權利是矛盾的。奧爾森《集體行動的邏輯》有一個核心的觀點:每一個個體的理性選擇并不能必然導致集體的理性選擇。新拆遷條例尊重了個體的理性選擇權,但并非實現了集體的理性選擇。
拆遷有一個特點,如果有100戶人家,99戶簽署了協議,1戶沒有簽署,那么該土地無法實現交地。1戶人家足以綁架99戶人家的利益,所謂“堅持就是勝利”就是這個道理。正因為一些“精明”的人看到了這一點,所以他們提出的條件是政府無法滿足的。如果法學家沒有看到這一點,而是拘泥于法律概念,我只能感覺到遺憾。法律規則如果在經濟上沒有可行性,那么即使制定也是得不到良好遵守的,如2001年的舊條例(實際是1991年的)。
我從工作經驗來看,新條例比舊條例進步不了多少。說實話,我學的知識很雜亂,都是淺嘗輒止,不能從學理上來歸納。僅僅是不成熟、不成系統地談談我的看法,不知道能否表達我的認知。
1.新條例太注重個體的權利忽視集體的權利。中國幾千年來的一個基本矛盾,就是人地關系的矛盾。孫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義”,其中民生主義的核心是平均地權,城市土地增值歸公。新條例再加上物權法,基本上確定了土地增殖私有。中山先生提出土地增值歸公,是基于節制資本的考慮;現實中土地增殖的歸屬,政府與民間理解不同,政府在處理國有土地和集體土地時也不同。這一問題是拆遷條例首先要回答的問題。新條例所說的“市場價評估”原則,基本上確定了土地增殖私有的答案。實際上,土地增殖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公共財政的投入導致土地的級差地租上升,這部分級差地租的歸屬在法律上不明確。這是爭議的焦點。也許我在危言聳聽,按照我們法學家的思路去做,恐怕真的會引起一場舊的革命。換個角度看問題,得出的結論截然不同。
2.新條例是法治的進步、社會的退步。從法理上看,新條例很“美”:尊重權利、尊重公益、尊重司法等等。然而,新條例如果真的照此實施,我估計整個拆遷得停止。為什么?因為除了很明顯的公共設施建設外,政府很難通過行政程序來界定出“公共利益”。一個小區業主委員會都很難產生的地區,如何去產生90%的人同意“拆遷”的“公意”?即使這樣的“公意”能夠產生,政府哪里有錢去實現“公共利益”?要知道,商業地塊的拆遷比公共利益拆遷要難上幾十倍,而且政府不能獲得“土地財政”的收益。克林頓有一句經典的嘲笑老布什的話:“笨蛋,關鍵是經濟。”沒有財政收入的增長為基礎,一切建設免談。
3.新條例沒有看到我國土地制度的“特色”。我國的土地制度是全世界獨一無二的:城市市區土地屬國家所有,“城中村”的土地屬集體所有;國有土地上有土地使用權,集體土地上有承包經營權和宅基地使用權。這些權利到底該如何歸類,恐怕民法學者也傷神了多年。當然,法律上是好歸的,關鍵是我國區域發展的不平衡、相對貧富差距很大、沒有物業稅、傳統的置業觀念等等,這些條件的作用下,再精美的概念都不堪一擊。土地公有走不順暢,土地私有更走不通。深圳“良性違憲”搞了土地批租,才開始了房地產近20年的繁榮。如果沒有“良性違憲”,我們可能還都住在集體宿舍等著分房子呢!正因為民法上對土地權利不好界定,才有了物權法的爭議。新條例試圖提前彌補這些漏洞,不知道行政法學家能否強過民法學家,拭目以待。
當然,我絕不是舊條例的擁護者。舊條例如乞丐的衣服,已經不值得一提了。現在有很多人將拆遷中的消極現象歸為舊條例的功勞,并以此來提出廢止舊條例,可能是找錯了方向。因為所謂拆遷“釘子戶”(這里借用稱呼)的過激行為,并非因為他們太尊重法律想以死護法(憲法、物權法);相反,如果都尊重法院的判決,那么政府會傻到冒著掉帽子的危險來強拆嗎?
我特反感各種媒體和所謂學者對拆遷問題的煽情闡述。現在很多人把拆遷妖魔化,試問:沒有拆遷,有中國近十年快速的城鎮化嗎?有我們居住的現代化小區嗎?我處理過很多的拆遷難題,目前為止沒有發現拆遷過后導致生活困難的;相反,拆遷時與村干部罵娘甚至打架,拆遷過后依然還像朋友。拆遷過程中的各種表象,無非是利益的爭奪而已,與法學家的“權利”“自由”恐怕關系不大。
破了還得立。舊條例不行,新條例也不行,我的觀點是既然很難形成一致的觀點,不如先把能確定的東西確定下來:首先是定價機制要有公信力。當然這個問題要綜合法學、經濟學、政治學等理論來確定;其次爭議解決機制要有公信力,主要是行政裁決與司法強拆的效力;再次監督機制要有公信力。不患貧而患不均,公開拆遷補償的結果似乎比其他措施更容易做到,效果也更好。至于公共利益問題,我認為是無法界定的。政府賣地收入都用來基礎設施建設了,實際上也是土地增殖歸公的表現。即使是商業地塊開發,政府也應當是當仁不讓的征收主體,然后進行土地出讓。新條例將商業地塊開發摒棄在公共利益之外,是最大的敗筆。
一邊倒的民意是非常危險的。“位卑未敢忘憂國”,關系到大是大非的問題,我認為參與很有價值,也希望更多理性的學者實際考察拆遷過程,為條例的修改作出貢獻。
此致
敬禮
×××
×年×月×日
×××主任,你好:
來信收悉。的確,我十分驚訝于你所持的立場和諸多觀點,尤其是出自一位正宗法學科班出身、浸淫法學多年的基層法制工作的領導者身上。由于你的信件內容涉及許多問題,我不知道是否能夠一一地予以回應,勉力為之吧。
首先,無論是你提及的“城中村”問題,還是土地制度問題(包括土地公有抑或私有的問題)、土地財政問題,都未在新條例中觸及。新條例的制定,是國務院得到《城市房地產管理法》(2007年修正)的授權,針對城市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問題。新條例沒有權力覆蓋農村集體所有土地及土地上房屋的征收與補償。這不得不說是一個遺憾,需要未來立法予以解決。也許未來立法還是會采取與新條例基本一致的立場和思路去解決農村問題,但至少從目前來看,你所持的新條例試圖解決這些問題卻又沒解決好的觀點,似乎不應強加在新條例身上。
其次,關于少數人綁架多數人的問題。新條例草案把危舊房改造列為公共利益事項,已經引起許多普通公眾(請注意不是法學家也不是媒體)的反對。在他們看來,危房涉及公共安全,自屬公共利益無疑。可舊房并未觸及公共安全,舊房是否改造應該由房主自己說了算,而不應該由政府進行“家長式的干預”。這個觀點是極有力的。而且,由此觀點出發,有許多人認為90%以上的居民同意會造成多數人綁架少數人(10%)的問題。我真地很奇怪,你倒是反過來擔心少數人綁架多數人。
我個人在這個問題上的觀點是支持草案的。因為,我國處于特定歷史發展階段,有許多地方存在大量棚戶區和危舊房。由于什么是危房都難以獲得統一標準,舊房的標準就更加難以統一,所以,通過程序或許是唯一可以解決問題的渠道。讓90%以上居民同意(不要以為小區業主委員會很難成立,就不能完成征集居民是否同意的意見的工作),就是要讓盡可能多的人來判斷自己所在區位的房屋是否需要重新改造了。這種讓多數人決定的方式,難道不比政府一廂情愿地說你們這里臟亂差、你們這里需要改造了更具合法性嗎?我國政府習慣于做仁慈的家長,官員也費盡心思地要為民著想,但熬白了頭發、累壞了身體也討不到好,為什么?因為現在的中國公民已經不是那么愿意“被改善”了,而是更愿意自己來決定如何改善自己生活。這就需要政府更多地與民眾溝通。
在危舊房改造以外,就更不存在少數人綁架多數人的問題。舊條例不區分公共利益和商業利益,一切拆遷許可皆由政府發放。而70%~80%的拆遷又是商業利益的開發。所以,為什么拆遷工作如此艱難?為什么會有少數人堅持做釘子戶?也許會有許多原因。但是,假如換做是我祖傳的四合院房子要被拆遷,政府沒有說出什么公共利益需要,卻是要給某個開發商用這個院子所在的土地建一個新的寫字樓,我也會選擇做釘子戶的。你呢?政府在這個問題上還不好說什么,因為不是公共利益的需要,不能單方面行使主權,只能不斷地以補償來解決問題,以至于補償價格不斷攀升。新條例區分公共利益和商業利益以后,政府只能在公共利益需要的情況下才能去征收。這同時也給了政府“理直氣壯”的理由。假如建設項目確實符合公共利益,那么,除危舊房改造的項目以外,無論是多數人同意還是少數人同意,政府都可以單方面決定實施征收。
第三,關于個體理性、個體權利和集體理性、集體權利的問題。我也讀過奧爾森的《集體行動的邏輯》,那還是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了,現在多少有點淡忘了。但是,在我依稀的印象中,像奧爾森等制度經濟學家在談論“集體”這個概念時,更多地是指向“政府”的。因為,在西方政治、經濟理論中,個人(individual)往往指向個別的自然人,集體(collective)往往指向各種組織(包括政府組織)。《集體行動的邏輯》一書恰恰是要說明,正是集體行動的困境,使得政府決策經常失靈或不理性。
在人類歷史長河中,一個永遠無法得到完美解決的難題就是“民主”與“科學”的矛盾、就是“民眾”與“精英”的矛盾、就是柏拉圖的“哲學王”治理困境。就像我們生病了,更多地是去找醫生看,把身體的一切交由醫生說了算一樣。在很多時候,我們希望或者習慣于“被專家治理”。但是,專家本身也是有局限的,專家也是會被俘虜的。你閱讀《美國行政法的重構》以及其他文獻應該很清楚這一點。這就是為什么我們不能單純指望政府來描繪宏偉藍圖,為什么我們需要發表自己意見和利益訴求,為什么我們每個個體之間應該通過相互溝通來減少歧見、形成共識或妥協的原因。新條例草案對公共利益事項的界定,其實還是給地方政府留下了許多空間(盡管我本人對窮盡式的列舉不是十分贊成,對絕對排除以招商引資方式實現公共利益的作法持保留看法)。實際上,關鍵的不是在于列舉,而是在于如何通過公共議論把公共利益事項說清楚,形成盡可能多的人的共識。征收決策前的聽取意見程序和征收決策后的司法審查程序,其實都是要借此制造公共議論,把事關大家的公共利益問題討論充分。
第四,關于商業地塊開發的公益性問題以及對歷史發展的判斷問題。盡管政府土地財政收入用于什么地方,在目前尚不透明的政府體制之下,我們不得而知,但我愿意相信你所說的政府收入主要都用在基礎設施建設以及其他公共服務職能上了。可是,假定是在純粹商業利益開發的制度環境中,政府賣地得了100元,然后把100元平均攤在50個人身上(包括被征收房屋的我身上),每個人都得了2元;開發商拿到這塊地以后進行開發利用,刨去其付出的補償成本、土地出讓成本等,他拿了30元的利潤;我從開發商那里得到的補償也可能只是10元。那么,我也許愿意為其他49個人每人得到2元的財富分配犧牲一點我的個人利益,但我為什么要為那個開發商拿到30元利潤而犧牲我的個人利益呢?既然政府答應給我70年土地使用權,憑什么就可以在任何時候(包括商業利益的開發)都提前收回土地使用權,并且告訴我,“即便是商業利益開發也是公共利益需要,你就認了吧。”
歷史是復雜的。1949年以后至1982年,還沒有哪部法律一律將城市土地國有化、一律將農村土地集體化。1982年憲法改變了所有的情況,卻沒有給任何補償。最近三十年的發展,與拆遷的確密不可分,人們居住條件的改善以及城市的發展也的確離不開拆遷。然而,必須承認,我們即便大多數人都分享了發展的成果,還是有相當一部分少數人并不是那么公平地分割了發展成果的更大份額,而這又是相當一部分少數人并不是那么公平地被犧牲掉正當利益所致。
第五,關于釘子戶問題。自從我們提出審查建議以后,我已經收到了300余封來自全國各地的信件。這些信件的絕大多數,都是在講述一個個令人心酸的故事。這些故事的講述者或許有他們的角度、有他們的利益訴求、有他們的眼光局限,但是,我寧愿相信其中的絕大部分是真實的心聲和現實反映。我不知道你為什么會這樣看待釘子戶。我可以告訴你的是,如果這些信件所講的大部分故事發生在我身上,我也會選擇做一個釘子戶。
被拆遷人在面對拆遷時采取擴建、改建等方式,意圖增加補償數額。這個問題可以用別的方式加以解決。但不能以此作為看扁釘子戶的理由。其實,你所描述的“一村臟亂差、鄰村潔凈美”的境況,并不能作為政府不區分商業利益和公共利益的理由。鄰村潔凈美恰好可以促使臟亂差的城中村居民“自治地”去決定是否愿意接受商業開發商的條件,對本地的房屋進行改造。而且,政府還可以利用其它一些環境治理措施,讓城中村居民承擔臟亂差的成本,從而以經濟杠桿迫使他們盡快擺脫這種境況。
最后,我還要提及的是,我們都是作為人而存在的,既然是人,就是有弱點、有感情的,而不是純粹的計算動物。我們每個人都會變老并死去。在死去之前,安安靜靜地住在幾十年來習慣了的房子里面,也許是死亡來臨前多數老人的選擇。如何讓個體利益與公共利益實現平衡,是一個古今中外的難題,但新條例至少實現了向個體利益的傾斜,而又沒有完全放棄公共利益。這就是我之所以支持它的主要理由。
當然,你仍然可以堅持你的觀點。
順祝工作順利!
沈巋
×年×月×日
(本刊記者尚國敏采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