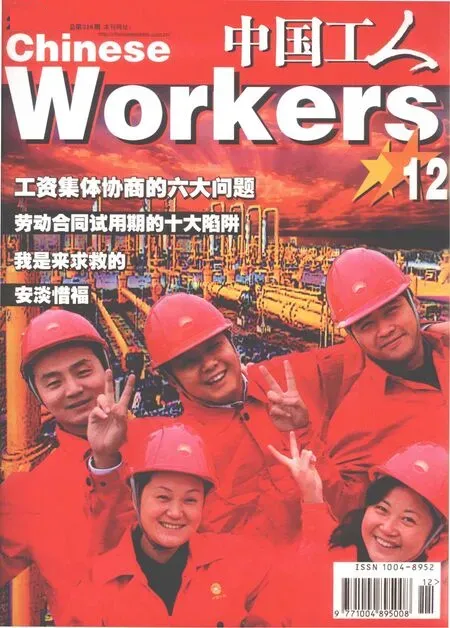工資條例:讓每一個勞動者都有“話語權”
任小平
工資條例:讓每一個勞動者都有“話語權”
任小平
最近,各類媒體都在關注《工資條例》,焦點聚在可能會將“工資協商”和“同工同酬”這兩個東西寫進去。
不可否認,這兩個東西都是目前在分配領域中最關鍵、最重要、最緊迫的問題。眾所周知的事情是,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的GDP蛋糕越來越大,2009年達到33萬億元,“蛋糕”的“膨脹速度”(增速)平均達到9.8%。這成為同期世界經濟的奇跡。但與奇跡相伴的問題就是,廣大民眾,特別是勞動者并未高興起來,反而出現了“生活越好、牢騷越多”的怪現象。
由此,我們要思考的問題就是,是人不知足,還是制度出了問題呢?如果是人不知足,另當別論,但如果是后者,那我們是否需要做點什么?尤其是作為制度供給者的政府,是不是到了該有所作為的時候了?
面對日益增多的“牢騷”,人不知足無可厚非。因為從人類歷史的發展來看,“不知足”才有發展的動力,人類的每一次進步都是在不斷的“不知足”中得到了發展。就這一點來看,我們不應該去說教讓勞動者要“知足”。
當然,回顧改革開放以來,讓勞動者“知足”的理由不是沒有。最簡單的事實就是,和改革開放之前比較,大家的工資都翻了“幾倍”。以筆者為例,1996年參加工作,工資不到500元,現而今已經是5 000元了,工作14年,漲了有10倍,按說很快了吧,也挺知足的。但事實就是筆者知足不起來,為什么呢?原來發現自己身邊的人,不管是學業、崗位還是技能有沒有差距,他們的工資都比筆者高,特別是一些在金融、央企乃至政府部門的“哥們兒”,每每見面,實覺錢包“汗顏”。
筆者終于明白,原來“生活越好,牢騷越多”,不是自己不滿意自己,而是和別人比了之后,失落感很強烈。理論上的話叫“相對公平感”缺失。為什么“失落”呢?技不如人,想想不應該,怎么也算一個高級知識分子吧;是單位不好,好像也不是,學校可是“黃金機構”,“旱澇保收”。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呢?經過思索,問題不在于技不如人、單位不好,而是分配制度出了問題。
在經濟學的理論中,好的分配制度應該效率優先;在社會學的理論中,公平才是分配制度好壞的標準。如果用馬克思講的一句話“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來分析的話,那就是好的分配制度應該把經濟學和社會學的理論融合起來,那就是中央提出的“效率和公平”。所以,只有效率,沒有公平,效率最終會被公平毀掉;相反,只有公平,沒有效率,公平本身也沒有基礎,計劃經濟時代的“大鍋飯”就是這個問題。
那我們現在的分配制度呢?從1978年開始考察,有學者將它分為四個階段:一是1978年至1984年,解放思想,恢復按勞分配原則;二是1985年至1991年,打破兩個“大鍋飯”(企業對國家,職工對企業),調整分配關系;三是1992年至1999年,確立改革目標,培育新的分配機制,后來叫作“市場機制決定、企業自主分配、職工民主參與,政府監控指導”;四是2000年至今,工資分配制度全面深化改革階段,核心就是強調各種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要求把按勞分配與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
從四個階段的提法來看,應該是符合“效率”和“公平”兩個標準的,說明制度的價值偏好是沒有問題的。既然制度本身沒有錯,問題只能出在是制度在執行中“走偏了”。
從現實的情況看,制度“走偏”確實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還是以分配為例,“蛋糕”現在做出來了,并且很大,說明我們的分配制度還是有效率的;但是“蛋糕”誰來“切”?怎么“切”?“切”多少就很有講究了。
理論上,政府、資本和勞動者共同在“切”蛋糕,都在“蛋糕”做大的過程中分到了一份看起來還不錯的“好處”。在“切”的比例方面,盡管各方的數據不一致,但公認的感覺是,勞動者的比例拿得最少,不僅表現在絕對數的比例方面,還表現在比例的增長幅度方面,勞動者都是拿得最少的。這就是問題的根本,“公平感”的缺失。
“公平感”缺失的后果是什么呢?從大的方面看是影響社會的和諧穩定,這方面我們已經有很多的事例了;而從小的方面看,就是我們的“效率”可能會被“公平”毀掉。
在這次的金融危機中,我們的感受更為深刻。原來依賴的出口大幅減少,原來要賣給境外的東西賣不動,以外向型為主的企業,特別是中小規模的勞動密集型企業,相當一部分不能經營或者不能有效經營,置身其中的工人,主要是農民工不得不卷起鋪蓋回家,就業形式一下就嚴峻起來。
面對“外需”嚴重不足的現實,我們開始老調重彈,又把內需搬出來,并且以從未有過的急迫心情來需要內需。觀念轉過來了,但市場不認賬,發現很多東西買不起或者不愿買,原因不是不需要,而是“沒錢”,這就是“內需不足”。“內需不牢、地動山搖”。怎么辦?政府搞了以4萬億為內容的經濟刺激“一攬子計劃”。經過1年,成效確實很明顯,中國經濟走出了漂亮的“V型反轉”,全年增長率達到了8.7%,這不能不說又是一個奇跡。
但奇跡的背后是什么呢?是真實性內需貢獻的還是政府在“買單”呢?后者的比重可能大一些。為了讓內需“旺”起來,成為經濟結構調整和經濟發展方式的“引擎”,政府想了很多的辦法,最核心的就是要讓老百姓有一個明確的預期,一個敢于花錢的預期。于是,在政府的主導下,2009年我們基本上建立了覆蓋全社會的保障體系。再加上政府前幾年做的一些工作,現在基本上實現了“種地不交稅、上學不付費、看病不太貴、老了無所畏”,特別是“老了無所‘畏’”,更關鍵。為什么無所“畏”呢?因為我們已經初步建立起了一個覆蓋全社會的保障體系,老有所養了。再加上溫總理講,本屆政府要做到人均120元,敢花錢的預期就更明確了。
預期明確以后,但內需仍然沒有“旺”起來。原來是沒錢花。為什么沒錢,因為收入低。這么大的“蛋糕”收入都去哪里了呢?原來人們發現,政府和資本拿得很多,勞動者拿得不多。怎么解決?就是要把這個比例給調過來,政府讓一點,資本少拿一點,勞動者增加一點,這就是中央提出要加大初次分配比重的一個重要原因。

所以,今年政府工作的一個重頭戲就是“分配”,用溫總理的話講就是,“做大蛋糕是政府的責任,分好蛋糕是政府的良知”。而媒體熱炒的《工資條例》,應該就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下被寄予厚望的,是政府責任之后的“良知”行動。
但我們需要更深入思考的是,是不是有了《工資條例》,分配失衡的問題就能解決呢?比較正確的觀點是,《工資條例》解決不了所有的分配問題,但沒有這個東西所有問題都解決不了。從這個角度看,《工資條例》被賦予了“破題”的功能,如何解題,還需要更進一步的摸索。
從過去的經驗來看,重大疑難問題的解決顯然不能僅僅靠一個制度,這是不現實的。既然如此,《工資條例》的目的是什么呢?調節失衡的分配制度或許太過于功利,并且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因此,如果說《工資條例》能夠出來的話,筆者認為,其最大的意義應該在于:讓每一個勞動者都有說話的權利,讓每一個勞動者都能感覺到勞動體面,讓每一個勞動者都能感受到做人的尊嚴。但對每一個勞動者而言,怎么說話呢?
首先,要讓每一個勞動者都“能”說話。
“資本+勞動=利潤”。公式很簡單,也很“骨感”,但利潤中有多少是資本貢獻的,有多少是勞動貢獻的卻“糾纏不清”。資本家說,沒有我的資本,你就沒有工作,還奢談什么工資;勞動者說,沒有我的勞動,你的資本也賺不了錢。看來各有各的道理,如果雙方要“較真”,可能都沒有好處。為了把這個問題說清楚,經濟學家想了一個辦法,那就是誰“稀缺”,誰的貢獻就大,也就可以多拿一點,這就是資本雇傭勞動的由來。
看來,資本之所以能夠雇傭勞動,根源在于它很稀缺。既然稀缺,大家都想要,誰給的條件優惠就給誰,資本的“買方”地位由此形成。
面對資本的強勢,原本在計劃經濟時代很有“話語權”的勞動者不得不“妥協”。“妥協”的后果就是在滋長“資本持續傲慢”的同時,不得不承受低于預期的工資價格。一旦勞動者對工資表現出些許的不滿,嚴重的后果就是“走人”。資本之所以敢這么做,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一個勞動者后面有N個替補在等著上崗,這就是為什么“富士康”盡管在員工“九連跳”后,每天的廠門外還有千八百的人等著進入的一個重要原因,而這也是資本的底氣所在。
所以,要讓勞動者能夠說話還真不容易。誰讓你“過剩”呢?從效率的角度講,面對過剩的勞動力,勞動者“噤聲”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如果把這個問題跳出效率的范疇考察,問題就很大,最大的問題就是“公平”的缺失,直接的后果就是破壞效率可持續增加的社會環境。請不要忘記,富人之所以是富人,歸根到底是他的財富能夠在社會環境中得到保持。如果這個環境被破壞了,富人也可能會“一無所有”。因此,我們講“企業家要有道德血液”。正如經濟學的鼻祖——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里所言,如果社會財富只集聚在少數人手里,是不公道的,注定是不得人心的,必將造成社會的不穩定。
理論上,富人的道德血液應該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自發性的培養道德意識,并將意識融入到企業的經營管理中。勞動力是生產要素,但和資本要素的所有者是人一樣,勞動力要素的所有者也是人。既然大家都是人,“生而平等”應該是一個基本的人權理念。因此,企業家不能把勞動力要素和其他要素一樣等同管理,要結合勞動力要素的“人”化特質,寄予更多的人本關懷,要讓每一個勞動者有充分表達意見的機會。二是遵循法規,在程序合法的情況下獲取收益。過去的經驗表明,在資本“貪婪”的驅使下,自發性的道德意識幾乎沒有,而約束的法律機制又沒有到位。因此,《工資條例》的首要目的就是要給勞動者一個能夠說話的權利,讓資本家明白,給勞動者說話的權利,不是施舍,而是制度的要求。如果一個連制度都無所畏的資本,估計也長不了。
其次,要讓每一個勞動者都“敢”說話
《工資條例》給予了勞動者能夠說話的權利,但勞動者是否將能夠轉變為行動,這涉及到一個說話“膽量”的問題。換句話說,面對資本的強勢,勞動者有沒有說話的“底氣”?
理論上,“底氣”是否足夠的條件有兩個:(1)家底是否殷實。家底越殷實,說話的底氣越足,這就是大家都在說“富二代”有點找不著北的一個重要原因,“錢多膽壯”;(2)制度鼓勵。好的制度應該是讓好人變得更好,讓不好的人無處遁形。這樣,制度的價值功能才能彰顯,制度的權威才能得到認可,制度的執行才能不被“規避”。
《工資條例》出臺,無疑給了勞動者一個能夠說話的機會。面對過剩、并且在將來一段時間還有可能繼續過剩的勞動力市場,勞動者能不能把制度賦予的權利變為行動,顯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還有很多的因素需要分析,還有許多的技術需要予以支撐。因此,勞動者要把權利變為行動,關鍵是要有權利的意識,并不斷培養對權利意識的維護能力。
受文化因素的影響,中國的勞動者普遍存在一種對資本、對制度、對權力的敬畏。正是這種敬畏,讓中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獲得了極大的發展。但是,如果敬畏變成一種服從乃至“奴從”,后果就堪憂了。
那么,勞動者的權利意識如何培育呢?社會的說教和制度的引導固然是重要的,但關鍵還是要自己把自己當回事。權利是天生的,但天生的權利更需要后天的保護。因此,勞動者就要做到有所需、有所不需。在生存面前,“面包固然重要”,但比面包更重要的還有尊嚴和價值。古人言,“憐者不受嗟來之食,志者不飲盜泉之水”;我國著名散文家朱自清教授也有一句話:“寧可貧病而死,也不接受這種侮辱性的施舍”。
現實當中,勞動者為了一份“面包”,不惜犧牲尊嚴乃至生命的現象也是有的。這既是勞動者的不幸,也是制度的不雅,更是社會文明的“污點”。如何改變,首要的就是要勞動者去樹立自己的權利意識。自己的權利只有自己爭取,權利才能受到尊重,侵害權利的人才能有所畏懼。
與此同時,勞動者還應將個體的權利融入集體的權利中予以表達,并以集體的意志發聲。中國工會作為勞動者的“代言人”,既是勞動者權利意識培育的重要主體,更是勞動者權利維護的重要保障。因此,要把最廣大的職工組織到工會中來。胡錦濤總書記也明確指出:工會要把表達和維護職工合法權益作為其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這既是廣大職工的迫切需求,也是執政黨的殷切期望,更是中國工會需要承擔的神圣使命。
面對日益趨緊的勞資關系,執政黨對工會提出了明確的要求,也承諾將更多的資源和手段賦予工會組織,要把黨政所需、職工所急、工會所能的事情交給工會組織去辦,要不斷擴大工會的影響力和號召力。《工資條例》將工資協商引入的制度預期就是,要讓廣大職工不僅“能”說話,還應該“敢”說話。這就要求廣大勞動者,在自覺培養和維護自身權利意識的同時,更加自覺地將個人的權利意識融入到工會組織中,并通過工會組織更加強有力地維護自身的權益。只有這樣,勞動者的個人權利才有保障,勞動者的尊嚴才能得到有效的彰顯,勞動關系可持續性和諧才有基礎。
最后,要讓每一個勞動者都“會”說話
《工資條例》賦予了職工“能”說話、“敢”說話的權利,但更重要一點是,勞動者要“會”說話。從某種意義上,這是實現勞動者自身權益,實現勞資雙贏和勞資和諧的關鍵手段。
就總體上的趨勢而言,勞資共贏是雙方訴求的根本目標。但在具體的時點上,勞資利益的分歧是客觀存在的,也是不容回避的。
面對具體利益的糾葛,理論上的解決辦法只有兩個:一是“魚死網破”;二是學會“妥協”。比較而言,“魚死網破”不應提倡,除非觸及最基本的底線,否則不應出現。因此,作為理性的利益主體和社會成員的勞資雙方,比較可行的辦法就是要學會“妥協”,在“妥協”中共生、共享、共成長。這就是《工資條例》中所衍生出的另一個制度偏好,以協商的方式來解決利益問題、權利問題。
所以,勞動者要“會”說話,關鍵的一點就是要學會“協商”。沖突總是源于“誤解”和“不信任”。消除“誤解”和“不信任”,也就減少了很多沖突。要做到這一點,勞動者就應該自覺做到以下幾點:
一是要培養協商的意識。意識決定行動,好的意識才有好的行動,也才有好的結果。尤其是在尊嚴面前,單純的以生命做賭注的利益訴求方式絕對不值得鼓勵。因此,敬畏生命才能推崇協商。公民社會的一個最大進步就在于社會性的協商機制。協商的目的不一定就是要達到某一特定的目的,更優的制度內涵在于雙方的溝通,并通過溝通來彌合分歧,消除誤解,累積信任。這在我國當前的勞資關系狀態下尤為緊迫,也是制度層面應予以高度重視的內容。
二是要培養規則意識。協商的目的是凝聚共識,無論是否能夠達成共識,在協商的過程中都要有規則意識,對協商的結果應自覺遵守。只有這樣,協商文化才能培育,協商意識才能完善,協商成效才能顯著。不可否認,在當前的勞資協商中,也確實存在一種“單方文化”,要么接受、要么破裂,這實際上就是沒有很好的規則意識。
三是要善于應用制度所允許的壓力機制,確保協商目標的實現。現實當中確實存在一種現象,就是有一方不愿意協商;即使協商,也不愿意妥協。從目前的情況來看,資方的因素更多一些。資方之所以這樣,就是我們前面講的,一個是確實還比較“稀缺”,還有一個就是既往路徑下勞動者習慣性的被“噤聲”所導致的資本傲慢。
所以,解決問題的辦法就是要有適度的壓力機制,并且是制度所允許的壓力機制。從目前的情況看,可選的壓力機制包括申請制度救濟,比如勞動仲裁、法律訴訟等;還有一種辦法就是更加重視和發揮工會的作用。
筆者一直強調,國情不同,勞動關系調整的范式不一樣,工會的功能也存在差異。在壓力機制方面,中國工會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勞動關系理論,但可以基于國情創新壓力機制實現的方式和路徑。而“源頭參與、科學維權”無疑是建構有中國特色勞資協商壓力機制的有效選擇。通過源頭參與,將與協商有關的壓力機制訴諸于制度設立的完善性方面,為實際的應用提供制度基礎,以保證壓力機制的程序合法;在具體的維權行動方面,要講究科學,這就要求工會要有政治意識、大局意識和責任意識,始終將勞動者的權益作為自己最核心的使命予以實施。也只有這樣,中國國情下的工會多維目標才能實現,工會的社會功能也才能充分發揮。
綜上所述,面對《工資條例》出臺的潛在期望,固然可以從技術層面對目前失衡的分配秩序和勞資關系有所改善,但作為事關勞動者最核心經濟權益的工資,《工資條例》最大的制度價值應該是要給勞動者一個“能”說話的機會,“敢”說話的“底氣”和“會”說話的能力。還是那句話,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就是,凡是市場能夠解決的東西歸市場,凡是市場搞不好的東西歸政府,但政府并不是簡單地應用行政權力予以干預,而是要弄出一個好的制度,并在制度的執行中扮演好“裁判者”的角色。只有這樣,社會的權利意識、規則意識才能有據可依,勞資關系也不例外。
欄目主持:紀 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