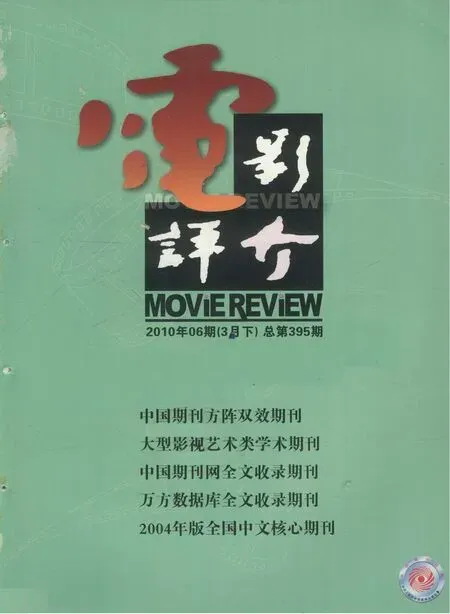關于“全球化語境下中國電影的跨文化傳播”的現象學之思——以電影《 梅蘭芳》 為例
單就本文的標題而言,我們可以做一些語義分析,或能更好的把握該問題的意義。顯見,該題目涉及到三個關鍵詞,即“全球化”、“文化傳播”以及“中國電影”。下面我們試著分別簡析之。
首先是“中國電影”。直觀的理解,就是中國人制作的電影,但是這一行為的背后涵義是豐富的,因此直觀的理解恰恰是一種匱乏,而需展示其背后的涵義。自然,“中國電影”必然的被賦予著處于活的歷史中的中國文化意義,本文以為這倒是中國電影之為中國電影的本體。例如中國電影《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其所依原著雖為外國同名小說,再者美國亦有對此小說的電影制作(1948年《巫山云》),然其之為中國電影是與原著和《巫山云》不同的。如一位研究女性理論的學者曾寫到,“導演徐靜蕾將小說背景轉移到中國,這一創造性的改編是成功的。但是除了和原著基本相同的話外音體現出文學美外,其他的臺詞、內容,與原著契合度就相對較低了。徐靜蕾說:‘茨威格的原小說充滿了激情,但我的電影很具體,偏重理性,所以兩者其實相差很遠。’然而她將原著中的熾烈奔放收斂為中國式的婉約隱忍,將慘烈的飛蛾撲火演化成了對男主角的寬恕和對女主角的救贖。當然這種救贖有很大的想象成分。不過,更多的是一種中國女人式的羞怯,羞于表達自我,怯于面對現實。寧愿在暗戀和自戀中生或滅,也不愿意面對自己、面對現實。”[1]不論此評價得當與否,但我們從導演和評論者的理解中可以看出,該小說的中國電影版已然被給予了活的歷史中的中國文化內涵,例如對女人的理解。所以中國電影之所是,不在于其技術層面或制作者,而在于其所賦予的中國文化內涵才如其所是。
再者是“全球化”。這是當下的一個流行詞匯了,大概無論何者都能對之言語一些,但常識中的理解和其本質的所有卻差之千里。不過當然,這個差距也大多被學界所意識到了,無論是西方學界的后現代思潮對現代性所塑造的同一性的顛覆抑或是漢語學界的思者的文化自覺,因此該觀念并非如其在常識理解中所負載有那么多的積極意義。
直觀地理解“全球化”,即全球各民族國家的經濟市場、政治理念、文化理解以及生活方式的融合與共化。一般的被分階段的理解,早期是隨著國家殖民活動而產生的資本和商品、貨物的流動所帶來的政治體制的融合與共化,而之后發展階段便過渡到了文化、思維和生活方式的融合,再者隨著當下互聯網技術的普遍,全球信息的傳播共享,全球化的標志具體的體現在了個體的身上。就全球化的成果來看,我們直觀的接受到的信號便是我們生活方式和內容突破了地域和民族的限制并實現著全球共同秩序和思維方式、文化特征的建立。例如跨國公司的發展、國際市場的建立、國際組織的活躍以及民族國家體系的瓦解和信息的國際化共享等等。但是就成果來看不免會與其本源失之交臂。本文以為全球化的本質恰從其發生之源倒可以看出。本質就是資本主義的新殖民運動,而資本主義的根原便是個體性的、中心性的,因此由個體中心性的資本主義所帶來的全球融合運動恰是一種對他者的剝奪。如胡塞爾在《歐洲科學的危機和超越論的現象學》中所相信的,歐洲文明自身負載著絕對理念,因此其它文明的歐洲化決不是歷史的荒唐胡鬧,而是具有世界意義。[2]可見全球化的本質是一種歐洲中心主義的普世神話,是個體中心性的資本主義的新型殖民運動,不過是沒有了槍炮而換之普世倫理秩序和開放市場與自由資本罷了。由此觀念產生并與之對立的便是民族主義。因此在資本主義的新殖民運動和民族主義的保守運動的二元邏輯中,只能有暴力傳播和固步自封,不可能實現和諧的跨文化交流與傳播。
但全球化如今已然成為事實,因此我們需要的不是對此的否定,而是代之以新的詮釋,在對文化全球化的新的理解境遇中方可實現更好的文化傳播模式和理念。然這不是一兩言便能理清的,本文理解,全球化的主體不是資本集團,而應該是民族文化體,即任意可能的多元的民族文化是全球化的參與主體。資本集團的全球殖民可以在世界新秩序的構建中予以削弱,而另一方面各民族文化的多元發展是走出新的文化間交往的必徑。因此這里存在一個辯證關系,民族文化的強大與發展,是民族間文化交往的前提,亦是超越個體民族體的全球文化共同體建構的動源。
可見,跨文化傳播需要在新的全球化視域中方才可能。而新的全球化視域的生成在新的媒介技術條件下并非異想。在文字時代,由于各民族語言和文字的不可通約造成了理解的限度,在如今的技術條件下已然被克服。多媒體技術通過直觀形象傳遞的信號可在不同語言的民族文化間實現共享。例如互聯網和電影便是優秀的媒介資源。我們下面試以陳凱歌08年制作拍攝的電影《梅蘭芳》為案例進行簡要分析。
電影《梅蘭芳》是一部人物傳記電影,其通過對人物所經歷故事和人物性格的直觀展示而彰顯的是影片中人物某些被認可的積極成分。如對傳統文化的維新精神,如對藝術人格的尊重而不甘于“相公堂子”,如對民族國家的危患情懷與對同胞的深沉的愛而不低頭于侵略者的暴力(影片中的梅蘭芳對日本軍官、少佐田中隆一發出了“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支那文化;欲征服支那文化、必先征服梅蘭芳”論調的反征服),等等。這些均是活的歷史中的中國文化的給予。因此,可見影片通過故事和人物所意向展示的是活在當下的文化理念。其實,這些理念也有通過其它媒介而向他者文化傳播共享,但電影媒介之優勢恰在于它能克服語言障而通過直觀的方式引起觀者的情感共鳴、進而成功的傳播文化理念。可見,電影媒介在跨文化傳播中的功能是強大的,甚于能更深刻地表達理念的文字文本的媒介。
再者,熟識“梅史”的人都知道,陳凱歌導演的《梅蘭芳》更多地是一種演義。例如關于梅蘭芳與日本的關系,梅蘭芳和“十三燕”的打對臺。都與迄今所知曉的歷史事實不符合。梅蘭芳本身與日本的關系實際上并不壞,至少沒有影片中的日據事件,而影片中的詮釋顯然是基于活的歷史中的文化理念的,因此是一種解釋學式的言說,帶有著當下文化境遇的信號。而梅蘭芳與“十三燕”的對臺亦是如此,歷史上梅蘭芳的成名不是一時一場所獲得的。而且影片強調梅蘭芳的勝出在于其對傳統劇目的創排,很明顯是要體現對文化的日新精神,而事實上梅蘭芳的創作并易事,劇本、服裝、唱段、場面等千頭萬緒,而且要順其時勢方能成就維新。因此很顯然,人物傳記電影不僅僅是直觀的告之人物故事,白描和擺拍之間亦無不可逾越的隔閡,而電影作為媒介顯然有對民族文化的詮釋功能,民族文化也恰是在此詮釋學方式中實現了與他者的傳播交流。因為文化間交流不是兩個既成的、已然的東西的外在比較,而是基于共在的生活境遇中內在地關聯的交往對話的。
[1]王虹,《羞怯與自虐——<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的中國式表達》,《電影文學》2005年第8期。
[2]胡塞爾,《歐洲科學的危機和超越論的現象學》,張慶熊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第2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