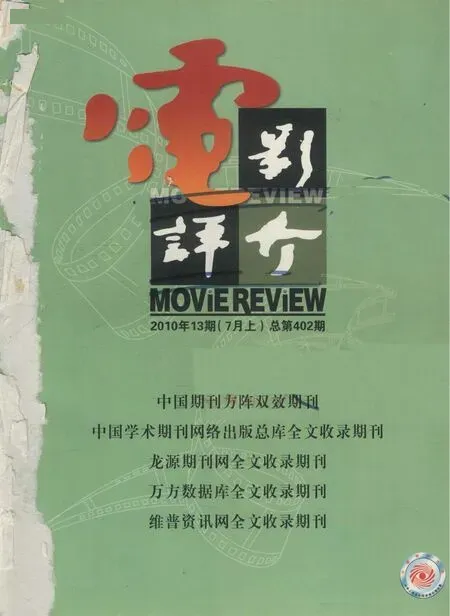淺談北野武電影中的重復蒙太奇
有學者說:“對電影劇作者來說,必須懂得什么是蒙太奇,和什么是蒙太奇思維。電影劇作者正是運用蒙太奇思維得以把一個電影劇本構筑起來的。”[1]顯然,這種說法是有道理的。那么什么是蒙太奇?簡而言之,就是鏡頭與鏡頭的組接或畫面與畫面的連綴。對于這一點,日本導演北野武有他自己的理解,在一次采訪中,他對影片《壞孩子的天空》的編劇構思做出如下解釋:“……最早的形式類似報上的四格漫畫,第一張是兩個人在學校里以奇怪的姿勢騎車,第二張是兩人被拳擊手打,第三張是一個成為拳擊手,而另一個變成黑道混混,最后一張也是同樣的畫面……我當初以為只要把這四格連貫起來,應該就能拍成一部電影……”,[2]在我看來,北野武是以最簡潔的方式正確理解了一個電影編劇的復雜問題,他甚至認為電影是“沒有音樂對白,只有四張幻燈片就讓觀眾落淚感動……。以前之所以會發展出電影,就是因為一張畫面無法表達……”[3]。北野武憑著這種習慣的“蒙太奇構思法”擔任了他執導的十部電影的編劇,在這些對白極簡的影片中,重復蒙太奇是他經常使用的為其影片提升內涵意蘊的標志性編劇特色。
作為敘述蒙太奇手法之一,重復蒙太奇主要是通過“一定寓意的鏡頭或場面在關鍵時刻反復出現造成強調、對比、呼應、渲染等藝術效果”[4],值得強調的是,這種重復不僅是從內容到形式的再次重現,更是以此突出人物命運、性格、心理的變化,達到深化主題的作用。
在影片《壞孩子的天空》中有一段表現新志與小馬在大橋上跑步的情節,小馬在幾天前被一個拳擊手打得狼狽不堪,為了杜絕此類事件的再次發生,他倆決定以跑步來強身健體。在跑步的途中,新志有意繞遠路從橋的下面跑過來。故事發展到后來,當新志在拳擊教練的帶領下再次從橋上跑步時,他已經被藥物和酒精整垮了身體,畫面同樣呈現出他繞到橋下的動作,但這次是因為吃了不該吃的藥物去上廁所。同樣的兩場情節暗示著不同的含義,第一次的出現表現了兩個青春期少年親密的友誼和健壯的身體,讓人感覺溫暖和羨慕;當第二次出現時,暗示著兩個昔日的好友已分道揚鑣,而且新志的身體由于嫉妒者的陷害日漸衰弱,拳擊的道路已快走到盡頭,兩組鏡頭的前后對比營造出令人追悔惋惜的意境。
影片《花火》出現了兩次警車從廢車場旁的小路駛出的鏡頭,但第一次是真正的警車,第二次是阿西從廢車場買來的廢車改裝的冒牌貨。當第二次同樣的畫面出現時,激起了觀眾強烈的沖動、快感和英雄般的自由感,給搶劫銀行的阿西籠罩上了一層劫富濟貧的俠士光環,這種重復不僅起到了預示影片情節轉折的作用,同時,也強化了人物悲劇結局的意象。
影片《玩偶》中同樣反復出現男女主人公身系紅繩在樹林里漫無目的游走畫面,當影片的第一個鏡頭呈現出這個場面時,給觀眾一種莫名其妙、不知所云的感覺,隨著故事的發展,當同樣的畫面再次呈現時,觀眾在心中漸漸累積起來的同情和悲憫迅速點燃,與情節產生強烈的共鳴,同時,影片中反復出現的行走鏡頭也強化了人作為流浪動物的意象。
在北野武的多部影片中,我們還可以發現他傾向于將故事的開頭和結尾設置成圓形結構,即開頭和結尾的情節設計完全重合,使影片在無形中強化了內在張力。
在1989年的處女作《兇暴的男人》開始 6 分鐘時,用了一組固定、移動鏡頭表現警察諒介從室外走進辦公室的過程,并配有一段旋律輕快的背景音樂。影片接尾時,真正的內奸——整日跟在諒介身邊的小警察菊池,踩著同樣輕快旋律的背景音樂,在同樣的固定、移動中從室外走進了室內,但是,這時的房間不再是影片開始時的警察辦公室,而是黑幫老大的所在地。我們看到他很老練地踏著大步到公司向黑道接班人領取保護費,當初清新可愛的菊池竟成了第二代的內奸巖城,黑白不分的循環往復似乎是那個只懂兇暴的正義男子難以預料的人性悲劇吧!可以發現,北野武在影片的開頭和結尾做了匠心獨具的重復處理,復現式蒙太奇似乎想力圖喚起觀眾的某些記憶,并誘導觀眾做出自己的評判:渴望獲得真理的叛逆英雄最終死在了小人們謀劃的一場利益游戲中,讓人覺得生命的脆弱和輪回的短暫與可笑;鮮明的前后對比關系,傳遞出一陣陣“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語淚先流”的無奈與悵惘之情;出乎預料之外的小人得志的結局讓人深深體味到現實的殘酷無情, 貪污腐敗永遠是當代文明社會割之不去的一枚毒瘤。
《3-4x10》同樣是一部前后對應的影片,北野武的這次“夢幻之旅”生動地描繪了一個無力洗刷恥辱的小人物的英雄夢。故事從一片社區的棒球場開始,影片的第一個畫面是黑黢黢的環境中主人公雅樹一張表情呆滯的面孔,接下來是他從球場廁所里走出來的一個全景畫面。在故事結束時,同樣的兩個場景再次出現,前后完全吻合的處理手法暗示著整個故事其實是雅樹在黑暗的廁所里獨自幻想的一出戲:一個受到侮辱的小人物渴望用同歸于盡的方式洗刷恥辱的英雄夢。可以看出,北野武用前后呼應的夢的形式賦予了影片濃厚的“存在主義”色彩,雅樹的夢想正是對薩特“絕對自由”觀念的最佳體現。瘦小的身體和低下的社會地位注定雅樹無法用實際行動為自己洗刷恥辱,但這些只不過是原始的給予物,人可以自由選擇一個意義(態度)賦予這種給予物。因為“至于我長得美還是丑,我是無產者還是名門望族的兒子,天下雨還是天熱……這一切都是我無能為力的事實。然而對上述獨立于我的存在方式采取何種態度卻由我自己選擇。我可以為這些事實感到驕傲或可恥,接受它們或反抗它們。我并不選擇它們,但我選擇對待它們的態度。”[5]因為人雖然不能改變世界,卻可以改變自己對世界的態度。
蘇聯電影藝術家羅姆說:“把兩個鏡頭連接起來,有時可以產生這兩個鏡頭本身所沒有包含的第三種意義……可惜現在的劇本過分依靠語言,幾乎不運用畫面,把畫面完全留給導演去處理,電影不應濫用語言。”[6]可以看出,作為編劇和導演的北野武不僅善于創造具有視覺性的畫面,而且還善于將畫面和畫面組接起來產生出第三種意義。同時,極簡的對白風格也很好地克服了電影編劇中過分依靠語言或濫用語言的弊病。
北野武影片在世界各種電影節上的頻繁獲獎不僅是對他導演藝術的欣賞,也是對其編劇技巧的肯定。對重復蒙太奇的嫻熟應用使他的影片獲得了與眾不同的累積感和厚重感,那一幀幀展示社會現實,揭示人生哲理的相似畫面構建成了北野武編劇的風格性特征。
注釋
[1]汪流:《電影編劇學》,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0年6月版。
[2]毛過:《北野武完全手冊》,北京朝華出版社,2004年 6 月版。
[3]同上
[4]《電影藝術詞典》編輯委員會:《電影藝術詞典》,中國電影出版社, 1986 年版。
[5]保羅?富爾基埃:《存在主義》,潘培慶譯,上海譯文出版社, 1988年5月版。
[6](蘇)羅姆:《電影劇作講話》,中國電影出版社198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