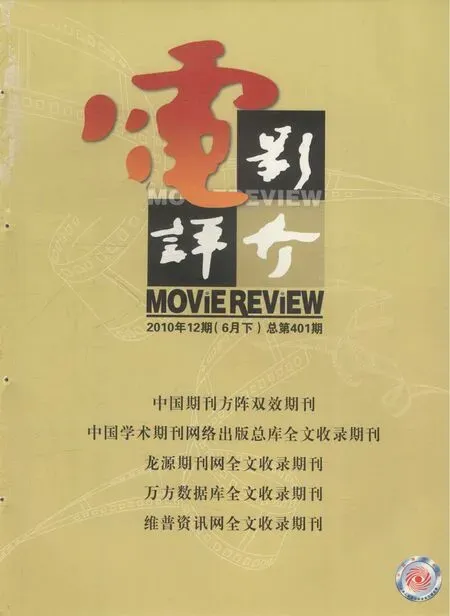《愛有來生》——女性主體意識的失落
一、引言
2010年上檔的一部由女性導演拍攝的影片《愛有來生》獲得了不錯的觀眾口碑,雖然票房不盡如人意,但是女性導演的大膽嘗試不可忽視。作為一部進入院線的商業片,導演俞飛鴻在接受采訪時曾說到,“我沒有什么電影技術可炫耀的,我也不覺得需要去用什么花哨的電影技術來競爭。我就是很老實地講了一個前世今生的愛情故事,觀眾能夠感動地哭就夠了。”俞飛鴻表達了隱匿于電影背后的商業邏輯,正如理查德?麥特白所講“觀眾去電影院消費他們的自己的情感。電影應該這樣被組織起來,讓觀眾在一種秩序之中產生他們的情感并獲得滿足”[1]。由此我們能夠看到俞飛鴻不無誠懇的創作態度以及通過煽情與觀眾達成共識的敘事策略。電影也的確拋棄了當下愛情題材電影創作中的類同化傾向,用唯美的鏡頭語言講述一個以“自我犧牲”為主題的前世今生的愛情故事,對現代人的價值觀造成一定的沖擊。但正如女性主義電影批評所揭示的:好萊塢經典電影模式的意識形態深處具有反女性本質。《愛有來生》作為一部商業電影,盡管由女性導演操刀,仍體現了男權社會主導下的意識形態對女性的塑造,女性角色依然逃脫不掉男性視閾的控制,女性主體意識的喪失成為這部電影的一大缺憾。
本文通過對《愛有來生》的分析,試圖揭示隱匿在商業片邏輯后的男權秩序,以及商業片女導演自覺認同男性主導話語權的無意識,對中國商業片中女性形象的表達提供參照。
二、敘事中的遮蔽——女性的被動與失語
影片敘述了阿九作為家族復仇工具被阿明搶走,阿明竭力討好阿九,并因對方的冷漠心灰意冷出家。阿九漸漸領會到阿明的真情,對他心生愛意,然而此時阿九兄長前來復仇,兩人約定來生再見雙雙死去。五十年間阿明一直在等待阿九,當他看到轉世后阿九的幸福生活之后,欣慰地轉身離去。我們可以看到,盡管影片中阿九一直處于“愛”的承受者地位,她依然繼承了傳統電影中女性作為男性的欲望客體而存在的身份。在影片中阿九對阿明的吸引首先來自她性的誘惑力。勞拉?穆爾維認為以男性視角出發的電影通過特有的修辭手段,把女性的視覺形象編碼為色情的消費對象。“女人在她們那傳統的裸露癖角色中同時被人看和被人展示,她們的外貌被編碼為強烈的視覺和色情感染力,從而能夠把她們說成是具有被看性的內涵。”[2]九兒這一角色最大程度地體現了男性將女性置于被觀賞和賞玩的地位,成為男性獲得性刺激的快感來源。在導演設置的情境下,鏡頭凸顯九兒作為女性的美麗特質,并把她作為男性欲望的客體而放大。導演不厭其煩地把特寫鏡頭對準女主角的臉,尤其是當阿明凝視阿九時,攝影機將觀眾視點納入阿明的視點,阿九成為雙重的被看對象。影片第一次出現對阿九的性別魅力的渲染出現在第二十三分鐘,悠揚的笛聲吸引男主人公翩然而至,女主人公一襲紅衣,手持一柄羌笛,背對觀眾入畫。這一頗具傳奇性的相遇和神秘的背影預示了阿九作為女人的不同尋常的魅惑力。接下來的鏡頭反打阿明疑惑的眼光,觀眾承接阿明的視線,鏡頭再次轉向回眸的阿九,并從中景變焦為一副凝視眼神的特寫。至此,影片首次完成對阿九女性魅力的渲染。在女性主義的觀點中,女性始終是作為男性的另外一個能指而存在,“男性菲勒斯中心主義自相矛盾之處在于,它是依靠被閹割的女人形象來賦予它的世界以秩序和意義的。”[3]女性身體所產生的閹割焦慮促使男性有意識地通過兩種途徑來解決,一是窺淫癖,二是戀物癖。前者通過對引發焦慮和威脅的女性懲戒和放逐從而消除閹割焦慮。后者通過“創造了對象的有形的美,把它變成自身就能令人滿意的某種東西。”[4]這種“有形的美”通常來自于女性身體某部分的美化展示。影片不斷強化阿九的美麗面容,尤其在她被阿明搶入山寨,被迫與之結合的段落里,出現大量阿明對阿九凝視和撫摸的鏡頭,赤裸裸的展示男性的拜女情節。此時觀眾的目光也追隨男主人公的視線,凝視于失語的女主人公的面孔之上。這讓人聯想起默片時代好萊塢銀幕女神嘉寶在柔光鏡下朦朧的臉部特寫。盡管電影歷經一百多年的發展歷程,女性作為消費對象和欲望客體的功能依然沒有得到改變。
單純的女性奇觀影像,并不能在線性時間上推進情節演進,導演把這種男性視角的凝視融入到阿明對阿九純情而又固執的單戀之中,阿明幾乎可以為阿九做任何事情,他可以安靜地注視做女紅的阿九,為她布置滿屋的杜鵑花,情之所至為之作畫,這一切換來的是阿九一句:“茶涼了,我再給你續上吧。”阿九的冷漠與封閉正是男權社會女性主動放棄話語權的隱喻。阿明為贏得阿九的愛所付出一切的過程,體現了男性窺淫癖和戀物癖的雙重之“看”。按照勞拉?穆爾維的理論,窺淫癖可以納入敘事之中,推進線性時間演進。正如戴錦華所說,“主流商業電影的敘事,事件實際上是破碎并充滿斷裂的。兩種影像與敘事機制交替構成主流商業電影的敘事體。其一,是敘事性的影像序列,它成功地制造著某種時空連續的幻覺,攫取著觀眾對劇情的緊張關注,它始終以男性主人公、英雄的行動與歷險為其表現對象。”[5]對阿九性別魅力的展示成為一種修辭結構,而敘事的功能則由阿明對九兒的不斷示愛承擔。“穆爾維認為,男性創造動作。不僅如此,故事的講述,它的敘事過程,要經過男性目光的中轉,男性目光是觀者投向女性目光的中介。”[6]阿明看阿九的視線成為代替觀眾“看”的中轉,男性的意志再次成為影片的基礎和向導。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愛有來生》中一系列的敘事機制建立在男人看/女人被看的基礎上,父權邏輯通過把色情編碼進父權秩序的語言之中,通過特殊的修辭結構和敘事結構使女性角色成為被消費的對象,實現了男性對女性的控制。
三、感動女性的男性愛情觀
《愛有來生》運用了超現實的情景和倒敘結構講述人鬼之間的愛恨情仇,通過梳理阿明和阿九/小玉情感發展線索,我們可以洞察電影蘊含的男性邏輯的愛情觀。阿九與阿明的情感糾葛大致可以分為四段:⑴阿九扮演復仇女神角色接近阿明并被阿明掠奪。這一階段,阿九處于失語的被遮蔽狀態,承擔被利用的工具角色。紅衣阿九只出現兩次:第一次是初見阿明,端坐于崖石之上,象征女性吸引力和不可被控制的魅惑;第二次是與阿明成親之時,象征兩人關系的轉折。除這兩次造型之外,白衣阿九成為其內心外化的體現。一襲白衣造型象征了其“貞女”身份的純潔無辜,女性在此成為被壓抑和奴役的能指。在此階段阿明搶奪阿九的緣由是處于性本能的驅動,導演企圖美化阿明搶奪阿九的私欲,將兩人的相遇設置在仿若世外桃源的曠野,并用高調攝影將這一場景浪漫化。⑵阿明與阿九成婚后,阿明傾心對待阿九企圖感化對方,但遭到冷遇。這一階段是導演煽情的鋪墊,阿明對愛情的獲取方式本身就是強盜邏輯,即我愛就要得到。影片掩蓋了阿明代表的父系強權邏輯,為阿明的愛的方式辯護。阿明的愛是前現代時期的愛情,他的愛情本質上是戀物癖式的,女性充當的是欲望投射的對象。影片中出現阿九對著籠中雀暗自神傷,并放走金絲雀的一幕,金絲雀的意象顯然是阿九境遇的象征。⑶阿明對愛情心灰意冷而出家,阿九終被感動,兩人的和解被前來復仇的阿九哥哥打破,最終在爭斗中兩人雙雙死去,并約定來世再見。⑷阿明找到已轉世的阿九,看到她盡享幸福后轉身離去。這一部分的戲放在夜間處理,與之前的高調攝影形成對比,造成幽謐的人鬼相交的氣氛。
在中國古典藝術中,女性往往是被迫做出情感犧牲的一類。從《詩經?氓》中被遺棄的女主人公開始,中國文學藝術中女主人公無法擺脫被男人追求、占有、拋棄的宿命。打破這種宿命不僅是革命意義上的婦女解放,同時意味著女性性別意識的重建。新中國成立到1979年,為打破封建社會父權制對女性的性別壓制,主流意識形態塑造了一批反抗悲劇宿命的“花木蘭”式的女戰士形象。正如戴錦華先生所言,這類反抗宿命的女性形象呈現出“非性別化”的狀態,階級的差別掩蓋了性別的差異,完成革命經典電影模式化塑造。“男性、女性間的性別對立與差異在相當程度上被削弱,代之以人物與故事情境中階級與政治上的對立和差異。”[7]女性的覺醒是迎向意識形態的召喚,經典電影模式的敘事巧妙地把女性與被壓迫階級畫上等號,完成了一次個體沉浮對集體命運的隱喻。“對于女性命運的描述便成了舊中國勞苦大眾共同命運的指稱,一個恰當而深刻的象喻。”[8]因此,中國電影缺少對女性“被追求、占有、拋棄”宿命的真正反抗。如果說意識到女性悲劇命運是一種自覺,《愛有來生》則主動放棄了這種自覺的可能性,代之以女性被男性專制獨斷的情感付出感動,對自我命運繳械投誠。女性獨立人格和對自我命運的把握被棄置不顧,而男性卻成為具有自我放逐精神的犧牲者。至此,我們看到90年代以來犬儒價值觀的彰顯:被損害者放棄了反抗,而壓迫者被書寫美化獲得合法身份。
女主人公阿九身體的展示本質上是一種消費符號,導演不厭其煩地用特寫對準女演員的臉,這張臉上一成不變的冷漠表情僅僅出自為家族復仇的動機。從某種意義上講,阿九并沒有意識到她存在的價值,她甚至不如五、六十年代的林道靜、瓊花們更具備主體意識覺醒的姿態。當激進的意識形態符號化表述被放棄后,創作者走進了虛幻卻蒼白的愛情烏托邦。感動取代了思想成為快節奏消費時代電影占領市場的賣點。
導演聰明地用男主人公的放棄滿足了大多數女性觀眾的觀影期待,而這卻恰恰反映出現實生活中女性在愛情中被迫付出更多的境況。正如取得火爆票房的《我的野蠻女友》,女性通過電影的想象方式把被壓制的地位轉換為肆意欺凌男性的暢快發泄。《愛有來生》把女性在婚姻愛情中被拋棄的現實境遇改寫為男性為成全愛人幸福而自我放逐,這種迎合女性觀眾的劇情設置激發女性觀眾陶醉于影片的悲劇氛圍,完成自我的想象性慰藉。
四、女性審美意識的凸現與審美內涵的缺失
作為一部由女性導演兼主演的影片,《愛有來生》體現了女導演細膩唯美的美學追求。高調攝影為畫面蒙上油畫般的質地,金黃暖色調營造出懷舊的感傷,為人鬼隔世之戀增添了些許溫情。在涉及人物內心情感波動時,影片多處采用360度攝影,與世間輪回的時空相應和,具有很強的藝術感染力。劇組遠赴云南全境取景拍攝,力圖為傳奇式的浪漫愛情故事制造唯美的背景。后期導演俞飛鴻由于不滿拷貝色彩質量推遲影片上映,這都體現了制作者的創作誠意。而影片的制作的確達到了預期效果,對觀眾形成強烈的審美沖擊。
然而我們看到,當下華語市場中對視覺形式的強調成為獲得票房的一種捷徑。例如分別在2009和2010年票房大熱的女導演之作《非常完美》和《杜拉拉升職記》,前者的幕后制作堪稱國際水準,運用了大量二維手繪動畫、三維動畫、FLASH等影視特效,場景設計、道具運用、演員造型在當下浪漫愛情題材類作品中華麗程度首屈一指。由徐靜蕾導演的《杜拉拉升職記》則號稱是中國內地版的《時尚女魔頭》,影片所選取的全球跨國公司這一背景對普通觀眾本就是一處激發窺視欲與好奇的場域。影片聘請好萊塢著名的形象指導,不厭其煩地更換主要演員的大牌服飾,在霓裳靚影中完成了主角由職場菜鳥到高級經理人的蛻變,成功地使觀眾獲得了對跨國公司職場生活的想象性參與快感。
可以說女性導演對視覺形式的利用符合消費社會人們對符號消費的欲望。正如波德里亞所言“流通、購買、銷售,對作了區分的財富及物品/符號的占有,這些構成了我們今天的語言、我們的編碼,整個社會都依靠它來溝通交談。”[9]一個以消費為旨歸的符號系統,通過對消費者潛在的審美、幻想及享受的把握實現其價值的增殖。然而把作為“想象的能指”的電影符號當成激發觀眾官能快感和欲望滿足的手段,在某種程度上削弱了電影的敘事表達和審美內涵。在這類電影華麗視效的背后看不到女導演對于自身性別處境的任何表述。從實質上講,《愛有來生》、《非常完美》、《杜拉拉升職記》與男性導演制作的大場面大投資的奇觀電影沒有任何區別,只不過女性導演對愛情題材把握更為熟稔,對情感體驗更為獨到細膩。女性天生對視覺形式的敏感為這類電影的形式美提供了保障。然而褪去精致的特效和華服,女主人公們仍然被束縛于男權文化構建的社會性別身份之中。“消費是一種主動的集體行為,是一種約束、一種道德、一種制度、它完全是一種價值體系,具備這個概念所必需的集團一體化及社會控制功能。”[10]可見消費作為一種價值體系已將女性的身體魅力和性別魅力轉換為具有交換價值的符號,并通過一定的審美形式實現其價值最大化。
五、結語
新世紀以來,女性在電影創作中再次成為一股生機力量,在中國電影日益市場化商品化的今天,體制以外的女性創作能夠獲得一定的票房收益并形成良性產業鏈正體現了時代的進步和電影發展的多元化。但是女性導演在面對激烈票房爭奪的同時,其女性意識的缺失無疑降低了電影藝術品格,從另一層意義上,是對電影作為文化現象其內在反思性的主動剝離。本文依據《愛有來生》這部具有代表性的女性導演之作,分析了女性主體意識的缺失,并期待中國電影中有更多關注女性主體身份、女性生存境遇的自覺之作。
[1[澳]理查德?麥特白.好萊塢電影——1891年以來的美國電影工業發展史[M]吳菁、何建平、劉輝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5
[2][3][4][6][美]勞拉?穆爾維.視覺快感與敘事性電影[M]周傳基 譯 北京:三聯出版社,2006
[5]戴錦華 電影理論與批評[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7
[7][8]戴錦華 霧中風景—中國電影文化1978—1998 [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
[9][10][法]讓?波德里亞 消費社會[M],劉成富、全志剛譯 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