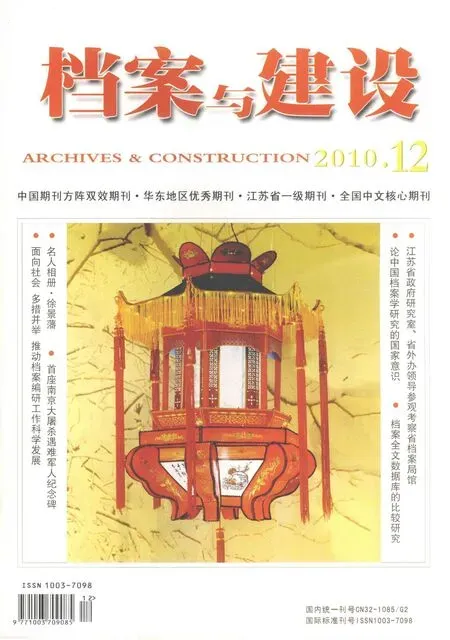首座南京大屠殺遇難軍人紀念碑
□孫宅巍

近年來,新聞媒體向社會報道了南京“抗日粵軍烈士墓”之碑的相關信息。筆者根據該碑碑名及碑文的內容考證,此座紀念碑應是遍布南京城內外20余座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碑中的首座南京大屠殺遇難軍人紀念碑。
紀念碑建立經過
抗日粵軍烈士墓碑位于南京中央門外張王廟40號“廣東山莊”墓園之中。廣東山莊為廣東同鄉會、兩廣會館,初創于清道光年間,由旅居于南京的廣東籍人士募捐購置,名為“山莊”,實為公墓,距今已有近200年歷史。莊園中埋有眾多旅居南京之廣東籍人士,包括民國時期政界商界一些有影響的人物,其中不乏亡故軍人。
據該山莊負責人介紹,1937年“八一三”淞滬抗戰中,粵軍傷兵運至南京后,住在城南八府塘后方醫院,廣東同鄉會及社會各界咸前往慰問,后部分傷兵傷愈出院,還剩一二百人留院繼續治療。城陷前,后方醫院屢遭日機轟炸,有50余名粵籍負傷軍人遇難。這批遇難的粵籍軍人經同鄉會義工收尸,被安葬于廣東山莊墓園中,并一一記錄有他們的姓名與部隊番號。12月13日,日軍攻陷南京后,對南京軍民進行了駭人聽聞的瘋狂屠殺,又有住于后方醫院的近20名廣東籍傷兵慘遭殺害。他們的遺體被掩埋于廣東山莊內。①
1941年初,依傍金川河的廣東山莊被日軍渦川部隊霸占。后經廣東籍人士與日軍當局多方交涉,方被迫遷移至中央門外現址。遷址后的廣東山莊占地約1.9萬平方米,園內樹木蔥蘢,花草繁茂,基本保持了原有的風貌。大門為一青磚砌成的高大厚實門樓,中有拱形大門,氣勢宏偉。門楣處保留了江蘇督軍齊燮元于1924年題寫的“廣東山莊”四個大字。大門外有兩尊石獅分立左右。大門右側有一塊遷墓理事會于1941年10月所立遷墓紀念碑,上書:“本莊舊址在城內三牌樓。于民國三十年被日本渦川部隊征用,遂募資購地移建于此。”遷移中,一些殮有遇難者的棺木也一并移此。對于這批慘遭日軍殺害的遇難官兵,廣東同鄉會每年都要舉行公祭。抗戰勝利后,粵軍部隊曾專程前來祭掃,并立有“抗日烈士之墓”的碑刻。
“文革”期間,墓園中這批遇難官兵的資料被毀。1997年,復將在南京大屠殺中遇難之官兵的74具遺骨加以清洗、消毒,重新歸葬于一處。2000年12月,重建烈士墓園,并立“抗日粵軍烈士墓”碑。
重建后的烈士墓園,位于山莊最北端的莊園深處,坐北朝南。全墓呈椅狀,以青灰色為其基本色調。椅背與兩邊扶手的頂部,均為半園形波狀紋,似有無數花圈簇擁。墓地設有7級臺階,拾級而上,于墓地正中,矗立一方尖形柱狀墓碑,碑的正面自上而下書寫著“抗日粵軍烈士墓”7個鎏金大字,碑座為黑色,椅背處為一長方形黑色大理石,上書金色繁體紀念碑文。墓園之整體設計氣勢恢宏,莊嚴肅穆,給人以無限的思念與遐想。
碑文的標題為:“先傷后亡,驚怒吾邦。無以厚葬,是為國殤。”碑文曰:
一九三七年,爆發震憾(撼)中外“八一三”淞滬抗戰之役。我粵健兒浴血奮戰,傷亡甚為慘烈。傷者多留醫南京城內八府塘后方醫院。是年十二月十三日,日寇攻陷南京,留醫傷者均遭屠殺,其后由廣東同鄉會率人草草掩埋于山莊內。公元二OOO年七月,為弘揚中華民族精神,振奮后人,經廣東山莊理事會研究,籌資重建烈士陵園以慰先驅。
抗日粵軍無名烈士永垂不朽。
公元二OOO年十二月重建需要說明的是此碑文內容較為籠統,對烈士數字與死難情況并未細說。根據前述廣東山莊負責人的介紹,新建墓園中埋葬的應為74具烈士遺骨,包含1937年南京淪陷前日機空襲中被炸身亡的50余名住院傷兵,及南京城陷后遭日軍屠殺的近20名傷兵。
遇難粵軍的相關資料
廣東山莊為抗日粵軍烈士墓的重建,做了大量的工作,作出了可貴的努力。但令人遺憾的是,這些遇難粵軍傷兵的資料,包括他們的姓名、部隊番號,均在“文革”中由于特定的歷史背景,已被銷毀殆盡。現今紀念碑與烈士墓園的建立,主要只是依靠了人們記憶的傳承。這就給史學界提出了一個任務,即從相關的新聞報道、歷史檔案中去搜尋與還原這一段已被湮沒了的日軍暴行歷史。
經過學術界多年來的努力發掘與開拓,如今有關日軍南京大屠殺暴行的史料已經比較豐富和充實。在這個基礎上,與本文相關的幾個關鍵詞,即“粵軍傷兵”、“八府塘后方醫院”、“日機轟炸與暴行”等,也都有相當豐厚的資料可以為之詮釋。

1.粵軍傷亡情況
參加南京保衛戰的粵軍部隊有:以葉肇為軍長的第66軍,下轄第159師與第160師;以鄧龍光為軍長的第83軍,下轄第154師與第156師。
第66軍自1937年9月下旬起編入第19集團軍薛岳所部的序列參加淞滬抗戰,11月上海失陷后,又先后轉戰于吳福線與錫澄線,經由句容、丹陽等地,撤至南京外圍,參加南京保衛戰。該部在淞滬地區及滬寧沿線的作戰中,歷經猛烈戰斗,傷亡甚巨。據第160師戰斗詳報記載:
本師自加入上海方面以來,即轉戰于劉行、廣福、南翔、周家笪地區,凡兩閱月。至十一月十一日,奉命撤退時,又因友軍掩護不力,以至在安亭之徐公橋附近受敵襲擊,損失奇重。后復奉令占領港田里、九謙橋之線,掩護我軍占領吳福國防工事線,隨又奉令占領原線,掩護全軍總退卻。至十一月十八日晚,奉令撤回洛社鎮,立足未定,又復奉令開錫澄線,占領石塘橋、長壽鎮、郁家橋之線。當時收容所得全師戰斗員兵不足三千,雖自十一晚由前線撤退以來,日夜未停,絕無整理與補充機會,因此實力大減……②
該師之第959團,僅在11月30日守衛丹陽陣地的戰斗中,即傷亡連排長4名、士兵110余名;該師之第959團、955團于12月7日在句容的突圍戰中,又傷亡軍官10余員、士兵300余人。③
第83軍于1937年10月組建于淞滬抗戰期間,組建后其第154師即在滬地參加了戰斗;其第156師于11月中旬由漢口東下,次第抵達蘇州、江陰,先后歸入第19集團軍薛岳部與江防部隊劉興部,參加了無錫、鎮江附近的阻擊戰斗。該軍撤退至南京后,兩師分別在水西門、光華門一帶參加戰斗。據該軍參謀處長劉紹武回憶,第156師在光華門曾進行了異常激烈的戰斗。“光華門不斷受敵人飛機、大炮的集中轟擊,城墻數處被毀”,“該師經多方苦戰”,“傷亡頗重”。④
上述資料證明,曾經參加南京保衛戰的兩支廣東部隊,在淞滬抗戰及保衛南京的戰斗中,確曾進行了英勇的戰斗,付出了極大的犧牲。其大量負傷官兵,除直接移送江北及大后方外,一部分被設在南京的后方醫院暫時收治,當為適應戰況、合乎情理的舉措。
2.八府塘后方醫院
南京城陷前,共有8所部隊醫院,負責收治傷病軍人。其中位于城東南的八府塘后方醫院院長為杜寶忠。據城陷后曾留京三月的野戰救護處科長蔣公榖記述:12月9日,“杜院在八府塘,已遭到了敵彈的轟炸,決令各醫院集合在外交部及軍政部二處,把職務劃分開來合并收容”。“祁院、杜院、李院集結外交部,冷院、尤院、鄧院集結軍政部,合處辦事,分負職務。”⑤于是,八府塘后方醫院院長杜寶忠便與第123醫院院長祁明鏡以及李義璋院長三人,各率本院人員遷往外交部集結。此時留在南京城內各部隊醫院中的傷兵共約300名。
南京城陷后,這批因負傷失去了戰斗力的傷兵,隨時都可能遭到日本侵略軍的屠殺和傷害。這時,他們的命運受到了以拉貝為主席的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同情和關注。為了保護和照料他們,外僑們特地爭取到了特殊經費,建立了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分會,由馬吉牧師擔任該會主席,該會的成員、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教授魏特琳女士在日記中寫道:“(12月13日)貝茨大約在11時過來,他說國際紅十字會已經得到了5萬美元,用以建立傷兵醫院,第一所醫院將設在外交部。已經組建了一個17人的委員會。”⑥
在中方衛生部門和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合力運作下,八府塘后方醫院的傷員遂被移送到外交部臨時傷兵醫院中。
3.日機轟炸與暴行
南京城陷前,日機在對南京的空襲中,慘無人道地實行了無差別的轟炸,其目標包括醫院與人口稠密的居民區,使大量和平居民與傷兵慘遭傷害。
八府塘后方醫院所在的城東南八府塘地區,曾多次遭到日機的大規模轟炸。8月15日,日機首次空襲南京。在來襲的27架敵機中,有18架竄入市區上空,對大校場、明故宮機場和八府塘、中山東路、大行宮等居民稠密地區進行狂轟濫炸。9月25日,日機對南京進行了空襲以來最大規模的一次轟炸,共有96架飛機分5批來襲。其轟炸目標除廣播、通訊設施外,便是醫院衛生機構和居民住宅區。
八府塘及其附近的白下路再次遭炸。南京大屠殺目擊證人李畹芳老人在一份證詞中說:“一九三七年八九月份,日本飛機經常來轟炸,炸彈投到大中橋八府塘一帶,市民恐慌,紛紛外逃。”⑦八府塘被轟炸的慘狀,令人目不忍睹。據描述:“在那里,死的人的衣服被炸飛在樹枝上,墻壁上血肉狼藉,有的房子燒了,有的房子倒了,缺胳膊少腿的人送到馬林醫院(鼓樓醫院)去了,活下來的人呆頭呆腦,欲哭無淚。”⑧可以想見,后來被埋葬在廣東山莊的50余名因空襲而犧牲的廣東傷兵,應當是八府塘地區屢遭轟炸而遇難軍民中的一部分。
經過數月日機轟炸劫難的八府塘后方醫院廣東傷兵,在南京城陷前后,被集中轉移到外交部,作臨時安置。但由于兵荒馬亂,硝煙彌漫,再次面臨兇殘日軍的任意屠殺。這種混亂和危險的狀況,使一部分傷兵一度不敢回到外交部的臨時安置點。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主席拉貝在12月13日的日記中寫道:
委員會的3個成員乘車前往設立在外交部、軍政部和鐵道部的幾所軍醫院,通過他們的巡視,我們確信了這幾所醫院的悲劇狀況……我們迅速弄來了一面紅十字旗掛在外交部的上空,并召回了相當數量的人員,他們在看到外交部上空飄揚的紅十字會旗后才敢回到軍醫院。外交部的進出口道路上橫七豎八地躺著傷亡人員。院內和整個中山路一樣滿地拋撒著丟棄的武器裝備。大門口停放的一輛手推車上擺放著一堆不成形的東西,仿佛是具尸體,露出的雙腳表明他還沒有斷氣。⑨
拉貝日記的內容揭示了被集中到外交部等臨時軍醫院的傷兵們的悲慘狀況,他們中的一部分在轉移中慘遭日軍殺害。對于日軍的兇殘暴虐,直接負責轉運傷兵的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分會主席馬吉有著親身的感受。他在一封致夫人的信函中敘述:12月16日,“我帶著滿載傷員的救護車到外交部,當我們設法使能走動的傷員朝臺階上走的時候(另一些用擔架抬),一隊日本兵來了,其中有些像是野獸。我正扶著一名可憐的傷兵,他痛苦地向前邁步,一個日本兵把他從我身邊拖開,猛地扭他受傷的膀子,把他的手捆在一起,并把另一名傷員的手也捆在一起。”⑩顯然,在這些日本士兵的眼中,已經受傷住院的中國軍人,仍然是他們任意拘捕、殺戮的對象。
遇難軍人紀念碑的價值
“抗日粵軍烈士墓”碑既是首座南京大屠殺遇難軍人紀念碑,也是到目前為止,南京市唯一的一座南京大屠殺遇難軍人紀念碑。這一紀念碑的設立與重建,具有重要的價值與意義。
前期建墓立碑,具有特殊的歷史價值。這批遇難軍人,在南京淪陷前后即立有單人墓碑;抗戰勝利后,粵軍部隊專程前來祭掃,改立集體無名墓碑。追溯此墓碑建立的歷史,應屬前期遇難同胞紀念碑。而在南京現存的20多座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碑中,大多數系1985年由南京市政府所建,其后又分別由公、私單位陸續建立了一部分。似該碑具有如此長久歷史淵源者,尚屬罕見。建墓立碑的久遠歷史,使這座墓碑包涵了深厚的歷史積淀,深深地打上了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時代烙印,為研究那個時代人們的心理、觀念與精神,提供了依據。
單一的遇難軍人紀念碑,具有獨特的群體意義。環顧先后設于南京城內外的20余座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碑,除“抗日粵軍烈士墓”碑外,莫不是軍民混處或僅為附近村民者,唯此碑所紀念者,全系在南京大屠殺暴行中遇難的軍人。軍人是一個獨特的群體。他們非陣亡于交戰的陣地上,而是罹難于受傷后住院治療的醫院中。為他們單獨建墓立碑,既彰顯了軍人在南京保衛戰中的付出與貢獻,更暴露了日軍無視國際公法,任意屠殺負傷軍人的殘暴行徑。
單一的廣東籍遇難同胞紀念碑,具有特定的地域象征意義。由于南京地處我國東南水陸路交通樞紐位置,民國以來又長期作為國民政府的首都,成為重要的政治、經濟、軍事與文化中心,從而眾多外省人士因各種原因,長期生活在南京或死后葬在南京。尤其是作為南方發達省份的廣東省,與南京的關系更為密切。在南京,能夠顯示廣東地域象征意義的機構與景物,有廣東同鄉會、兩廣會館、廣東醫院,以及莫愁湖畔的建國粵軍陣亡將士墓碑、廣東山莊的粵軍抗日烈士墓碑等。粵軍抗日烈士墓碑是抗戰歷史中廣東軍人為保衛南京、保衛國家而英勇獻身的標志,也是侵華日軍在南京大屠殺中殘暴屠殺外省、外地中國同胞的明證。它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華民族在外敵入侵面前的強大凝聚力,反映了江蘇、南京與外省、外地同胞血濃于水的手足深情。這對于加強蘇粵兩省的經濟合作、文化交流,有著明顯的現實意義。
注釋:
①《“廣東山莊”抗日粵軍烈士墓為南京大屠殺又添新證》,《新華日報》2009年8月13日。
②③《陸軍第160師戰斗詳報》,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④劉紹武:《第八十三軍南京突圍記》,《南京保衛戰》,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250頁。
⑤蔣公榖:《陷京三月記》,《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料》,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68頁、90頁。
⑥[美]魏特琳:《魏特琳日記》,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90頁。
⑦朱成山主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幸存者證言集》,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407頁。
⑧張其立:《日寇對南京的空襲》,《南京史志》1987年特刊(總第25期)。
⑨[德]拉貝:《拉貝日記》,江蘇人民出版社等1997年版,第171頁。
⑩章開沅編譯《天理難容——美國傳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殺(1937-1938)》,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9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