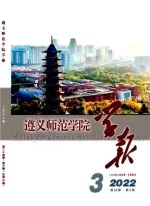論廖公弦詩歌“月”意象
麥成林
(貴州師范大學文學院,貴州貴陽550001)
論廖公弦詩歌“月”意象
麥成林
(貴州師范大學文學院,貴州貴陽550001)
廖公弦詩歌中的“月”意象,是他追求、探索的意象美學象征,也是營造詩歌意境的主要手段之一。“月”意象,一方面展示了田園式的意境,另一方面又充斥著不協(xié)調(diào)的政治話語訴求。同時,廖公弦在創(chuàng)作的不同時期,詩歌“月”意象內(nèi)涵也在無形中發(fā)生著變化。
《山中月》;月意象;田園牧歌;政治話語
在貴州的新詩詩歌史上,廖公弦是一個有力的存在。新時期以來,為方便當代文學的研究與教學,全國30多所高校中文系與中國社科院文研所協(xié)作,曾于上世紀80年代初編輯出版了一套《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資料》叢書,叢書為國家重點研究項目,由茅盾、周揚、巴金、陳荒煤、馮牧等人為顧問。其中貴州僅有的一冊只選了兩位作家——蹇先艾和廖公弦,書名為《蹇先艾廖公弦研究合集》。足以見得,廖公弦當時在貴州確實是最有影響力的作家之一。雖然他的詩歌并不多,留給我們的僅有四本詩集:《山中月》、《美人醒來》、《山與我們合影》以及20世紀90年代由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貴州文學叢書第二輯《廖公弦詩選》。但是其人在貴州的新詩史上有著難以磨滅的影響和光輝,尤其是他生活化的意象挖掘和田園牧歌式的意境營造,不失為一種純樸生活的自由點綴和無言的審美享受。其中有關“月”意象和意境的營造在《山中月》一集中多次出現(xiàn),這里“月”已經(jīng)成了表達感情,增強詩感的重要組成部分和有機結(jié)合體。月亮也不單單是思鄉(xiāng)懷遠的象征,更是山里人對一種生活方式的期許和對自然、生命的一種審美關照與對視。
蘇珊·朗格認為:“意象的真正的功用是:它可作為抽象之物,可作為象征,即思想的荷載物。”[1]當然在中國的古代詩詞中,詠月的篇章多如牛毛。月亮這種本質(zhì)的物質(zhì)存在已經(jīng)被賦予了豐富的美學內(nèi)涵和文化象征意義。在詩人的筆下,它不再是一種客觀關照物,單獨的客觀審美對象,更多的變成了承載和包含作者感受和經(jīng)歷的主觀化的抒情客體。同一輪月,此一時,彼一時,此一人,彼一人,他們都在構(gòu)造著不同的意境和審美感受,或思鄉(xiāng),或懷遠,或慨嘆,或傷情……而在廖詩中,月亮的靜謐,月亮的調(diào)皮,月夜的靜美,月色的朦朧,月亮和山里人的和諧關系,讓我們領略了“月”意象的另一種美。詩人從小生活在黔北綏陽的大山中,他在《談我寫詩》中回憶道:“我來自農(nóng)村。當我剛學會走路,便已經(jīng)是在外祖母家里了。那里的肥田沃野、茂林修竹,平緩的山丘,彎彎的小河,以及那些老實的牛、歡快的羊,從小就給我一種特定的詩的啟示。”廖公弦對月意象藝術美的追求,也帶有一種獨特的色彩,也是對月亮在新意境下承載意義的新的開拓。
在廖公弦薄薄的詩集《山中月》中,共收錄了詩人68首詩歌。這些詩歌絕大多數(shù)寫于1957至1964年間,只有開頭和結(jié)尾幾首寫于文革結(jié)束之后。總的來看,寫于50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的這些詩歌主要特點表現(xiàn)在以下三方面:首先,從取材范圍來看,均與家鄉(xiāng)的生活和勞動場景有關,充滿著泥土氣息,詩歌呈現(xiàn)出了山寨之美、山民之純,表現(xiàn)出濃厚田園牧歌的意蘊。其次,詩歌喜歡用大量的口語和通俗的語言入詩,既樸實自然,又不失活潑風趣,妙趣橫生。再者,詩歌兼收并蓄,善于從傳統(tǒng)詩詞和民歌當中吸收養(yǎng)分,充實自己的詩歌內(nèi)涵和增強藝術張力。詩集《山中月》中直接寫到月亮的就有五首:《晚安》、《編籮》、《山中月》、《雨后月出》、《月下曲》,其中屬《山中月》的影響最大,意境最美,該詩獲1961年《羊城晚報》創(chuàng)作獎,曾受到著名作家陳殘云的好評。這里“月”意象的營造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傳統(tǒng)詩詞中月亮所形成的原型意象的影響。本文就試從“月”意象的營造來反觀廖公弦詩歌創(chuàng)作的某些獨特表達方式和意蘊。
一、“月”意象的形態(tài)意象刻畫
月亮作為現(xiàn)實之物,我們是能夠看到月亮的實際輪廓的,當然常人眼中的形態(tài)感與詩人眼中的形態(tài)觀念是不可等同的。最重要的是詩人筆下的月亮或者月意象已經(jīng)承載了詩人的獨特審美想象和情感負載。根據(jù)詩歌表達的需要,對月亮進行情感化的處理。
這里的“形態(tài)”并非日常邏輯觀念中的月亮形態(tài),或圓或缺,而是借助詩歌的藝術表現(xiàn)手法將月亮賦予有形態(tài)的東西,或者說是直接觀念形態(tài)和意念的產(chǎn)物。例如詩歌《編籮》中開篇就寫到:“林里的夜風跑出來,/把槐樹兒輕搖輕搖,抖落些銀色的月光,/斑斑點點滿地跳/……拈起地上的月片/……扛鋤的人影竄過來,/滿背盡是月光跳……”[2]全詩月光貫穿始終,并且將月光賦予了有形的東西,像樹葉一樣可以搖落,像地上殘留的物體碎片,可以隨手拈起,還像扛起的重物在肩上亂跳。這樣生動的描寫,使詩歌本來靜態(tài)的文字表達,賦予了生物的動態(tài)感和生命力,進而使詩歌的意境活靈活現(xiàn)的展現(xiàn)在人們面前。“抖落些銀色的月光,/斑斑點點滿地跳”一句,是直接賦予了月亮“頑皮”的孩童形象,擬人化的效果躍然紙上,描寫山中的夜月,在樹林間仿佛過了濾似的,分外皎潔,投下了斑駁陸離的光影,境界顯得更加寧靜、和諧,和寂靜的山村一起營造了一副田園式靜寂鄉(xiāng)村月夜勞動場景的意境圖。月亮本是相對靜止的,但用一“跳”字,便將它寫得搖曳多姿起來:從夜風中探出頭來的月亮,把月光灑在槐樹上,這月光像給山村的夜蒙上了一層輕柔的白紗,晚風輕輕地撩撥著含羞帶嬌的白紗。樹在月光的映照下擺弄著嬌羞柔美的倩影,將“月”意象人格化了,富有了生命的質(zhì)感。
二、“月”意象在靜與動的互為辯證中的反襯比手法運用
詩人善于寫山中皎月,當然詩人筆下的月亮不同于海上明月的空曠,也不同于大漠邊塞夜月的孤獨與寂寥。《晚安》一詩中:
好一個靜謐的夜晚,/月亮跳進了秧田,/獨自兒悄悄洗澡,/洗掉那些銀色的鱗片//忽然間火星幾點,/迸濺在廣漠的夜間,/喓!是他呀,他銜著煙斗,/夜深了,未回還。//他在田野里走動,/眺望四周的群山,/群山變成了羊群,/馴服地躺在他身邊。//他一時時彎下腰去,/和秧苗握手傾談;/天上閃爍的星星,/齊向他眨著笑眼。//他那邁動的步伐,/走的多輕、多穩(wěn)健,/因為這安謐的山鄉(xiāng),/連同夢中的社員,/全睡在他的心間。//洗澡的月亮爬上田坎,/微風吹拂著霧中的遠山,/書記?,書記,/晚安!晚安……//[2]
詩中塑造了夜晚專心、認真、負責地查看秧苗的書記形象。為了烘托靜謐的夜晚,沒有直接地去寫夜是如此的空曠和寂靜,而是通過一系列的動詞“跳”、“洗澡”、“洗掉”、“爬”、“吹拂”等來寫月,靜靜的月亮,頓時“活”了,像一條活蹦亂跳的“銀魚”,進而以月亮的“動”襯托山鄉(xiāng)的“靜”,以月夜的“靜”反觀書記的專注和認真。這里的月成了勤勉書記形象的陪襯。
《山中月》一詩中,把“靜”和“動”反用的筆法達到了極致。特別是他的名作《山中月》,更受讀者群眾們贊賞。詩是這樣寫的:
傍晚出來,/依依回頭看,/明月與山民,/性格竟一般,/老在莊頭竹林后,/默默長相看,/回首不知多少次,明月未回還。/出山轉(zhuǎn)了彎,/上山復巔,/伴我下平川。//我走平壩,/月上中橋,/月涉澆水灘。/一而再,再而“山”/送我到明天。//山中月兒學山民,/感情也內(nèi)涵,/傾給滿腔熱情,/留給你幾多方便。/在它默默無言里,/你在不知不覺間。//[2]
“明月與山民,性格竟一般”一句,月亮成了山民的直接化身。[3]直接破題,點名主旨,直接了當?shù)赝侣冻鲈娙说男嫩E。從立意和構(gòu)思來看,詩人曾經(jīng)在《新詩我見》一文中說:“詩人要爭取讀者,讀者越多越好。故意把詩寫得晦澀、難懂,讓人費勁猜謎語,讀者越來越少,此種情況,無異于詩人自殺”。并明確提出:“詩要讓多數(shù)讀者看得懂”。[4]他對自己的詩作提出進一步的要求,在創(chuàng)作中力圖把中國祖?zhèn)鞯脑姼琛⒚窀韬驮~曲熔為一爐,愿能識漢字的人,都能看懂自己的詩。眾多人讀懂詩歌,并不等于降低詩歌的水平,而恰恰相反。詩歌要走出詩人狹小的圈子,成為廣大民眾樂于接受、易于理解的精神產(chǎn)品,就必須反對難懂的詩風,反對晦澀,提倡尊重民族的欣賞習慣。因此,他強調(diào)詩人要把握住詩歌的內(nèi)在規(guī)律,具有民族特色和個人風格。廖公弦的詩,易讀易懂,同時也含蓄耐爵,讓讀者把握意象、意境的同時,引發(fā)聯(lián)想、引人深思。
從詩歌的意境來分析,全詩以“我”的視角不斷游弋變化為中心點,借月展情,不斷地開拓新的意境和月亮的表現(xiàn)范圍。“我”上山,下山,月亮也陪我上山,下山;我走平壩,過峽谷,過中橋,明月夜悄悄地“上中天”、“站崖邊”、“涉淺水灘”。最后幾句,與開頭交相呼應,通過月之“象”,鮮明的表現(xiàn)出月之“神”。這何曾單單寫月,分明是在寫人,同時通過近似通感的表現(xiàn)手法將這種“象”和“神”直接地嫁接到山民身上來,將山民的那種勤勞、熱誠、質(zhì)樸、厚重的山里人品格和月的皎潔、純瑕、靜美對應了起來。這里月“活”了,不僅“活”的生機,而且極富山民的性格和大山的精魂。詩中賦予月完美的藝術形式,并活靈活現(xiàn)地刻畫出了貴州的山、月與民的和諧統(tǒng)一的關系。
三、和諧“月”意境中的時代政治話語訴求
在《山中月》里面當然從詩歌中看到了不協(xié)調(diào)景象,那就是詩歌的功利性表現(xiàn)和強烈的政治話語訴求。因為前面已經(jīng)提到,這些詩歌全部寫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當時的政治環(huán)境和時代環(huán)境決定了詩歌必然要為其服務,實踐出“頌歌”時代的強音。《山中月》中諸篇,好多處出現(xiàn)“公社的土地”、“公社的麥浪”、“公社的莊稼”、“公社的鴨”、“社員”、“書記”,這些詞反反復復地在詩中出現(xiàn),以詩人的才學和修養(yǎng)而論,不可能出現(xiàn)這樣低級重復的錯誤。后來詩人自己也印證了這一點,1983年詩人的隨筆《談我寫詩》中寫道:“寫詩于我,時日不算短了。每一回顧,總覺背冷。從十九歲到現(xiàn)在,期間除去不準寫作的十一二年(文革期間,作者加),也有十四五個年頭。十多年來的詩作,數(shù)量不算太少,但在嚴肅的歷史面前,能經(jīng)受考驗,不會低下頭去的作品,實在是寥寥無幾。”仔細思之,方能理解詩人的苦衷和那個時代所有文學(包括詩歌)打上的“為政治服務”、“為工農(nóng)兵服務”的時代烙印。
在那個時代,“大凡寫山水風景詩,最懼被扣上‘無思想內(nèi)容’的帽子,于是乎不得已,硬加上‘公社’此類的詞兒,以示所謂‘時代精神’,免遭棍子。”[5]從這一點看出,因為時代政治環(huán)境的左右,詩歌的功利性話語就明顯增強,這就造成了很多詩歌缺乏美學深度。雖然詩人一直在嘗試和堅持著淺顯易懂的詩歌創(chuàng)作道路,但是具體的創(chuàng)作實踐深受時代環(huán)境影響,諸多詩歌為了表達時代的聲音,詩人在結(jié)尾處就直接點題,把自己的思想直接說出來,缺乏含蓄和深度,使詩歌的詩味也逐漸減弱。
從這一點我們可以明白,“十七年”的詩歌,在詩歌的理論和實踐價值上主要是以政治價值取代審美價值,特別是對詩歌政治功利性話語訴求表現(xiàn)的尤為明顯。詩的社會“功能”、詩歌作者的“立場”和思想感情的性質(zhì),是評斷詩人及其作品的首要標準。在這樣的社會背景和時代背景下,廖公弦的諸詩也表現(xiàn)出了相關的政治訴求。首先,詩歌正如賀敬之所說:“詩,必須屬于人民,屬于社會主義事業(yè)。按照詩的規(guī)律來寫和按照人民利益來寫相一致。詩人的‘自我’跟階級、跟人民的‘大我’相結(jié)合。‘詩學’和‘政治學’的統(tǒng)一。詩人和戰(zhàn)士的統(tǒng)一。”[6]在賀敬之看來,寫詩就是為人民的利益而戰(zhàn)斗,反對詩歌創(chuàng)作背離社會主義事業(yè)的方向。作為同時代的詩人廖公弦,他不可能不受這種思想影響,詩歌創(chuàng)作必然會不約而同的打上相同時代的政治烙印,踐行這種詩歌創(chuàng)作的觀念和主張。其次,作為貴州的詩人,廖公弦并不像其他高聲吶喊的詩人,這種政治話語那么直白,直接歌頌祖國啊、母親啊、社會主義呀等一系列民族國家的想象圖式。而是將該時代的政治訴求轉(zhuǎn)移到農(nóng)村生活現(xiàn)實中去,將“公社”、“社員”、“書記”等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和物象寫入詩歌,間接上是為歌頌社會主義、人民公社、中國共產(chǎn)黨等功利性訴求服務的。所以說廖詩月意象的不協(xié)調(diào)景象是符合社會主流思潮,具有一定為政治服務的性質(zhì)。廖詩的詩歌的政治功利性話語訴求,是符合主要價值取向需要的,而且,該詩也彰顯了時代色彩,它向人們描繪了人們對特定時代的看法。這一點也充分說明,只有站在時代的高度,掌握時代的脈搏,才能成為廣大人民所歡迎的詩人。
總之,廖公弦詩歌政治功利性和十七年詩歌創(chuàng)作的審美要求標準是相符合的。集中表現(xiàn)在兩個方面:一是深入生活,緊緊把握時代的主旋律,這是詩歌健康發(fā)展的方向;一是堅持不懈地貫徹雙百方針,促進民族化大眾化和個人風格多樣性的統(tǒng)一。只不過,廖詩在把握這樣創(chuàng)作路線的同時,不斷地探索自己獨特的創(chuàng)作方法和理念。
四、“月”意象在文革前后詩歌中內(nèi)含的轉(zhuǎn)變
縱觀廖公弦的整個創(chuàng)作,前面已經(jīng)提到《山中月》里面的大部分詩歌都寫于文革前期,當然這幾首與“月”相關的詩歌也出自該時期。在新時期之后,廖公弦的詩歌里也有意象出現(xiàn),但是已經(jīng)不是早期的韻味和情景。這說明隨著時代的變化和詩人心境的變化,詩人的創(chuàng)作審美關照也在悄悄地改變。“月”意象的審美趣味也在轉(zhuǎn)換。例如《上海之夜》中的兩節(jié)是最能體現(xiàn)這種轉(zhuǎn)變的:“新月來到高樓邊,/寂寞里透露出凄涼,/抬頭看她一眼,/總覺又瘦又黃。/不懂事的霓虹燈/——那些燈的姑娘,/竟對月亮眨笑眼,/炫耀彩色的衣裳。//勸你月亮回山去,/不必隨在我身旁。//”[7]
這短短的兩小節(jié),把完全不同的月亮已經(jīng)呈現(xiàn)在我們面前。這里的月亮已經(jīng)沒有原來“山中月”的皎潔、明亮、溫馨、靜寂和閑適等情景,而變的“寂寞”、“凄涼”、“又瘦又黃”,完全沒有原來詩歌中月亮溫暖的詩意。同時,還拿城市的燈光和月亮之光進行了強烈的對比,從五顏六色的霓虹燈到花枝招展的姑娘,全都在暗示著“月亮”的“土氣”和不協(xié)調(diào)。所以詩人最后才發(fā)出了“勸你月亮回山去”的呼聲。
從表面上看,詩人是拿兩種燈光作比較,其實,兩種燈光是“城市”和“農(nóng)村”的兩種關照的對應處理。城市的霓虹燈下,出現(xiàn)的是紙醉金迷、五顏六色和強烈的喧嘩及浮躁,而月光關照下的鄉(xiāng)村是一派靜寂的田園,具有月光般的淳樸、厚實和恬靜。從此可以看出,詩人通過月意象的營造,將城市和鄉(xiāng)村的巨大差異性表現(xiàn)出來。同時從某種程度上來看,月亮簡直就是詩人自己的化身,詩人“勸月亮回去”,實際上在勸自己回去,暗示自己,自己不屬于上海這樣的大都市,自己的出現(xiàn)與大都市的繁華是不協(xié)調(diào)的,只有回到自己的山鄉(xiāng),月亮才有那么美妙的意境。
簡而言之,雖然作者此時已經(jīng)定居貴陽,但對于上海來說,仍以鄉(xiāng)下人的眼光關照自己和詩歌。以強烈的鄉(xiāng)村本位和排斥都市物欲文明的思想進行詩歌創(chuàng)作。他不著重刻畫鄉(xiāng)村的落后與悲慘,而是通過月意象表現(xiàn)鄉(xiāng)里人的淳樸和厚實。從本首詩看,詩人其實是拒絕都市文明的,尤其是發(fā)達的城市物質(zhì)文明,充滿了塵世的喧囂,這是作者不樂意看到和融入的。同時,如果把這首詩納入作者的城鄉(xiāng)關照思想體系,或許從側(cè)面也能印證詩人筆下月意象其實是山里人生活的自由點綴和浪漫想象的載體。
在廖公弦的創(chuàng)作視野中,月亮不再是一種無知覺的本然存在,而是做為一種有生命體,或是山民的象征而出現(xiàn)的,其筆下的月意象有詩情、近生命,無不滲透了詩人的情感和追求,澎湃著詩人田園牧歌式空靈與思考,點綴著大山中那些自由浮動的靈魂。詩歌的月色意境,不是憑空冥想出來的,而是從生活中來的。詩人從小在黔北綏陽的大山中,詩人在《談我寫詩》中回憶道:“我來自農(nóng)村。當我剛學會走路,便已經(jīng)是在外祖母家里了。那里的肥田沃野、茂林修竹,平緩的山丘、彎彎的小河,以及那些老實的牛、歡快的羊,從小就給我一種特定的詩的啟示。”這種對于人生的深刻記憶強烈地影響了詩人以后的詩歌創(chuàng)作,月意象當然也是對山里生活記憶的挖掘和升華。通過對月意象藝術美的追求,將月亮在新意境下承載意義的范圍進行新的拓展。
綜上所述,廖公弦詩歌在特殊的時代、特殊的時代環(huán)境中詮釋了“月”意象別樣的美學內(nèi)涵和情感表達。這種詮釋跟詩人們在不同的人生際遇中對自我的情感體驗有關,而這種情感體驗的內(nèi)涵是對自身生活的期許和心靈的關照。
[1]廖玉萍.水意象:觸動心靈的弦索——論徐志摩詩歌中的水意象[J].作家作品研究,2007,(05):94.
[2]廖公弦:山中月[M].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78.34-35,28-29,68-69.
[3]廖公弦.新詩我見[J].詩刊,1982,(01).
[4]張勁.簡論廖公弦的抒情詩[J].貴州社會科學,1980,(03).
[5]梅翁.閑話“山中月”[J].花溪,1980,(02).
[6]賀敬之.賀敬之談詩[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89.
[7]廖公弦.廖公弦詩選[M].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4.50.
(責任編輯:魏登云)
On the Image of"Moon"of Poems by Liao Gong-xian
MAI Cheng-Li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Guiyang 550001,China)
The image of"moon"of the poems by Liao Gong-xian,a means of creating poetic imagination,is the esthetic symbol of image he pursues and studies.The image of"moon",on the one hand,can show us an idyllic imagery,and on the other hand,it is shot through with inharmonious political complaints of discourse.Meanwhile,the connotations of the image"moon"vary at different phases of creation of poems by Liao Gong-xian.
moon in the mountains;moon image;idyllic songs;political discourse
I207.22
A
1009-3583(2010)-04-0036-04
2010-04-12
貴州省教育廳人文科學基金項目“從新時期到新世紀:貴州新詩30年”(08JD015)和貴州省優(yōu)秀科技教育人才省長資金項目“大西南文化與貴州20世紀新詩研究”(黔省專合字[2009]112號),項目主持人:顏同林教授。
麥成林,男,河南洛陽人,貴州師范大學文學院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