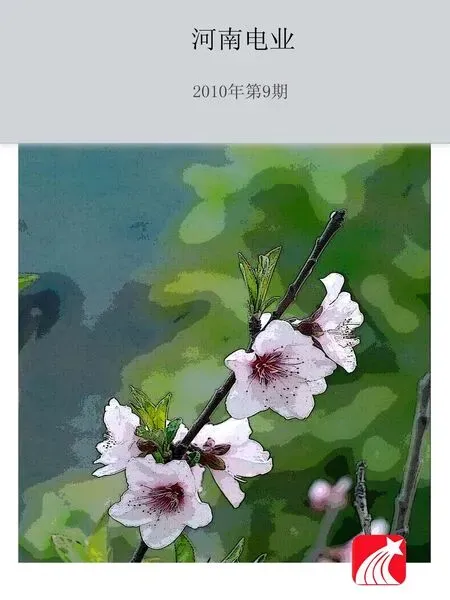中岳嵩山:理性綻放的花瓣
_寇寶剛

1.觀星臺(tái)
嵩山如臥。和其他四岳的如坐、如立、如行、如飛相比,臥是更沉穩(wěn)的姿態(tài)。因而,嵩山就奧。山大多以雄、秀、險(xiǎn)、奇為著,這奧用于山,平添了幾分厚重和神秘。
嵩山橫臥于天地之中,不僅僅是供人們觀賞和朝拜的,更是思想的誕生地,是理性思考的搖籃。
源于嵩山的禪宗和理學(xué)廣為流布數(shù)百年以后,元代的郭守敬以天文學(xué)家的身份,在嵩山南麓的一塊空地上,建立了一座觀星臺(tái),用當(dāng)時(shí)世界上最先進(jìn)的方式,來為天地空間和時(shí)間建立一種秩序,以歷法的形式,固定我們的每一個(gè)日子。郭守敬在全國建立了27座這樣的觀星臺(tái),這一座的獨(dú)特不在于它是現(xiàn)今唯一的存留物,而是它居于人們觀念中的天地之中的位置。在當(dāng)?shù)兀藗儼堰@座臺(tái)子叫“量天尺”。郭守敬認(rèn)為,“歷之本在于測(cè)驗(yàn),而測(cè)驗(yàn)之器莫先儀表”。在觀星臺(tái),郭守敬發(fā)明和制作的天文測(cè)驗(yàn)儀表已經(jīng)蕩然無存,只剩下一座青磚壘砌的臺(tái)子,我們無論如何也想象不到當(dāng)年他是怎樣對(duì)沒有邊際的天來測(cè)量的。那一定是一套繁雜而系統(tǒng)的測(cè)量方法。正是郭守敬對(duì)“天”的精確測(cè)量,才發(fā)現(xiàn)沿用了600多年的祖沖之算定的歷法存在明顯的誤差。郭守敬的《授時(shí)歷》確定每年365.2425天,與現(xiàn)行公歷相差無幾。這一歷法襲用了360年,經(jīng)由徐光啟進(jìn)行了新的測(cè)算和修訂。觀星臺(tái)確立的是每個(gè)日子在宇宙中的位置,仿佛讓人們看清了未來的日子。
郭守敬在這里丈量天地,推演天文義理的650年前,禪宗始祖達(dá)摩來到嵩山,在一個(gè)山洞里面壁悟道,揣摩著安頓人心的修煉法門。天道人心,人心天道,也只好由嵩山來承載這份沉重。
達(dá)摩面壁9年修煉的山洞,在一處山的高端。通往洞的山路盤繞崎嶇,沿途及洞的周邊沒有可觀的景色。嵩山本來就不是賞景的山,它更適合思考。湊巧的是,思考的背景都定格在了茫茫大雪之中。
佛教的禪宗與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周易、老莊不謀而合,是悟中的體察。它一經(jīng)傳入,迅即本土化,傳布禪宗思想的《壇經(jīng)》是唯一的中國原創(chuàng)佛典。禪宗的“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是神性與詩性的高度融合,它的傳布卻充滿了血腥與神秘。
達(dá)摩面壁時(shí),始終有個(gè)身影相伴,那個(gè)人是禪宗二祖慧可。慧可原名神光,久居伊洛,他博覽百家,善談玄理,卻常常嘆息“孔老之教,禮術(shù)風(fēng)規(guī);莊易之書,未盡妙理”。聽聞達(dá)摩在面壁悟道后,神光當(dāng)即前往求法,旦夕參拜。神光雖久執(zhí)弟子之禮,達(dá)摩卻只管端坐面壁,不聞不問,神光沒有氣餒,“昔人求道,敲骨取髓,刺血濟(jì)饑,布發(fā)掩泥,投崖飼虎。古倘若此,我又何人?”某一年的臘月十九,徹夜大雪,神光“堅(jiān)立不動(dòng),遲明積雪過膝”。達(dá)摩悲憫神光,開口相問:“汝久立雪中,何事相求?”神光頓下悲淚:“惟愿和尚慈悲,開啟甘露之門。”達(dá)摩說:“諸佛無上妙道,曠劫精勤,難行能行,非忍而忍,豈以小德小智,輕心慢心,欲冀真乘,徒勞勤苦。”神光聞此教誨,潛取利刀,自斷左臂,放在達(dá)摩面前。立時(shí),紅光彌漫周遭雪野。達(dá)摩覺得神光是個(gè)“法器”,賜名慧可,授以法衣。禪的立根,使?jié)h語里有了拈花微笑、一葦渡江這樣富有彈性和溫暖的語匯。宗白華說:“禪是中國人接觸佛教大乘義后體認(rèn)到自己心靈的深處而燦爛地發(fā)揮到哲學(xué)境界與藝術(shù)境界。”“人閑桂花落,夜靜春山空。月出驚山鳥,時(shí)鳴春澗中。”“行到水窮處,坐看云起時(shí)。”我們不一定去修禪練道,然而禪境卻是我們向往的至高審美境界。
“就某種意義說,更新的儒學(xué)(宋明理學(xué))可以認(rèn)作是禪宗思想合乎邏輯的發(fā)展。”馮友蘭的論斷,與嵩山有密切的關(guān)系。距“立雪斷臂”故事發(fā)生地不遠(yuǎn)處,還發(fā)生了“程門立雪”的故事。這場(chǎng)飄落在宋朝的大雪,差不多覆蓋了它以后的中國思想文化史。

2.嵩陽書院
現(xiàn)今的游人們?cè)卺躁枙憾几嗟谋粌煽脻h柏征服,感嘆生命的力量。而在書院的鼎盛時(shí)期,人們?cè)谶@里是被孔孟的思想所征服,感嘆它的博大精深。程顥、程頤兄弟先后在這里研究、講學(xué)10多年,成為理學(xué)的策源地。他們把“理”或“天理”視作哲學(xué)的最高范疇,認(rèn)為理無所不在,不生不滅,不僅是世界的本源,也是社會(huì)生活的最高準(zhǔn)則。存天理、滅人欲,天理是倫理道德的“三綱五常”,人欲是違背禮儀規(guī)范的行為,人們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就是人欲的表現(xiàn)。封建綱常與宗教的禁欲主義結(jié)合起來共同對(duì)人性進(jìn)行扼殺。
楊時(shí)的“程門立雪”,為這一理論的傳承提供了牢固的基礎(chǔ)。“程門立雪”前,楊時(shí)已經(jīng)是程顥的高徒。程顥死后,楊時(shí)在一個(gè)冬天前往嵩陽書院,再拜于此聚徒講學(xué)的程頤為師。這個(gè)福建人決意把“二程”的理學(xué)傳播到江南。一場(chǎng)大雪,并沒有感動(dòng)已是木石心腸的程頤。楊時(shí)見程頤時(shí),程頤“瞑目而坐”,等到“門外之雪深一尺”,程頤“醒”來,只輕巧地說了聲“日既晚,且休矣”。我們只看到了楊時(shí)拜見老師最初的情景,不知楊時(shí)又費(fèi)了什么周折,才拜在了程頤門下。只是隱約感到,“程門立雪”和“斷臂立雪”之間有一條通道,禪宗與理學(xué),意趣迥異,傳道方式竟是何其相似乃爾。禪宗是衣缽相傳,朱熹集理學(xué)之大成,一脈相傳,在很長時(shí)間里,成為統(tǒng)領(lǐng)國家的意識(shí)形態(tài)。
思想從來都不能被禁錮。同是禪宗,“時(shí)時(shí)勤拂拭,勿使惹塵埃”是一種境界,“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是又一境界。同樣,在程朱理學(xué)盛行的同時(shí),我們也聽到了陸九淵、王陽明、王夫之尖厲的反對(duì)聲音。
歌德說:“理論是灰色的,只有生命之樹常青。”禪宗與理學(xué)的深?yuàn)W義理自然還有人去理會(huì),但是,如睡的嵩山,應(yīng)該有更神奇的生命之奧。我們會(huì)時(shí)常對(duì)它回眸和關(guān)注,那是對(duì)自己靈魂的安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