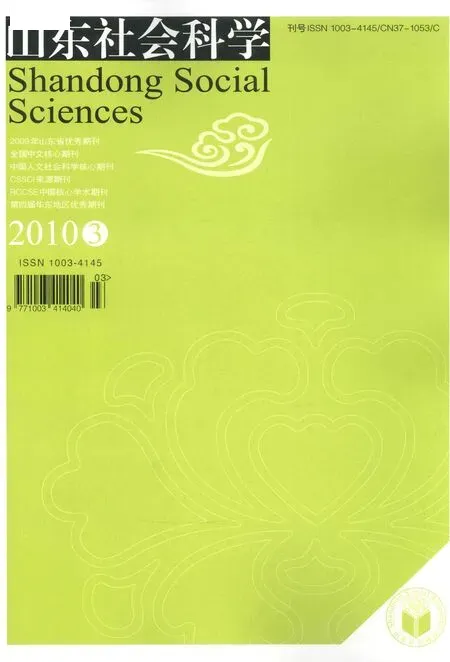競(jìng)技體育暴力行為的刑法解讀*
曲伶俐 吳玉萍
(山東政法學(xué)院刑事司法學(xué)院,山東濟(jì)南 250014)
競(jìng)技體育暴力行為的刑法解讀*
曲伶俐 吳玉萍
(山東政法學(xué)院刑事司法學(xué)院,山東濟(jì)南 250014)
競(jìng)技體育的暴力性和體育暴力兩者截然不同:暴力性是競(jìng)技體育的固有屬性,體育暴力則是競(jìng)技體育的異化。競(jìng)技體育暴力行為是指在正當(dāng)?shù)膶?duì)抗性體育比賽中,參賽的一方運(yùn)動(dòng)員以比賽為目的,故意犯規(guī)超過必要限度,故意造成另一方參賽運(yùn)動(dòng)員重傷或者死亡的攻擊性行為。針對(duì)目前競(jìng)技體育領(lǐng)域以行規(guī)代替刑罰而又收效甚微的現(xiàn)狀,刑法應(yīng)當(dāng)對(duì)競(jìng)技體育暴力行為予以規(guī)制。
體育暴力;刑法;概念;規(guī)制
體育運(yùn)動(dòng)自產(chǎn)生以來,在人們的生活中就占據(jù)著日益重要的地位。體育運(yùn)動(dòng)能夠強(qiáng)健體魄、愉悅身心、增進(jìn)友誼。當(dāng)人們陶醉在體育運(yùn)動(dòng)帶來的美妙享受的同時(shí),不可避免要受到其副產(chǎn)品——體育暴力的困擾。體育暴力伴隨著體育運(yùn)動(dòng)而產(chǎn)生,并隨著體育運(yùn)動(dòng)的發(fā)展而日益嚴(yán)重。二戰(zhàn)以后,體育暴力像一場(chǎng)看不到盡頭的瘟疫一樣席卷全世界,我國也不能例外。對(duì)競(jìng)技體育暴力行為這一社會(huì)現(xiàn)象進(jìn)行研究并采取措施予以規(guī)制,已經(jīng)成為體育學(xué)界及法學(xué)界亟待解決的問題。然而研究的現(xiàn)狀卻不容樂觀:體育學(xué)界的研究并不深入,刑法學(xué)界尚少人問津。本文擬對(duì)競(jìng)技體育的暴力性質(zhì)予以詮釋,對(duì)競(jìng)技體育暴力行為的概念從刑法的視角進(jìn)行界定,并對(duì)刑法如何規(guī)制競(jìng)技體育暴力進(jìn)行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