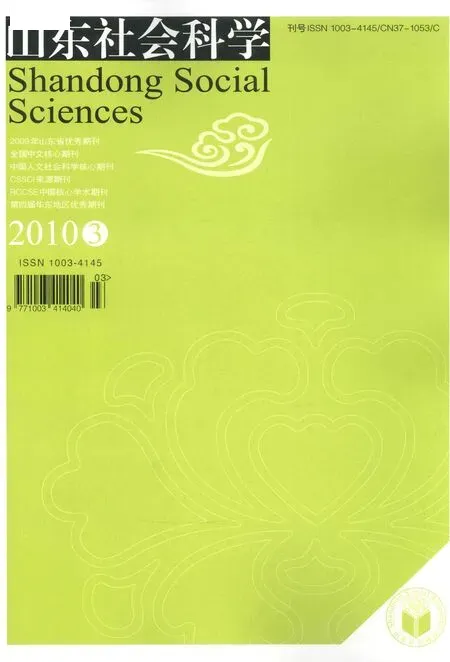中國現代文學史書寫向人本型轉換的探索過程*
2010-04-12 19:46:43朱德發
山東社會科學
2010年3期
朱德發
(山東師范大學 文學院,山東 濟南 250014)
中國現代文學史書寫向人本型轉換的探索過程*
朱德發
(山東師范大學 文學院,山東 濟南 250014)
新時期伊始至二十一世紀初葉,中國現代文學史書寫逐步突破政治理論框架和政治化寫作規范,經過艱難的探索,終于使政治型文學史書寫向人本型文學史書寫轉換;而這個轉型過程則呈現出“過渡”、“嘗試”、“拓展”三個邏輯階段,每個階段的人本型現代文學史書寫各有不同的突破點與創新點。
現代文學史;書寫;人本型;轉換過程
建國后的前三十年,中國現代文學史書寫,始終是在教育部制訂的教學大綱規范與框定下運作的,大都為高等院校文科教學而編寫,即使五十年代王瑤本、丁易本、蔡義本、張畢來本、劉綬松本等現代文學史的書寫出自個人之手,也是為了適應教學之需,可見高等院校文科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教學是推進文學史研究和書寫的內在動力。雖然“文革”十年正式出版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實為罕見,然而“復課鬧革命”的 1971年后,卻為給文科工農兵大學生授課不得不思考文學史的書寫,哪怕寫出的講稿不能公開出版也要嘗試寫些東西,如魯迅、樣板戲、《講話》、文藝思想斗爭等專題講義,無不運用“文革”思維來寫來講。當然偶而也運用鉆網戰術插進教師的獨立思考,而工農兵大學生則喜歡聽到一些異質聲音,這一方面說明即使“文革”這個學術有罪的特殊時期,一旦“復課”就會驅動教學主體去思索文學史的書寫;另一方面也說明歷史的曲折,正在醞釀和迎接新機遇到來時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書寫的大變革。……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