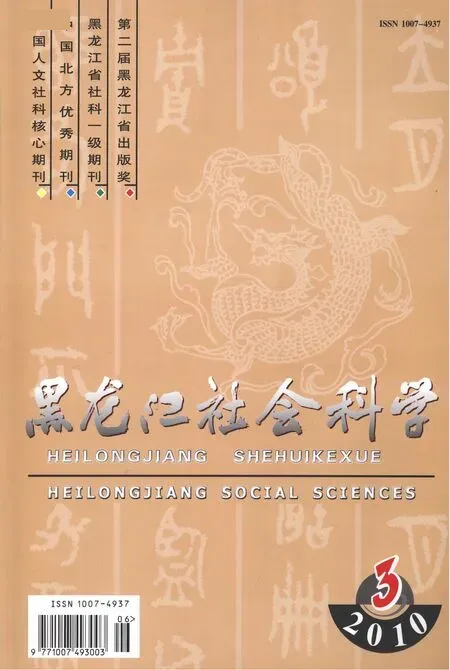從歷史角度看科學劃界
程曉皎,孫玉忠
(哈爾濱師范大學科學技術教育系,哈爾濱 150025)
從歷史角度看科學劃界
程曉皎,孫玉忠
(哈爾濱師范大學科學技術教育系,哈爾濱 150025)
劃界問題是西方科學哲學最基本的問題,劃界行為具有社會和政治后果。不考慮歷史維度的純邏輯研究割斷了科學的完整歷史,在理論上造成缺憾,并導致現實的困惑。西方科學哲學在劃界問題中走不出片面和困境的原因之一是他們混同了標準與判據。劃界標準立足于科學的本質,據此形成劃界的充分必要條件,但不能對此提出“足夠精確,便于操作”的要求。劃界的判據是具有可操作性的判定依據,在整體上體現出科學與非科學認識論意義上的差別。
科學劃界;科學判據;科學哲學
科學劃界問題是西方科學哲學最基本的問題。波普爾認為,科學劃界是“認識論的中心問題”,英國科學哲學家吉勒斯把劃界問題列為 20世紀科學哲學的四大主題之一。時至今日,劃界問題已不單單是科學認識領域的問題,劃界本身往往蘊涵著更為廣泛的問題,用吉勒斯的話說,劃界問題關系到超出科學王國之外的普遍知識的論題。邏輯經驗主義把劃界作為排除形而上學的手段,然而更多的是作為懷疑的手段。在我們今天的社會當中,劃界顯然更具有社會和政治后果。
一、劃界問題的歷史維度
1936年,一批“不具科學價值”的牛頓手稿被拍賣。隨著這些文件的曝光,作為科學家的牛頓的形象遭到質疑。這些文件顯示,牛頓在 1667年進入煉金術領域,1669年底開始煉金實驗。其后近三十年的時間中,牛頓投入大量的時間與精力從事煉金術的研究與實驗。他的收藏中有 169冊關于化學及煉金術的書籍,而他留下的有關煉金術的資料超過了 100萬字。有關煉金術,現代科學史上所認可的正面意義是,它催生了現代化學。而煉金術在完成了其歷史使命之后,由于其本身的非科學性也已成為科學史上的遺跡。然而,煉金術并不像人們想象的那樣,只是一些江湖術士的招搖撞騙,它在一定程度上與科學有著密切的關系。牛頓時代的煉金術包含三個領域,首先,煉金術聚集了大量的技術,包括顏料和染料的制造、無機酸的制造和水的蒸餾等,這些產品在當時已經有了商業用途。其次,作為早期科學的新領域之一的醫學曾是煉金術的分支。第三,從物質中制造黃金。就牛頓而言,他所從事的煉金術和物理學研究就其出發點和研究手段來說并無實質性的差別,他沉迷于煉金術的原因也不排除發現宇宙的真理。這或許可以部分地解釋與牛頓同時代的科學家摩耳、巴賓頓、巴羅、波義耳等人均癡迷于煉金術的原因。之所以這樣說是基于如下理由:一是可重復的實驗結果。在美國印第安那大學布盧明頓分校一個普通的化學實驗室,兩位化學家威廉姆·紐曼和凱瑟琳·里克“復制”了牛頓用于做實驗的儀器,依據牛頓手稿所描述的實驗,力圖在與牛頓相同的條件下重做煉金術實驗。按照牛頓的實驗方法,他們制出了被牛頓稱為“網”(net)的一種球狀物質。他們還利用牛頓的筆記重新制造了樹狀金屬結構,制造出這種結構對牛頓的煉金術研究有重要的作用。二是可解讀的符號體系。像其他煉金術士一樣,牛頓發明了自己的符號體系來描述他的實驗。他用行星符號來表示已知的金屬,用標準符號來代表一些普通的物質。除此之外,牛頓還創造了大量的非常個性化的象形符號。這些符號雖不正統,但均有明確的代表性。用來代表金屬礦石的符號比較容易對譯,今天的人們已經能夠知道其含義,但還有一些人們至今不知其含義。盡管如此,用符號來表示物質表明牛頓的研究在形式上已接近科學形態。
現有的劃界標準無法對煉金術進行結構上的分析,根據現有的標準我們會把這一時期的研究整體上判定為非科學,因為按照歷史主義的劃界標準,這一時期尚未形成科學范式。邏輯主義的劃界標準也對此無能為力。可檢驗性是邏輯經驗主義和證偽主義提出劃界的一元邏輯標準,標準雖然是一元的,但結構是二元的,即經驗—理論的二元結構。因為可檢驗性雖然是經驗的可檢驗性,但所檢驗的結論卻是來自理論。可檢驗性是指命題具有如下性質:可以從命題中推演出一個可與觀察、實驗結果相比較的推斷。因此,當我們面對煉金術并對其進行分析時會發現,雖然煉金術是非科學的結論,但將其宣判為非科學的理由卻掩蓋了有價值的思考,暴露出不考慮歷史維度的純邏輯標準的局限性,忽視了劃界帶來的社會后果。
此外,我們還必須對劃界問題進行歷史維度的思考。“所謂科學認識,其區分有兩個等級:整體的和個體的”[1]。科學劃界既針對科學的整體,也包括科學的個體。就科學的個體而言,其廣義的發展有三種情況:第一種情況是發生,即科學理論從無到有,從非科學領域進入科學領域。第二種情況是科學范圍內的發展,此時的科學活動表現為一種在現有的理論框架內解決問題的活動,用庫恩的話來說,即常規科學階段科學家在范式的范圍內從事解難題的活動。第三種情況與第一種情況剛好相反,科學個體的發展從科學領域走向非科學領域,進入到諸如哲學、神學以及其他的非科學領域。我們現有的科學劃界問題的研究不僅割斷了科學的完整歷史,而且對前科學時期分析的缺失也造成了理論上的缺憾,更給今天的現實分析帶來了思想上的不一致。如果我們對過去的歷史做事后分析,科學實踐的成功會決定我們作出的判斷。而在牛頓時代,科學與哲學、科學與神秘學的界限十分模糊,科學研究的探索本性更決定了他不可能在一個已經圈定好了的能夠通向成功的領域內去從事研究。科學研究的探索本性注定了研究道路的不可預知性,人們不會預先知道哪條道路能通向成功。
如果對當下的歷史進行分析,我們將如何對尚無法預測能否成功的實踐行為進行科學與非科學的劃界呢?按照現有的劃界標準,不具備系統知識形態(范式)的就是非科學,可在今天的現實中,一項有價值的探索性研究一旦被宣布為非科學或偽科學,就會徹底喪失社會的支持,這勢必會阻斷前科學通向常規科學的必由之路。
二、不能消解的劃界問題
目前,劃界問題的研究首先需要面對的是后現代主義頗具破壞性的沖擊。從實證主義正式提出劃界問題到社會歷史學派及其后來的發展,劃界問題經歷了三個轉變:從靜態標準向動態標準的轉變、從一元標準向多元標準的轉變、從有標準向無標準的消解。歷史主義準確地抓住了邏輯主義的要害,指出,無論是證實標準還是證偽標準都嚴重脫離和歪曲了實際科學,因而不可能對科學與非科學作出正確的區分。歷史主義雖然準確地揭示了邏輯主義的錯誤,但不能夠給出正確的解決方案,反而使劃界問題走向消失。
歷史主義之后對劃界問題的消解基于兩個前提:一是徹底否認現有劃界標準的合理性。二是拒絕承認科學與非科學的本質區別。勞丹就認為,自實證主義提出劃界問題以來,沒有一個劃界標準滿足了他所提出的三點要求,“不管人們如何區分科學與非科學 (例如根據進步性、合理性、經驗性、可證偽性),這些區分都經不起仔細推敲。”[2]196因此,也就不可能有效地分清科學與非科學。他還進一步指出,科學本身是異質的,它們不都是從認識中獲得的。科學本身的異質性決定了我們尋找劃界標準只能是徒勞之舉,因為“非科學與科學完全一樣,也有經驗問題和概念問題;二者均能表明在其歷史演化的某個階段取得了重大進步。”[2]196勞丹之后,羅蒂也站在后現代主義的立場上重申了劃界問題的消逝。
科學哲學作為對科學的反思和超越,其所研究的主要問題來自于科學理論和科學實踐中最普遍的問題,劃界問題也同樣如此。任何事物都是肯定與否定矛盾的統一體,異質不能替代本質,更不能消除差別。劃界標準的不成功不會迫使我們消解劃界問題。只要我們承認科學與非科學之間存在本質的區別,那么合邏輯的結論必然是承認科學劃界的存在,進而尋找劃界標準。理想的科學劃界建立在這樣一個基礎上——劃界標準的合理性和劃界判據的可操作性。
西方科學哲學在科學劃界問題的研究中走不出片面和困境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們混同了標準與判據。他們無法在最大的普遍性和現實的可操作性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結果是這兩方面都不令人滿意。以勞丹為例,勞丹認為劃界標準應滿足三個條件:一是能夠表明科學的認識論根據或證據基礎比非科學更加確定;二是能夠對區分科學與非科學的方式作出明確的解釋,并從認識論意義上表明科學與非科學的區別;三是足夠精確,便于操作[3]。從邏輯經驗主義到社會歷史學派以及后來的發展,沒有哪一個劃界理論不受質疑,更沒看到哪一個劃界理論在科學實踐中取得了壓倒式的成功。
科學的劃界意在把科學與非科學或反科學區分開來,其劃界標準顯示出科學與非科學或反科學的本質區別。在科學領域進行的劃界是人們運用一定的標準對知識領域進行的用以區分科學與非科學、科學與偽科學的一項活動。就其目的而言,科學劃界就是確定一個邊界,從而把科學與其他知識形式區分開來。這種區分關乎科學的本質規定,對“什么是科學”進行追問,據此形成劃界的充分必要條件。因此,不能對標準提出“足夠精確,便于操作”的要求。劃界的判據是依據劃界標準,并結合具體的科學實踐,判定科學行為和科學成果是否符合科學標準的具體的、可操作的判定依據。各種判據結合在一起,會在整體上體現出科學與非科學在認識論意義上的差別。每一條具體的判據都蘊涵著這種意義,但不能期待它來回答科學的認識論何以比非科學更加確定。
劃界的標準與劃界的判定不能混為一談。劃界標準與科學的本質相關,即提供一種界定,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抽象性;而判定是一種實踐行為,與科學具體的行為和結果直接發生關系。標準是抽象的,而判據是具體的。劃界標準不能替代判據,如果僅僅抽象地談論標準,而沒有在此基礎上形成與這個標準相對應的方法論判據,就會使劃界標準找不到實現的可靠途徑,使劃界標準無法用于區分科學與非科學、科學與偽科學的判定,就會使后現代主義消解科學劃界的各種觀點有機可乘。同樣,判據也不能離開標準,標準對判據有指導和規范作用,標準是形成判據的前提和根據,任何判據都不能離開劃界標準這個前提而獨立存在。
這里,值得一提的是兩位加拿大哲學家薩伽德 (P.Thagard)和邦格 (M.Bunge)的劃界思想。薩伽德的劃界理論有兩個部分:其一,提出了科學劃界的三個元哲學問題:(1)為什么科學劃界是重要的,從何處劃分?(2)什么是科學劃界標準的邏輯形式?(3)作為科學或偽科學的單元是什么?其二,提出了劃界的具體評判單元,包括:(1)科學使用相互關聯的思維方式,偽科學使用相似性思維。(2)科學追求經驗確證和否證,偽科學忽視經驗因素。(3)科學研究者關心與競爭有關的理論評價,偽科學研究者不關心競爭理論。(4)科學采用一致并簡單的理論,偽科學則是非簡單理論和許多特設性假說。(5)科學隨時間而進步,偽科學在文本和應用中停滯不前,保守等[4]。盡管這些評判單元還十分模糊,尚不能構成劃界的充分必要條件,但仍然可視為是劃界研究的進步,它代表了理論未來努力的方向。
歷史分析使我們認識到,現有的劃界問題的研究不僅在理論上不能令人滿意,而且距現實的需要相差甚遠。要想把問題的研究推向深入,除了理論思考之外,還要依賴科學實踐的推動。科學劃界的標準是從成功的科學歷史中總結出來的,是歷史經驗的總結,其必將隨著科學的發展被繼續總結,進而豐富和發展。
[1] 舒煒光.科學認識論:第 4卷[M].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4.
[2] [美 ]拉瑞·勞丹.進步及其問題[M].劉新民,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99.
[3] Laudan.The Dem ise of theDem arcation Problem[A]//in R.S.Cohen and L.Laudan(eds),Physics,Philosophy and Psychoanalysis[C].D.Reidel Pub lishing Company,1983:8.
[4] 陳健.科學劃界的多元標準[J].自然辯證法通訊,1996,(3):1-2.
〔責任編輯:王雅莉〕
B2
A
1007-4937(2010)03-0158-03
2010-03-15
程曉皎 (1985-),女,黑龍江哈爾濱人,碩士研究生,從事科學哲學及科學史研究;孫玉忠 (1964-),男,黑龍江哈爾濱人,教授,科技哲學博士,從事科學哲學及科學史研究。
- 黑龍江社會科學的其它文章
- 關于日本戰后賠償分期問題的思考
-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進路及實踐坐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