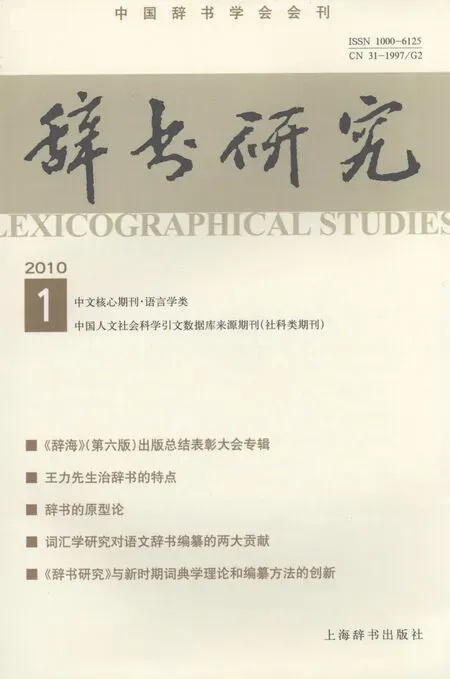就《新世紀漢英大詞典》的評論與赫迎紅先生商榷
趙 剛
《新時代漢英詞典》執行編委赫迎紅先生連續撰文[1],對西安外國語大學惠宇和杜瑞清主編的《新世紀漢英大詞典》(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3,下文簡稱《新世紀》)進行了評論,認為《新世紀》“機械搬用、以訛傳訛”,“隨意改動、弄巧成拙”,“按照漢語思路,直譯硬譯”,“(收詞釋義存在)政治性錯誤”,“百科性條目不平衡、譯文不一致(畸輕畸重)”,“隨意添加、畫蛇添足”,“隨意搬用英語成語,造成誤解”。赫先生的結論為“《新世紀》給人的印象是:它大體沿用了《新時代》的釋義和例證體系”,“《新世紀》在語言質量方面的問題較多,不夠嚴謹”。
作為參編《新世紀》的一員,筆者在拜讀赫先生的三篇文章后,一方面承認他文中所舉某些例子《新世紀》的確處理不當,另一方面又對赫先生于《新世紀》的各種評語及所得結論不以為然。特撰此文,為《新世紀》一辯。
一、《新世紀》出版前后
《新世紀》的編纂大約始于上世紀90年代初期。據筆者所知,惠宇先生起初并未打算編纂如此一個“巨無霸”,他的目標只是編寫一部釋義配例精益求精的中型漢英詞典,當時約定由武漢一家出版社出版。后來詞典越編越大,相關方面對詞典的期望也越來越高,武漢的出版社財力不濟,中途退出,這才有了《新世紀》與外研社的聯姻,而與外研社洽談成功大約已在2000年年初,當時詞典已經進入了最后攻堅階段。外研社當時獲知《新時代》即將出版,曾催促《新世紀》于2000年年底出版,但惠宇先生認為詞典應以質量為先,沒有必要爭搶時間,拒絕了這一要求。赫先生說《新世紀》大體沿用了《新時代》的釋義和例證體系,這是很難成立的,因為《新時代》出版前后,《新世紀》即將竣工,這樣一部歷時十年之久的大型漢英詞典,其編纂原則、釋義方式、例證體系是不可能在最后階段才根據剛剛出版的《新時代》來確定的。事實上,赫先生在自己的文章中只強調了《新世紀》與《新時代》在釋義方面的某些相同之處,并未看到兩本詞典大量的相異之處。舉一個簡單的例子,赫先生認為《新世紀》的“海內”條刪去(《新時代》)別的例子,卻單單保留了“海內外”這個錯例。這里姑且不談該例證是對是錯,筆者想說明的是,《新世紀》選擇“海內外”作為“海內”的例證,并非是在《新時代》所提供例證上的刪減,而是與《新世紀》自己的例證體系相一致的,即盡量減少使用互文性強、譯文爭議較大的文學例證,而是選用一些與日常生活比較貼近的、使用頻率較高的例證。至于《新世紀》和《新時代》的種種相異之處,可參看拙文《立足實用,努力創新——編纂〈新世紀漢英大詞典〉點滴談》[2]。
二、對于評論的再評論
赫先生在三篇文章中,對《新世紀》作了方方面面的點評。筆者擬從六個方面與赫先生商榷,主要論及赫先生未解《新世紀》編纂原則之處及其評論中之不妥之處。
1.關于收詞
赫先生(2006b)提到《新世紀》較少收錄人名,“忽視人文、社科某些方面”,他認為,人名翻譯比較困難,所以漢英詞典應該收錄:(a)已經約定俗成的我國某些名人的譯名,如孔子(Confucius)、孟子(Mencius)、陳香梅(Chen Hsiang-mei)等;(b)沿用方音或中西結合的名字,如李光耀(Lee Kuan-yew)等;(c)某些外國名人的傳統漢字譯法,如陳納德(Claire Lee Chennault)等;(d)其他語言中漢字人名,如金日成(Kim II-sung)等。其實,《新世紀》并未漏收孔子、孟子,赫先生可能是疏于查檢。筆者認為,在因特網普及并“已經成為詞典部分替代品”[3]的背景下,名人名字的英譯并不難尋,只要將這些人的漢語名字輸入google或baidu,很容易找出其英文譯名。赫先生認為應該收錄名人的名字,那么哪些人才算“名人”呢?這個度其實很難把握,譬如,赫先生認為《新時代》收錄日本首相“田中”是正確的,那么《新時代》怎么又未收前德國總理“科爾”呢?由于“名人”的標準不一,數量巨大,難免掛一漏萬。既然讀者可以通過網絡輕松地找到這些人的英文譯名,漢英詞典不收錄名人姓名無可厚非。
赫先生(2006b)認為,“隨著全球化的發展,著名公司、品牌等名稱日益流行”,《新世紀》應該像《新時代》那樣系統收錄這類詞匯,如“聯想” 、“因特爾”、“豐田” 、“大眾”等。他認為,《新世紀》“偶爾收了個別詞語,卻毫無系統性、一致性可言”。著名公司、品牌名多如牛毛,如何才能做到赫先生所說的系統性和一致性,的確是個問題。就品牌名而言,《新時代》是收錄了上面提到的幾個品牌,但國內名牌如“海爾”、“長虹”、“國美”、“鄂爾多斯”、“娃哈哈”、“華為”、“瑞星”等收不收?國際名牌“宜家(Ikea)”、“康柏(Compaq)”、“美寶蓮(Maybelline)” 、“資生堂(Shiseido)”、“蘭蔻(Lancome)”、“佳能(Cannon)”、“萬寶路(Marlboro)” 、“耐克(Nike)”、“阿迪達斯(adidas)”、“銳步(Reebok)”等收不收?如果不收,何談系統性?如果要收,度如何把握?舉個簡單的例子,《新時代》收了“美國航空公司”、“日本航空公司”,卻漏收了“中國航空公司”;收了“麥當勞”卻不收“肯德基”。這樣看來,《新世紀》在品牌名收錄方面沒有不切實際地要求“系統”,而是收錄最常見的少數品牌名,并非沒有道理。
2.關于借鑒中的以訛傳訛
赫先生(2007)認為:《新世紀》在不少地方借鑒了《新時代》的詞條、釋義和例證,有時造成“以訛傳訛”。他從《新世紀》中挑了“晦暝、圍、海內外”三個例子加以佐證。
關于“海內外”的處理,前文已論及,這里不再贅言。筆者認為《新世紀》對“晦暝”和“圍”的處理的確有誤。但另一方面,僅憑兩個例證來斷言新世紀是“以訛傳訛”,似乎有點言過其實。事實上,大型辭書的編纂肯定要借鑒其前出版的同類詞典,但由于編者的疏漏或自身學識的限制,出現個別錯誤完全有可能,看看古今辭書,有哪一部是完美無瑕的?但由于個別錯誤,就匆匆冠以“以訛傳訛”,似乎有些言重了。
辭書編纂是一項艱苦卓絕的工作,只有身體力行,才能體會到其中的甘苦。筆者并非是為《新世紀》中的謬誤進行辯解,只是認為,辭書評論者要客觀對待詞典中存在的問題。
3.關于一些詞的翻譯問題
關于詞條的翻譯問題,赫先生討論較多。但不無遺憾的是,這些討論往往由于疏于調查或對譯事規則不盡了解而有失偏頗。本文由于篇幅關系,只舉兩例進行論證。
赫先生(2007)認為,《新時代》和《新世紀》把“色酒”譯為“wine,champagne”不準確,應該翻譯為“coloured low-alcohol wine(made from grapes or other fruit)”。此外,他認為《新世紀》把“香檳酒”簡單譯為“champagne”也不準確,因為中文中的“香檳酒”雖然來自champagne,但它已演變為不限于法國Champagne地區的產品,而泛指任何經過兩次發酵的、帶汽的酒,應譯為“white sparkling wine”。
先看“色酒”的翻譯。《現代漢語詞典》中該詞的定義為:用葡萄或其他水果為原料制成的酒,一般帶有顏色,酒精含量較低。再看《朗文當代高級英語詞典》(2004)對wine的定義:(1)an alcoholic drink made from grapes,or a type of this drink.(2)an alcoholic drink made from another fruit or plant。筆者實在看不出來用wine譯“色酒”有什么不當之處。最后,筆者認為,champagne跟在wine之后翻譯“色酒”也符合詞典翻譯中譯文之間要相互補充的原則,更何況,“色酒”并非指某種特定的酒,只是指以葡萄或其他水果為原料制成的一種酒,所以champagne雖然并非最佳譯文,但跟在wine的后面對譯色酒,并不為錯。說不定外國人見了我們的“色酒”,第一印象就是champagne,而非赫先生的coloured low-alcohol wine(made from grapes or other fruit)。其實,英文中的“low-alcohol wine”一般譯為“低醇酒”,是一種適合老人、婦女、兒童及一些特殊人群如病人、孕婦等飲用的“酒”,與“色酒”根本沒有關系。
再看“香檳酒”譯為champagne是否妥當。首先,雖然漢語中的香檳酒語義有所擴大,但其最佳對應詞為champagne當無疑問。此外,在英文中champagne一詞的意義也已擴大,可以指和champagne同種類的酒,如以下論述[4]:
Champagne is a sparkling wine produced by inducing the in-bottle secondary fermentation of wine to affect carbonation.It is named after the Champagne region of France.While the term“champagne” is often used by makers of sparkling wine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and is commonly used by the general public as a generic term for sparkling wine),many wine enthusiasts maintain it should only be used to refer only to the wines made in the Champagne region.When used to refer specifically to wines produced in Champagne,the word may(or may not)be capitalized;when used as a generic term for sparkling wine(or in reference to the color champagne)it is always spelled in lower case.
這樣看來,《新世紀》用champagne來譯“香檳酒”無論是特指還是泛指均無不妥。
赫先生(2006b,2007)認為,《新世紀》中“山盟海誓”的釋義“oaths as high as the mountains and vows as deep as the oceans-solemn pledge of love”為“沿用漢語思維,不顧文化內涵的硬譯”,并指出:“在英語里,oaths和vows哪里有高、矮、深、淺之分?又如何與山或海比擬呢?”
筆者認為,辭書翻譯和一般意義上的翻譯是有區別的。漢英詞典對具有文化意義和民族特色的詞語的翻譯,一般都采取先直譯、后意譯的做法。直譯的目的是告訴外國讀者,中國人采取什么方式來表達某個意義,意譯則告訴讀者這個條目的語用意義。就“山盟海誓”而言,oaths as high as the mountains and vows as deep as the oceans為直譯,旨在告訴外國讀者,中國人就是以這樣的措辭來表達誓言和盟約永恒不變這一意義的,至于oaths和vows是否有高、矮、深、淺之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傳遞這一獨特的漢語表達方式,而后面的solemn pledge of love則是意譯,告訴讀者這一漢語成語的語用意義是什么。事實上,不但漢英詞典如此,英漢詞典在處理富有英語文化特色的諺語時也是如此,例如,“A rolling stone gathers no moss”,通常在詞典中也會譯為:滾石不生苔,轉業不生財。這樣看來,《新世紀》對“山盟海誓”的處理當無問題。[5]
4.關于政治性問題
赫先生(2006b)認為,《新世紀》把“中國大陸”譯為mainland China,而非赫先生提出的 Chinas mainland或 the mainland(of China),是“一個嚴重的政治性錯誤”。事實情況真有這么嚴重嗎?筆者不這樣認為。首先,《新世紀》把“中國大陸”譯為mainland China,并非政治錯誤。在中國外交部的英文網站上,中國官方使用mainland China來表達“中國大陸”這個概念的比比皆是,甚至比 Chinas mainland還要多得多。例如,新華社 2003年4月16日有一篇報道的題目就是Latest Statistics on SARS on Mainland China[6],2008年3月 25日的文章“Beijing Olympic flame lit in ancient Olympia”中講到“中國大陸”,用的也是mainland China。其實,赫先生提出的“中國大陸”的英文翻譯也并非其首創,筆者記得《中國翻譯》等刊物前些年早就有討論,但討論歸討論,使用歸使用,約定俗成的力量有時甚至更大,與政治性錯誤實在掛不上鉤。誠然,《新世紀》收了“漢城”而不收“平壤”,“塞外”、“三通”的誤譯等問題確實如赫先生所批評的那樣是存在的,但平心而論,這實在只能算是辭書編纂工藝上的疏漏,要給編者或詞典冠以“政治性錯誤”的帽子,似乎讓人難以接受。辭書批評中還是慎用此類政治標簽為好。
5.關于條目義項設立的標準問題
赫先生(2006a)認為:“鑒于漢語單語辭書的義項設立、釋義體系已相當成熟,漢英詞典設立義項的一般標準是:必須`立足漢語',充分借鑒漢語辭書的義項設置方案,不宜輕易增刪、顛倒、合并義項,否則往往會導致背離漢語詞語的原意。”關于雙語辭書義項劃分原則的問題,黃建華等[7]有過詳細說明:“……除了以選定的藍本為基礎并參考其他原版詞典作必要的分合以外,還應根據不同語言詞匯的語義內涵的異同和讀者在理解和運用上的困難作必要的調整。例如漢語的`搞'這個詞在《現代漢語詞典》里只有一個義項:做;干;辦;弄。而在《漢英詞典》里卻分為五個義項。”此外,漢英詞典義項的排列,也不一定要與漢語單語辭書一致,因為單語辭書義項的排列往往因詞典類型的不同而相異,譬如,有按義項的歷史發展順序排列的,有按義項之間的邏輯關系排列的,也有按義項的使用頻率排列的。漢英詞典不能死扣藍本,而應根據詞典的編纂原則及讀者對象作出調整。更何況,像《新世紀》這樣的大型詞典,其義項的設立往往以多個藍本為依據,怎能不作出調整?
6.關于自由搭配詞組立條的問題
赫先生(2006a)認為,《新世紀》將諸如“賽過、繞過、讓給、讓與、忍住、燒壞、燒焦、燒死”等大量自由搭配立條,實屬過分。正如赫先生所言,漢英詞典與漢語詞典在立目方面應有所不同,而且固定詞組和自由搭配詞組之間確實存在一個灰色地帶,不易判斷。漢英詞典立目時不但應該考慮某個表達是否為固定詞組,也要考慮該表達是否有獨特的英文表達方式。而按照這個標準,以上各詞大多應該進入漢英詞典。譬如,讀者很難從“賽過”的字面意思推知其英譯“surpass;exceed;overtake”,更何況這三個對應詞在英語中還有用法區別。《新世紀》通過例證體現它們的用法區別,應該說非常恰當。再如“繞過”,英文常用bypass來表達,也是一般譯者希望從漢英詞典中獲得的信息。“讓與”一詞是否自由搭配也值得商榷,因為該詞在現代漢語中常用于一些術語中,如“債權讓與”、“讓與擔保/交易”、“讓與人”、“著作權讓與”等。這樣看來,《新世紀》收錄該詞并提供譯文“cede;relinquish;surrender;transfer;yield;assign”是十分恰當的。另外,“燒焦”一詞在“在線新華詞典”中單獨立目。而普通譯者對“忍住”、“燒死”等的翻譯也會感到難以措手,從詞典實用性的角度來看,收錄這些詞也并無多大問題。最后,赫先生說《新世紀》“大量”收入這些詞匯的說法也不恰當,因為筆者不知道赫先生在這部大部頭詞典中究竟找到了多少這樣的詞語?
三、結 語
以上從六個方面對赫迎紅先生關于《新世紀》的評論作了分析,限于篇幅,赫先生文中的其他失當之處難以再詳細討論。作為編寫《新世紀》的一員,筆者由衷感謝并接受赫迎紅先生就《新世紀》中的不當之處提出的批評。但筆者認為,對《新世紀》這樣已獲公認的較為優秀的詞典,不應一味惡評,而應抱著促其發展和完善的態度進行評論。
附 注
[1]赫迎紅先生所撰三篇文章分別為:《淺談大型漢英詞典的詞條和義項設立》(《辭書研究》2006年第2期,文中簡稱“2006a”),《談談漢英詞典編纂中的幾個問題——從〈新世紀漢英大詞典〉的錯誤談起》(《文匯讀書周報》2006年6月2日,文中簡稱“2006b”),《大型漢英詞典的編纂與漢英翻譯》(《外語與翻譯》2007年第1期,文中簡稱“2007”)。赫先生在(2007)這篇文章中署名為“迎紅”,第二作者為“鄒備”。為方便起見,文中均稱“赫先生”。
[2]趙剛.立足實用,努力創新——編纂《新世紀漢英大詞典》點滴談.辭書研究,2004(6).
[3]張國強.要重視因特網成為辭書替代品的現象.∥辭書與數字化研究.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
[4]Champagne(beverage):Encyclopedia,http:∥en.allexperts.com/e/c/ch/champagne (beverage).htm
[5]赫先生對《新世紀》中“暗箱操作”一詞的討論與“山盟海誓”類似。首先,black case work是直譯,而且《新世紀》緊跟著就給出了意譯manipulation behind the scenes。此外,China Daily等英文報紙上也用該譯來表達“暗箱操作”。
[6]http:∥www.fmprc.gov.cn/eng/topics/sars/t23066.htm
[7]黃建華,陳楚祥.雙語詞典學導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
1.陳忠誠.初評《新時代漢英大詞典》.上海科技翻譯,2001(2).
2.陳忠誠.為2002年版《新時代漢英詞典》指誤.四川外語學院學報,2005(2).
3.過家鼎.注意外交用詞的政治含義.中國翻譯,2002(6).
4.趙剛.談談《新世紀漢英大詞典》在例證方面的創新.外語教學,20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