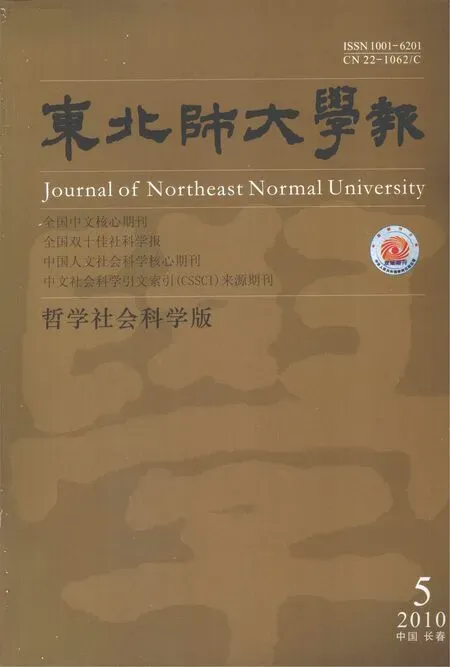共產(chǎn)國際、聯(lián)共(布)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的新探索
——《共產(chǎn)國際、聯(lián)共(布)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1919—1943)》簡評
鄭德榮
共產(chǎn)國際、聯(lián)共(布)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的新探索
——《共產(chǎn)國際、聯(lián)共(布)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1919—1943)》簡評
鄭德榮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是毛澤東對中國追求科學真理的先進分子和中國共產(chǎn)黨人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路徑的鮮明寫照和精辟概括,是人們熟悉并得到廣泛共識的至理名言。我們應深入思考,全面領會和把握。中國共產(chǎn)黨是在俄國十月革命勝利的啟迪和共產(chǎn)國際的支持下誕生的,黨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決定正式加入共產(chǎn)國際。此后,直到1943年共產(chǎn)國際宣布解散,在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內(nèi),中國共產(chǎn)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正確與否,都與共產(chǎn)國際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由此可見,共產(chǎn)國際與中國共產(chǎn)黨的關系是中共黨史研究必須搞清楚的重要領域。王占仁博士的新著《共產(chǎn)國際、聯(lián)共(布)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1919-1943)》(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系屬這個領域研究的組成部分,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一次歷史性飛躍重大理論成果——毛澤東思想形成發(fā)展史研究領域的重要組成部分。遺憾的是,這個交叉的邊緣性課題,長時期以來很少有人問津。這恐怕是同這兩個領域研究的歷史和現(xiàn)狀密切相關的。
共產(chǎn)國際、聯(lián)共(布)與中國革命關系研究在改革開放前由于涉及中蘇兩黨兩國關系,是個“禁區(qū)”。改革開放后,中央高度重視,一度掀起研究熱潮,20世紀90年代又冷落了下來。直到今天,由于全新文獻資料的翻譯出版,學術界又掀起了幾個“浪花”。20世紀80年代初,為了工作的需要,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要負責人經(jīng)請示中共中央黨史領導小組批準后,組建了“共產(chǎn)國際與中國革命關系研究領導小組”。領導小組由廖蓋隆任組長,我是六個成員之一。參與這個領導小組,對我深入研究共產(chǎn)國際、聯(lián)共(布)與中國革命關系起到了極大的促進作用。在這個小組的組織領導下,研究工作逐步開放和開展起來,每年舉辦一次規(guī)模不大(50—70人)的學術年會。這一領域的研究突破了長期以來的“禁區(qū)”,并在20世紀80年代形成了第一個研究高峰。產(chǎn)生一批研究成果,一些高校還開設了課程,擴展了以往黨史研究的領域,澄清了一些歷史謎團,恢復了歷史的本來面目,推動了中共黨史研究的整體深入發(fā)展。20世紀90年代以來,這項研究的總體發(fā)展趨勢逐漸趨冷,一些高校國際共運史的課程不開了,從事這一課題的研究者也少了。但是,從歷史研究和學術研究的角度來看,這仍然不失為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領域。可喜的是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一直關注這個領域的研究,不惜投入大量的人力財力引進由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和俄羅斯現(xiàn)代歷史文獻保管與研究中心同德國柏林自由大學東亞研究會聯(lián)合編輯的有關聯(lián)共(布)、共產(chǎn)國際對華政策的大型系列檔案文件集《聯(lián)共(布)、共產(chǎn)國際與中國(1920-1949)》,這批檔案文獻資料的編輯出版為深入研究提供了難得的可貴資料,創(chuàng)造了極為有利的重要條件。不少學者充分運用這些新史料并取得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在整體趨向冷落的過程中掀起了幾個“浪花”。我之所以把它說成是“浪花”,是因為現(xiàn)在從事這個領域研究的學者有些青黃不接,老的像我們這一代,都已經(jīng)七八十歲了,年輕的一代四五十歲的有一些,三十幾歲的就很少了。以前我們從事研究時總是感覺文獻資料不夠用,現(xiàn)在的情況是大批原始材料翻譯過來了,卻沒有得到充分的利用。對于這么有學術價值的問題,面臨這樣現(xiàn)實的境遇,令人擔憂。所以當王占仁向我提出對共產(chǎn)國際、聯(lián)共(布)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關系問題很感興趣并想作為博士學位論文進行深入研究時,我便大力支持并全力幫助,這也促使我在過去取得的研究成果基礎上,挖掘現(xiàn)在翻譯出來的最新史料,重新思考和梳理這個問題。
關于共產(chǎn)國際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關系問題,我曾在1993年發(fā)表了《共產(chǎn)國際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雙效應》的研究論文。文章系統(tǒng)考察了中國共產(chǎn)黨的創(chuàng)立暨大革命時期、土地革命戰(zhàn)爭時期、遵義會議以后及抗日戰(zhàn)爭時期共產(chǎn)國際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積極和消極影響。在對各個時期共產(chǎn)國際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關系進行全面的具體分析的基礎上得出結論:總體上共產(chǎn)國際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起了積極的和消極的“雙效”作用。這就澄清了學術界存在的一些片面認識,如片面強調(diào)共產(chǎn)國際對中國革命指導上的錯誤,而無視或否定共產(chǎn)國際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具有積極影響的一面。其實,歷史地審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史進程,不難看出,共產(chǎn)國際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影響在總體上是“雙效”的,當然在不同歷史時期、不同歷史問題上發(fā)揮的作用也有所不同,有的是積極的,有的是消極的,有時二者同時并存。
當然,共產(chǎn)國際、聯(lián)共(布)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關系不是一兩篇文章就能說清楚的大問題,還有很大的研究空間。我認為共產(chǎn)國際、聯(lián)共(布)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關系在內(nèi)容上主要體現(xiàn)在三個方面。一是體現(xiàn)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包括思想理論和原著通過俄國傳入中國;二是共產(chǎn)國際、聯(lián)共(布)對中國革命形勢的判斷和對中國共產(chǎn)黨路線方針政策的指導,包括錯誤的和正確的兩個方面;三是共產(chǎn)國際、聯(lián)共(布)對毛澤東在領導開創(chuàng)農(nóng)村革命根據(jù)地和紅軍戰(zhàn)爭中的貢獻及其思想和主張的關注和評價,以及毛澤東對共產(chǎn)國際、聯(lián)共(布)的態(tài)度,對馬列經(jīng)典著作的重視、學習和運用。在研究方法上,一是既要把此課題置于共產(chǎn)國際、聯(lián)共(布)與中國革命關系的歷史大背景下,還要置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中加以考察;二是以歷史主義和辯證法的觀點全面地實事求是地具體地分析與評價。如果按此方法評析,就會得出以下結論:首先,共產(chǎn)國際、聯(lián)共(布)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總體來說是“雙效應”,當然在不同時期和不同歷史問題上有所不同,不宜簡單地肯定或否定。其次,不能由于毛澤東與“左”傾教條主義者是兩條對立的路線而用形式邏輯加以推論,認為共產(chǎn)國際、聯(lián)共(布)既然是王明的后臺就必然全盤否定毛澤東,或者是贊同毛澤東就必然否定王明。這些就是我在指導王占仁撰寫“共產(chǎn)國際、聯(lián)共(布)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1919—1943)”博士論文時的主要指導思想。從寫成的專著看,達到了這個預期目標。這本書通過深入細致地考察共產(chǎn)國際、聯(lián)共(布)與毛澤東主體思想和支柱理論包括“一條道路”和“三個法寶”,即社會革命理論、革命統(tǒng)一戰(zhàn)線理論、武裝斗爭理論和黨的建設理論的關系,從理論上深入探討了共產(chǎn)國際、聯(lián)共(布)繼承、發(fā)展和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對中國共產(chǎn)黨產(chǎn)生的深刻影響,深入地剖析了共產(chǎn)國際、聯(lián)共(布)與中國革命策略的關系,深刻地闡明了毛澤東思想產(chǎn)生和形成的國際條件和歷史背景,有利于我們更加完整準確地認識馬克思列寧主義與毛澤東思想的內(nèi)在聯(lián)系。全書在完整準確地理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科學命題,綜合闡述中國特色革命道路的科學內(nèi)涵與理論價值,比較研究毛澤東與共產(chǎn)國際、聯(lián)共(布)革命統(tǒng)一戰(zhàn)線理論的異同,歸納總結“城市中心”與“農(nóng)村中心”的三條判斷標準,闡述毛澤東的“城市·農(nóng)村”觀,分析抗日戰(zhàn)爭時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中國革命實踐的“雙向互動”關系等方面都能提出自己的獨到見解,很有創(chuàng)新性。
在當今時代的中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成了“顯學”,大家都在以極高的熱情探討著這個問題,這是非常可喜的事情。但是,由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作為二級學科設置的時間還很短,從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和教學相當多的是原中共黨史專業(yè)人員,他們在寫文章或講課時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闡述往往浮光掠影,一帶而過,不同程度地存在著根基不牢的問題。能夠深入到共產(chǎn)國際、聯(lián)共(布)的歷史中去進行研究的成果更屬鮮見。對于民主革命時期的中共黨史研究而言,弄清楚共產(chǎn)國際、聯(lián)共(布)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來龍去脈是不可欠缺的。我認為有價值的東西不分冷熱。不能因為共產(chǎn)國際研究逐漸趨冷就忽略了它的學術價值。與此相反,這種一冷一熱的結合,恰好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熱中的冷思考。王占仁的專著恰恰是這一思考的可貴成果,也算是這個領域研究趨向冷落過程中的一個“浪花”吧!這本書是他的第一本學術專著,但愿能夠得到國內(nèi)外學術同仁的認可并給以指正,就算是對一個年輕學者最好的鼓勵吧!
2010-03-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