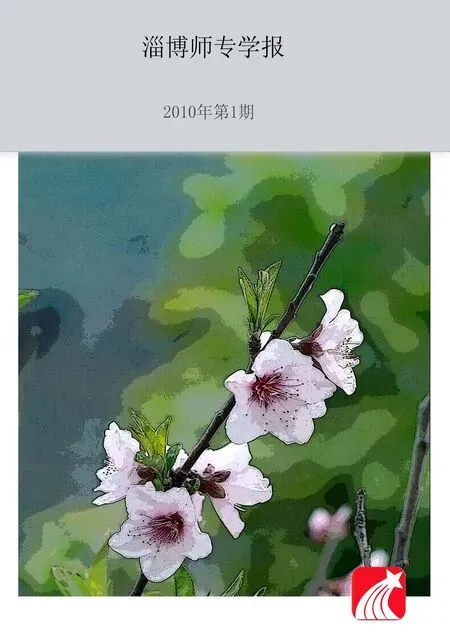關于晚年郭沫若佚作中“大寨”的幾點看法
逯 艷
(山東師范大學 文學院,山東 濟南 250014)
一、一首《重到晉祠》,詩性的自覺追隨
在郭沫若晚年佚作中首次涉及到“大寨”的是刊登在1966年1月1日《光明日報》第四版《大寨行》組詩中的首篇《重到晉祠》:“康公左手書奇字,照眼紅墻繞晉祠。周伯低頭迎舊識,鐵人舉手索新詞。欲流荇菜情難已,驚見睡蓮花未衰。懸翁山頭松失翠,頓憎旱魃費鞭笞。”[1]1966年的中國,被一股令人窒息的政治氛圍所籠罩。當許多知名文人在文壇銷聲匿跡時,作為中國文聯主席的郭沫若卻是幸運的。京城全國三大報刊之一的《光明日報》(另兩家是《解放軍報》和《人民日報》)在元旦這一天的文藝副刊“東風”專版上以醒目的位置刊登了郭沫若的組詩《大寨行》,標題以手跡套紅印制,相當引人注意。組詩共十八首,壓軸為《頌大寨》。1977年3月“由作者重新校對過”而出版的《沫若詩詞選》選入其中九首,并在《大寨行》標題下加了一則小序:“1965年11月19日,曾往山西參觀農村社教工作。歸途于12月7日,參觀大寨。先后成詩十六首,輯為《大寨行》。”[2](P2)《光明日報》作為京城權威性報刊之一,在元旦之際高調刊發大型組詩《大寨行》,毫無疑問看重的是組詩的政治宣傳作用。但是,為什么要把歌頌的對象放在大寨上?拿大寨大張旗鼓地說事兒,說服力和權威性的支點在哪?這也許關涉到政治走向。
1964年之后的數年,毛澤東提出了“新三面紅旗”——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全國學人民解放軍,為全國各界樹立楷模。在口號提出的1965年,“學大寨”更多強調的是艱苦斗爭、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但不能否認其中孕育著階級斗爭、路線斗爭的胚芽。這個從1936年就大快人心地說“黨決定了,我就照辦,要我做喇叭,我就做喇叭”[3](P80)的“傳聲筒”,盡職盡責地“喇叭”到1966年。除了政局的強力之外,或許也是一種久成的習慣性的思維套路,由此深諳政治玄機的郭沫若不可能意識不到領袖決定執行口號背后的動機和意圖。所以在參觀了設在太原的大寨展覽館之后,郭沫若為之題詞匾額并當場作詩:“大寨人人是愚公,神州爭效此雄風。百年基業防旱澇,千年山頭待柏松。勤奮力將全國學,虛心贏得普天同。為防自滿尋差距,決不因循步自封。”在親自接觸到大寨勞動人民時,握著老農布滿繭子的手,看著他們飽經風霜的臉,登上虎頭山人造小平原,郭沫若寫出了山西之行的一首五古:“全國學大寨,大寨學全國。人是千里人,樂以天下樂。狼窩變良田,兇歲奪大熟。紅旗毛澤東,紅遍天一角。”詩中直接指涉到領袖毛澤東的名字,滿溢著政治宣傳色彩。1966年刊發的《大寨行》組詩“不但因內中不少篇幅揄揚大寨,即就切和時宜而言,也是最為醒俗的”。[4](P12)但是,問題就出現在一九八四年出版的《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五卷,既未說明小序中的“先后成詩十六首之誤”,又“將《大寨行》中未收入《沫若詩詞選》的八首詩附錄如下。”所以,讀者誤認為組詩共計十七首,其中為首的七律《重到晉祠》被刪除了。這首詩之所以被逐出全集之外,目前的說法是因為詩的首聯“康公左手書奇字”中涉及到了“康公”,也就是當時中國政壇知名人物康生。我們權且不論86歲沉疴在體的郭沫若在“重新校閱”這組作品中如何的勉為其難,但是以因為“康公左手書奇字”碰觸了政治禁忌為理由加以刪除的官方辭令,著實牽強。無論什么原因,《重到晉祠》終究是被刪除在全集之外。我們認為,進不了史冊的往往是有悖官方意志的。所以,《重到晉祠》也許是一個契機,一個了解郭沫若置身政治之外的、摒棄了為政治服務的負重,遵循詩性的勃發,表達自我隱蔽情愫的心靈探照燈。
《重到晉祠》,這首游記詩未標明創作日期,據推測(馮錫剛)是在參觀社教工作之后歸途中所做,時間當是12月中旬。這首詩是《大寨行》這組純粹政治宣傳詩組中不直接涉及政治的詩篇,也是十八首詩中最有詩意的一首。頷聯“迎舊識”表明作者是繼1959年初游晉祠之后第二次來訪,當年詩人曾吟詠著“隋槐周柏矜高古”,今日重游卻有“欲流荇菜情難已”之語。“欲流荇菜”語出《詩經·關雎》“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是膾炙人口的愛情詩篇,這也是此詩最出彩的地方。在那個談情色變的年代,年過七旬的郭沫若卻能雅致地語出這樣的“禁忌”,不管是不是借助典故來障眼,多少都能流露出郭沫若作為詩人的直率和坦然。尾聯對照初游晉祠時的“懸翁山溪碧玉盤,飛梁荇菜布蔥荇”不難體會詩人為生存環境的惡化而倍感焦慮和擔憂。雖然被刪除在全集之外,這首詩作為晚年郭沫若所有詩作中數量罕至的不直接干預政治、謳歌時政的作品對后人研究郭沫若晚年那種故地重游突覺物是人非,為知識分子精神空間日漸狹促、生存環境岌岌可危的生存狀態的隱憂,具有一定的指引意義。
二、灰撒虎頭山,精神的自我回歸
于立群在《化悲痛為力量》中記載了郭沫若在病重期間近似遺囑性質的話:
四、五月間,沫若的病情幾次惡化。
他要孩子們把科學大會開幕式上華主席關懷他的照片好好珍藏起來。
他把我和孩子們叫到身邊,要我們記下他的話:“毛主席的思想比天高,比海深。照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就會少犯錯誤。”
“對黨的關懷,我特別感謝,我在悔恨自己為黨工作的太少了。”
“我死后,不要保留骨灰。打我的骨灰撒到大寨,肥田。”[5](P10)
在舉行了高規格的追悼大會之后,郭沫若的骨灰在1978年6月下旬灑到了大寨的層層梯田之中。從此,虎頭山上聳立起一座“郭沫若同志”紀念碑。有意思的是,五年之后原先的大寨領班陳永貴在北京逝世后作出了魂歸故里的后事安排,于是虎頭山出現了文壇泰斗的紀念碑和全國勞模墓碑并峙相映的奇特的人文景觀。
郭沫若一生和農民相涉甚少,為什么選擇大寨作為自己的歸宿?單單是對中央政策的至死維護和遵守嗎?所謂“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郭沫若作此決定,不會沒有原因。目前最容易為人接受的觀點是他視為知己的周恩來首先決定把骨灰撒在大寨,他之所以效仿可以看成是對故友的一種獨特的追隨。我認為這除了單純的追隨之外,或許還要加上一份深幽的懺悔。何出此言?1974年江青借“批林批孔”之名行“批周公”之實,威逼郭沫若寫揭發周恩來的材料。但是郭沫若最終用莊嚴的沉默維護了老戰友周恩來,不過有一點“晚節不保”意味的事件卻發生在了1976年。5月12日他作了《水調歌頭·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十周年》:
四海《通知》遍,文革卷風云。階級斗爭綱舉,打到劉和林。十載春風化雨,喜見山花爛漫,鶯梭織錦勤。茁茁新苗壯,天下凱歌勝。
走資派,奮螳臂,鄧小平,妄圖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三項為綱”批透,復辟罪行怒討,動地走雷霆。主席巨揮手,團結大進軍。[6](P12)
早在1972年,周恩來主持工作,批判極左思潮,各項工作出現轉機。不久便遭到毛主席的否定,繼而為江青一伙污蔑為“右傾回潮”。1975年11月下旬開始的“反擊右傾翻案風”,使病重的周恩來憂心如焚。1976年3月間上海《文匯報》刊登了“黨內那個走資派把至今不肯悔改的走資派扶上臺”,這樣赤裸攻擊的正是“反擊右傾翻案風”的矛頭所向——周恩來、鄧小平。郭沫若以“走資派、鄧小平”入詩,表達的卻是“奮螳臂”、“妄圖倒退”、“復辟罪行”!九泉下的周恩來要是知道老友語出此種“頌歌”,會是一種怎樣復雜的心情?當這位故友的骨灰養肥了大寨之后的兩年,郭沫若做出也要灰撒虎頭山的決定時,再聯想到這位知己生前是如何關照自己和家人,會有一種怎樣的內疚和懺悔的心情?所以,與其說郭沫若灰撒虎頭山的決定是說給家人的遺囑,不如當成是給總理的一種致歉。
“文革”結束后不久,1976年12月下旬召開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會議重申了周恩來生前總結的“三原則”(政治掛帥、思想有限的原則,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愛國家愛集體的共產主義風格),同時夾雜著不少“新經驗”。次年2月,郭沫若做了《望海潮·農業學大寨》。當然,假如用這種形式為了重遵周恩來當年的政治決策,來表達自己對友人的懺悔和歉意也應該足夠了。郭沫若作為知識分子的精英代表何以要在臨終對代表農村和農民的“大寨”表現出如此重視?所以其執意將骨灰撒在大寨,單靠追隨知己這一說恐怕有一點單薄。我們認為應該還有一點緣由,這就涉及到精神世界的自我回歸上。
早在年輕時,郭沫若創作《鳳凰涅槃》時就曾經有詩情來了難以自抑,便抱著大地親吻的常人難以接受和理解之舉。可見,他是一個感性的詩人。1921年他在杭州游覽,于雷峰塔下面看見一位鋤地的老農,在描繪“他那慈和的眼光”、“健康的黃臉”、“斑白的須髯”之后,出人意料地用以下詩句作結:
我想去跪在他的面前,
叫他一聲“我的爹”!
把他腳上的黃泥舔個干凈。[7](P433)
時隔44年后的1965年,當郭沫若系統地參觀了大寨展覽館之后,當他握著老農布滿繭子的手,看著他們飽經風霜的臉,登上虎頭山眺望一塊塊人造小平原時,那種想俯下身子親吻大地的沖動和大呼要“把他腳上的黃泥舔個干凈”,或許是礙于久經人生的戰場已經可以控制情感表達尺度的歲月沉淀,或許是礙于自己當時所處的時局和身份(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中國科學院院長、中國文聯主席),一句“大寨人人是愚公”,使“愚公”成為貌似許多難以直訴情感的濃縮產物。帶著這個觀點再看1976年的《望海潮·農業學大寨》:
四兇粉碎,春回大地,凱歌聲入云端。天樣紅旗,迎風招展,虎頭山上蹁躚。談笑拓田園,使昆侖俯首,渤海生煙。大寨之花,神州各縣,遍地燃。
農業衣食攸關,輕工業原料多賴支援。積累資金,繁榮經濟,重工基礎牢堅,主導愈開展,無限螺旋。正幸東風力飽,快馬再加鞭。[8]
這也是一首不折不扣的政治宣傳詩,談不上什么詩意。農業之所以“衣食攸關”,因為它關系到“輕工業原料”和“重工業基礎”,經濟要繁榮就要“積累資金”,“基礎愈牢堅”“主導”才能“愈開展”。摒除迎合政治那些粉飾之語,結合郭沫若人生不同階段曾經對農民的感情,這首詩貌似是可以浮現出詩人對 “大寨人人是愚公”那種愚公精神的禮贊,對“談笑拓田園”的創造精神的敬畏。
筆者截取了以上1925年、1965年、1976年三個時間段的三首詩作,通過分析,我們不難看出郭沫若在情感表達上經歷了由自在的狂放恣意到不忘迎合政治的謹小慎微到最后的政治口號淹沒了真實情感的“三級跳”。當然,這一個“三級跳”在今天看來更多的是倒退的“三級跳”。但是,對于當時處于特定環境和時局的郭沫若而言或許也是無奈之舉。其中的緣由,作為不是當事人的我們當然不可能主觀的去下結論。透過這一個“三級跳”,我們或許可以了解到當時的知識分子精神空間的狹促和寒磣。也許郭沫若有未卜先知的特異功能,早在二十年代就預示到自己最終只有在離開人世之后才能重回自由的、肆意的,我口說我話、我手寫我心的本我吧。所以執意將骨灰撒在大寨不獨是看重“大寨”的政治意義,實則應該是由“大寨”勾起了郭沫若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由自在舒唱的“鳳凰”到粉飾政治的“喇叭”那種扭曲蛻變的哀思,灰撒虎頭山、魂歸大寨,或許可以重回那個自在妄為、恣意灑脫的精神世界。
[1] 郭沫若.大寨行[N].光明日報,1966-01-01.
[2] [4][7]馮錫剛.郭沫若的晚年歲月[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
[3] 季國平.毛澤東與郭沫若[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
[5] 新華月報資料室.悼念郭老[C].北京:三聯書店,1979.
[6] 郭沫若.水調歌頭——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十周年[A].詩刊[C].1976,(6).
[8] 郭沫若.望海潮·農業學大寨[N].光明日報,1977-0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