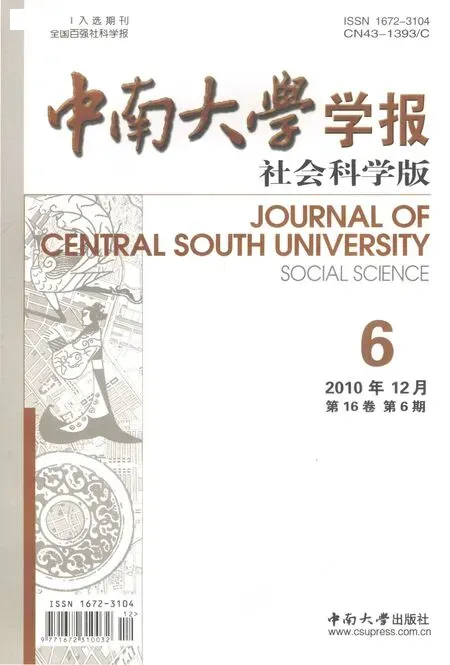西方生態女性主義探源
吳琳
(中南大學外國語學院,湖南 長沙,410083)
20世紀60年代,西方發達國家的工業化生產帶來了生態環境問題,引發了全球性生態環境危機,威脅著人類的生存與發展。進入70年代,由于全球生態環境問題日益惡化,人們開始思考和尋找解決的辦法。為了控制環境污染、保護自然環境、維持人類的生存和發展,全球興起了一場現代環境保護運動。與此同時,女性主義運動也蓬勃發展起來。隨著女性主義理論和實踐的發展,許多女性主義者越來越認識到女性問題與其他社會問題是密不可分的,認識到壓迫女性與壓迫自然、有色人種等邊緣群體有著密切的聯系,因此,許多女性主義者積極參與到環境保護運動中來。在這種歷史背景之下,生態女性主義誕生了。
生態女性主義的淵源十分復雜,它不僅是一種文化理論,也是一場為實現社會變革而興起的實踐運動,還是一種看待世界和他人的哲學視角。作為二十一世紀一股洶涌澎湃的文化思潮,生態女性主義在文學批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和獨特的地位,筆者嘗試對其淵源進行全面和深入的分析與探究,揭示生態女性主義的本質,以期為我國的生態女性主義研究做一些補白的工作。
一、女性主義思潮的新發展:生態女性主義的理論淵源
生態女性主義與女性主義思潮有著密切的聯系。生態女性主義的理論著作源于20世紀70年代中期的女性主義運動,所有生態女性主義者的批評觀點均建立在女性主義理論觀點的基礎之上。法國激進女性主義者弗朗索瓦·德奧博納(Francoise d’Eaubonne)是第一個使用“生態女性主義”這個術語的人。1974年,德奧博納在她的著作《女性主義或者死亡》中使用了“生態女性主義”這個詞。在書中她指出,父權制是造成人口過剩和自然環境破壞的主要原因,而女性主義是治愈這兩種危機的唯一途徑。她說:“拯救世界的唯一途徑就是讓男性權力產生‘劇變’以及由女性引導一場改變權力結構的革命。”[1](178)她號召婦女領導一場生態革命以挽救地球,這場生態革命將會在男性和女性之間、人類和自然之間建立起新的性別關系。
德奧博納在書中描述了生態女性主義運動產生的背景并對這一術語作了解釋。生態女性主義運動與中歐的政治運動有關,德奧博納的關于生態女性主義的理論和定義正是來源于對這些運動的解釋和總結。在與生態女性主義有關的政治運動中,最有名的是法國的前沿改革主義者。她們最初以為婦女爭取墮胎權、離婚權和平等權作為她們的主要目標,1973年,她們發展了與生態有關的內容,其中部分內容是以美國女性主義者舒拉米斯·費爾斯通在《性的辯證法》中提及的美國女性主義的生態語境為基礎。但是前沿主義者沒有能夠堅持對生態的興趣,不久就宣布放棄對生態的關注,重新轉向她們原有的興趣:墮胎、離婚權和平等權。后來,他們中的一部分人分離出來成立了另外一個組織——生態女性主義中心。中心的成員領導了一系列有關生態女性主義的運動。
1978年,德奧博納在另一本書《生態女性主義:革命或者轉變?》中詳細討論并深化了在前一本書中未完成的話題。在這本書的第一部分,德奧博納指出,雖然從人口數量、生育方面來看,婦女本應該充當主宰的角色,但是男性統治的社會壓迫女性,并使她們處于從屬地位。不但如此,在男性神學和法學的控制下,婦女的生育權力被男性剝奪,在人類歷史上大部分時期,女性的生育權都被男性控制著。地球和人類均受到人口過剩的威脅,男性像統治女性一樣統治著地球。男性主宰的城市化、科技化的社會導致了土地貧瘠,男性造成的過度生育導致了人口過剩。面對這一現實,她呼吁,女性要行動起來解放自身,也拯救地球。生態女性主義運動將使人類最終被視為是人,而不是首先是男人或者女人。一個接近女性的地球也將變得對所有人都更加郁郁蔥蔥。
德奧博納指出,僅僅只是“轉變”并不足以產生女性主義者需要的結果,為了引起人們對女性和地球現狀的關注,女性主義者需要在西方發動一場思想革命。這本書的副標題——“革命或者轉變”正體現了德奧博納的這種觀點。她宣稱,生態女性主義革命的目標是建構一個適宜生存的社會,讓歷史得以延續。她認為,人類和地球瀕臨滅亡,要阻止這種危險,就必須對人類的思想和行為加以變革。她堅信這一目標只有靠生態的和女性主義的組織才能實現。
在書的第二部分,德奧博納簡要回顧了從舊石器時代以降至20世紀60年代,男性主宰的社會對婦女和自然的壓迫和統治。她指出,在史前時期的人類社會中,女性掌有農業生產的支配權,女性的權力使她們具有和男性同等的社會地位。[1](193)她駁斥了那些認為母權制只是一種假想的神話的觀點,批判了男權制權威的無限制主義,這種無限制主義指的是對其他國家和民族進行統治的父權制力量。德奧博納指出,這種無限制主義的統治如果繼續發展下去,將使地球無法再給我們提供生存所需的食物。只有生態女性主義領導一場改變人類思想和行為的革命,才能終止這種無限制主義的統治。她大膽地呼吁:“今天我們必須把地球從男人手中奪走,為人類的明天重建地球。”[1](193)
二、激進的行動主義:生態女性主義的行動淵源
生態女性主義在誕生之初就是一種以現實的緊迫問題為驅動力的草根政治運動。[2](35)當生態女性主義這個術語還沒有廣泛傳播開來時,已經發生了一系列具有生態女性主義重要意義的事件。20世紀70年代,女性主義運動和生態主義運動迅速發展起來。大批生態學著作出現,使人們了解了環境破壞的后果,增強了環境保護意識。與此同時,婦女們受惡劣的經濟條件所迫,加入資本主義的勞動大軍,但是她們卻遇到了同工不同酬、玻璃天花板、性騷擾等性別歧視問題。環境破壞以及婦女生育和兒童健康受到的嚴重威脅引發了美國的生態女性主義運動。
最早將女性主義和生態主義聯系起來的事件是1974年在加利福尼亞的伯克利召開的“婦女與環境”會議,會議主要討論了父權制體系中婦女和自然的聯系。1976年,美國生態女性主義者伊內斯特拉·金在美國佛蒙特州的“社會生態學研究所”開設了“生態—女性主義”課程。1979年,賓夕法尼亞州哈里斯堡附近的三里島核能電廠發生泄露事故,這使得婦女運動、環境運動與現代科學之間的聯系突顯出來。1980年,由于三里島核反應堆事件造成的影響,伊內斯特拉·金和其他一些人在馬薩諸塞州阿姆赫斯特組織召開了主題為“婦女和地球上的生命:1980年代的生態女性主義”的會議,它標志著美國生態女性主義的誕生。這次會議開辦了80多個工作室,分別討論了女性主義理論、軍國主義、種族主義、都市生態學、可選擇技術運動等重大問題。這次會議促進了生態女性主義在全美的發展。會議的組織者伊內斯特拉·金與其他人一起,在1980年11月和1981年11月發起了名為“婦女五角大樓行動”的一系列反軍國主義示威游行。婦女五角大樓行動是第一次女性主義者大規模的反對環境破壞的示威行動。第一次示威行動大約有2000名婦女參加,第二次的參加人數大約是第一次的兩倍。示威過程中沒有演講者或領導者,這些婦女圍在五角大樓旁邊,用一種象征性的方式抗議殺戮生命的核戰爭和核武器的發展,強調軍事行動與生態女性主義之間的關系。
此后,這類行動很快傳遍了世界各地。1982年12月,在英格蘭格林漢公地舉行了抗議威脅地球生命延續的核導彈部署行動。伊內斯特拉·金在文章中描述了這次行動:“三萬名婦女圍住美國軍事裝備,揮舞著嬰兒的衣服、圍巾、詩歌和其他個人生活的象征物品。一時間,‘自由’這個詞從她們的口中同時說出來,在基地的四周久久回響。三萬名婦女以非暴力的方式封鎖了基地的入口。”[3](27)此外,1981年在加利福尼亞州索諾馬州立大學召開了“婦女和環境:第一次西海岸生態女性主義者”會議。1987年,全美生態女性主義會議在南加利福尼亞大學召開,此次會議產生了巨大影響,生態女性主義運動從此進入了公眾的視野。生態女性主義運動促進了兩個社會組織的發展:“婦女—地球女性主義和平研究所”和“環境與發展婦女組織”(WEDO)。“婦女—地球女性主義和平研究所”是由伊內斯特拉·金和斯塔霍克于1986年創建的,她們力圖使它成為一個非機構性政治組織。她們的目標是創建一個包括多種族的組織,這個目標要通過在各種會議上實行種族平等而得以實現。但是,這個組織于1989年宣告結束了。盡管這樣,對于許多曾經參加這個組織的人而言,種族平等的經驗是十分寶貴的。另一個組織——“環境和發展婦女組織”是由前美國國會女議員貝拉·阿布朱格和其他女性政治家于1989年創建的。WEDO是一個國際性的非政府組織,它把女性問題納入到發展和可持續性問題當中來。WEDO提出的問題中有許多都與不同種族、階級和國家的婦女生活密切相關。WEDO的許多目標也與生態女性主義的目標是一致的。1991年,由WEDO在邁阿密組織召開“為了健康的星球世界婦女代表大會”。這次會議是為1992年在巴西里約熱內盧的地球峰會做準備。1995年,在俄亥俄州立大學舉行了“生態女性主義視野”的會議。同一年,戴蒙德和麥茜特在俄勒岡格萊夫山創立了“生態女性主義者營地”。
在生態女性主義的發展過程中,伊內斯特拉·金有意識地把女性主義理論中相互沖突的各個理論流派的觀點結合起來,力圖建構更加一致的生態女性主義理論。金試圖發展一種“激發我們烏托邦的想象、體現我們最深層的思想改革的女性主義,這種女性主義是對我們的想象的肯定,對父權制的否定”[4](202)。她意識到生態女性主義理論的分裂削弱了它作為一種政治行動的力量,“女性主義需要合理的復魅,使精神和物質、存在和認識結合到一起。”[4](202)金指出,生態女性主義是由兩個部分組成,亦即生態女性主義運動和生態女性主義理論,這兩個部分是相互聯系的,共同構成生態女性主義。生態女性主義運動竭力推翻危及地球上生命的、歷史建構的政治和經濟結構,生態女性主義理論致力于顛覆支持所有壓迫形式的語言和意識形態系統。金強調,為了拯救地球和人類,這兩個部分必須辯證地共同發揮作用,“生態女性主義是和解和有意識地調停,是承認歷史的陰暗面和一千多年來婦女隱藏的無聲的行動……它是被壓迫者的回應——所有被壓迫者都被貶低、被否認,以便建立多重統治制度的父權制文明。它是被否定的、丑陋的、無聲者的潛在的聲音——所有這些事物都稱為‘女性氣質’。”[4](205)
三、古老的傳統智慧:生態女性主義的哲學淵源
女性與自然的聯系自古有之,這種聯系通過文化、語言和歷史長久地持續下來。生態女性主義者關注的焦點是:統治、擄掠婦女和自然究竟是從什么時候、在什么地方開始的? 美國文化史學家、社會思想家里安·艾斯勒和生態女性主義者查倫·斯普瑞特奈克認為這種統治模式可以追溯到大約公元前 4500年歐亞大陸的游牧民族征服印歐社會開始。
在西方歷史上的史前時期,人類居住在伙伴關系社會中,那時,男性地位和他們的社會職能并不在女性的地位和社會職能之上。那時的社會是非支配性社會,不是把地球當作人類獲取利益、取之不盡的資源,“它們具有一種生態意識,亦即人類應該敬畏地球。”[5](23)在柏拉圖時代(大約在公元前 427年——公元前348年),婦女孕育生命的權力仍受到敬畏,人們用藝術形式將其偶像化。在柏拉圖的著作中,他把世界看作是一個有生命的動物,他認為“神構造了一個看得見的動物,它包羅了具有相似本性的所有其它動物”。它的靈魂是一位女性,“在起源和卓越程度上都比身體更加居先、更加古老”,因而它“成為統治者和霸主,身體則成為它的臣民”。靈魂滲透于宇宙的有形身體之中,圍繞著身體并“在靈魂內部旋轉自身”。“‘作為我們的看護者’的地球則被置于宇宙不可變動的中心”。[6](11)女性被認為是受人敬畏的宇宙運動的源泉,與此類似,地球和地球的繁殖周期(如季節的更替等)也受到人類的敬畏,
女神不僅僅只是代表生命的繁殖,在許多社會里,女神崇拜行為包含了這樣的觀點:把地球當作一位創造和哺育生命的母親。婦女和地球的聯系使婦女和地球同樣受到敬畏。然而,隨著印歐人的第一次入侵,人類的伙伴關系社會終止了。印歐人帶來了憤怒的男性神祗,產生了彼此互相反抗以及反對外來成員的暴力傳統,他們贊美男性、男性的統治和壓迫,用暴力粗暴地掠奪地球,他們的宗教和社會觀念取代了古希臘、埃及、蘇美爾人關于人類和自然的非等級制關系的概念。婦女從事的維持生命物質基礎的工作逐漸遭到貶抑,隨之而來的是,與婦女工作有密切聯系用以滿足人類需要的自然資源(土壤、水、植物等)也遭到貶抑。農業的發展以及把動物和婦女視為奴隸,這些都鞏固和加強了男性的權力。由于這些變化,男性取代女性獲得了土地所有權,并且消滅了母系繼嗣。
人類從伙伴關系社會向父權制社會轉變的一個重要標志是男性主宰的宗教的發展。父權制下的猶太教與基督教的傳統貶低自然和婦女的價值。在希伯來《圣經》中,自然界和人類社會都是上帝創造和統治的,上帝是主宰所有生命的男性。以神學為基礎的希臘哲學此時也發生了激烈的轉變。柏拉圖設想了一種本體論的等級制:非物質的精神世界在物質的宇宙之上。在這個等級制中,“男性、女性和動物按降序排列。”[7](17)任何與女性和自然的“低等”特質相關聯的事物都遭到貶抑。當男性主宰的基督教和猶太教在全世界傳播開來后,女神崇拜衰落了。那些繼續女神崇拜,拒絕信奉男性神——上帝的人被視為是巫師,是罪人,受到殘忍而痛苦的懲罰。
“統治”的思想(男人統治女人、人類統治非人類生命)牢牢占據了宗教和哲學中的位置,同時,也成為文學藝術中一種牢固的觀念。文藝復興時期流行的田園詩將自然符號化為一位善良、仁慈的女性,默默地向世人奉獻她的慷慨。“在田園意象中,自然和女人都是從屬的、本質上被動的……這種田園模式包含著這樣的意思,即耕種和培育著的自然可作為一種商品來利用,作為一種資源來控制。”[6](10)
婦女在社會中扮演角色的顯著變化是資本主義和現代科學發展的結果。前現代社會里,在農業生產中,婦女勞動提供了家庭生存的物質基礎。婦女日常的勞動——種植糧食、準備食物、生育、撫養孩子,作為一種對人類社會的基本貢獻而受到尊敬。隨著資本主義的興起和發展,勞動變成了可以估價的事物。在資本主義社會里,利潤是由剩余價值轉化而來的,由于婦女的勞動不能創造剩余價值,婦女的勞動也就不能產生利潤,所以也就沒有價值可言。由此得出結論:婦女的勞動對社會沒有做出貢獻。當男人成為資本主義企業的雇傭勞動力后,他們不再可能是土地所有者,土地被資本家侵占,這進一步減少了女性為家庭提供資源的可能性。即使女性在家庭之外能找到工作,她們的收入也大大低于男性,她們作為母親的身份被認為是最主要的,排在第一位,而收入僅僅是補充性的,而且婦女在外工作時,家庭的健康和營養也會受到影響。因此,婦女被認為不適合扮演資本主義勞動力的角色。
隨著資本主義的擴張,婦女逐漸喪失了她們擅長領域的控制權,雖然她們曾經在這些行業中為人類的生存提供了必需的產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轉變是醫學的發展,它使婦女遠離了看護孩子的工作,甚至可以取代她們的生育。17世紀末,生孩子成為了男醫生和“男助產士”手中的活。[6](171)現代科學則走得更遠,它甚至否認婦女在生育過程中的重要性。英國人威廉·哈維在研究了雞的生殖過程之后,把它與人的懷孕及分娩過程進行比較并指出,“女性單獨不足以產生胚胎并養育和保護幼體,男性生來就與她結合,作為優越者和更有價值的始祖,作為她分娩的伙伴和彌補她不足的手段。”[6](174)到了17世紀中葉,認為“女性精子”對生育并不做貢獻的觀點仍然很有影響。進入19世紀,達爾文理論被發現對婦女有社會意義,可以作為意識形態用來維持婦女原有的位置。在達爾文理論的指導下,科學家們比較了男性和女性的頭骨和腦的各部分的大小,以證明性別差異的存在,解釋女性智力較低下和易動感情的氣質。20世紀,“男女之間激素的差別曾被用來暗指那些顯示出智商較高,有競爭性行為,有領導和行政才能的婦女的男性激素處在異常水平。”[6](179)
資本主義的發展和現代科學的進步導致了對自然環境的統治和破壞。現代科學之父弗朗西斯·培根提出:把自然視為機器而非活的有機體。這一新的世界觀成為了現代實驗科學的基礎。“強制自然于實驗室中,用手和心來解剖它,進入自然最隱密之處”。[6](171)培根和他的追隨者們改變了人類看待自然的觀點,自然從一個萬物有靈、有機的原始社會變成了一個為滿足人類社會需要而被人類操縱的機械的框架。人類看待自然的觀點的轉變導致了“自然之死”,這種觀點使人類操縱自然的行為合法化。
生態女性主義理論家卡洛琳·麥茜特指出,機械論的世界觀導致了對自然和女性的壓迫。這種機械論的世界觀使人們相信,科學研究是力圖尋找客觀的、價值中立的、無關境域的知識。這種機械的自然觀把權力與秩序的概念作為理解社會所必需的要素,在爭取權力和維護秩序的過程中,產生了牢固的等級制價值觀體系。在這個體系中,擁有權力最多的人具有控制他人的合法權利,其結果是大大削弱了一個主張人人平等的人類社會的生存能力和地球持續發展的能力。基于上述原因,生態女性主義者對科學主義進行了質疑和批判。
四、結語
當下,生態女性主義被認為是西方女性主義的最新思潮,已成為“女權主義理論中最有活力的派別之一”。[8](286)生態女性主義流派眾多,觀點各異,表現出兼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征。但是不管各流派的生態女性主義之間存在多大的分歧,所有的生態女性主義者都相信,統治自然與壓迫女性之間有著密切的關系。美國女性主義者羅斯瑪麗·雷德福·盧瑟在她的書中指出:“婦女們必須看到,在一個以統治模式為基本關系模式的社會里,不可能有自由存在,也不存在解決生態危機的辦法。她們必須將婦女運動與生態運動聯合起來,以實現重建基本的社會經濟關系和支撐社會價值觀的目的。”[9](204)基于這一觀點,生態女性主義者批判男性中心主義,力圖建立一個以生態主義和女性主義原則為標準的、可持續發展的社會,主張改變人類統治自然的思想,改變導致剝削、統治和攻擊性的價值觀。因此可以說,生態女性主義是一種生活態度和生活實踐。
此外,從生態女性主義產生的語境來看,它與人類對自然生態和文化生態的雙重反思有關,是人們對自然生態危機、人類社會危機和人類精神危機的出現所做出的積極反應。從生態女性主義的溯源中,我們發現,誕生于20世紀70年代的生態女性主義運動思潮是生態女性主義理論的基礎與現實依據。生態女性主義是女性主義的一個新的分支,一種后現代主義的文化思潮,然而它的歷史淵源可以上溯至史前時期,這表明,婦女與自然的聯系自古有之,這種聯系通過文化、語言和歷史長久地延續下來。在當下,人類關注這個古老的問題,對其做出新的解釋,為我們提供了審視和評價當代社會的新視角,并將產生變革現實的力量。
[1]Francoise D’Eaubonne.The Time for Ecofeminism[C]// Carolyn Merchant.Ecology.New Jersey: Humanities Press,1994.
[2]Karen J Warren.Ecofeminist Philosophy: A Western Perspective on What It Is and Why It Matters [M].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2000.
[3]Ynestra King.The Ecology of Feminism and the Feminism of Ecology [C]// Judith Plant.Healing the Wounds: The Promise of Ecofeminism.New Society Publishers,Santa Cruz,1989.
[4]Ynestra King.Feminism and the Revolt of Nature[C]// Carolyn Merchant.Ecology.New Jersey: Humanities Press,1994.
[5]Riane Eisler.The Gaia Tradition and the Partnership Future: An Ecofeminist Manifesto[C]// Irene Diamond and Gloria Orenstein.Reweaving the World: The Emergence of Ecofeminism.San Francisco: Sierra Club Books,1990.
[6]麥茜特.自然之死[M].吳國盛譯.長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
[7]Rosemary Radford Ruether.Ecofeminism[C]// Carol J.Adams,Ecofeminism and the Sacred.New York: Continuum,1993.
[8]多諾萬.女權主義的知識分子傳統[M].趙育春譯.南京: 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
[9]Rosemary Radford Ruether.New Woman/New Earth[M].New York: Seabury,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