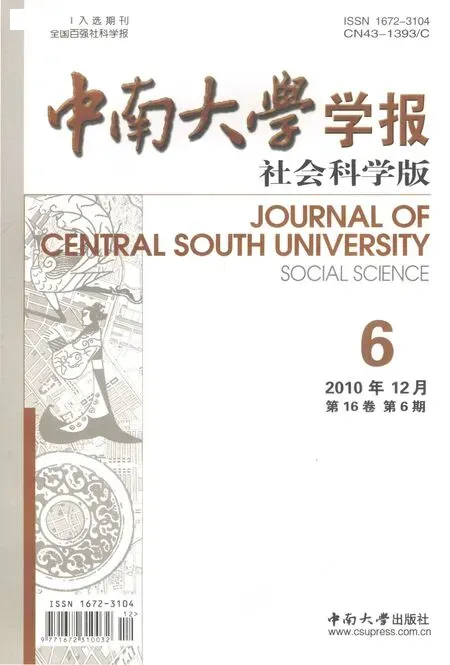翻譯與共謀——后殖民主義視野中的譯者主體性透析
屠國元,朱獻瓏
(中南大學外國語學院,湖南 長沙,410083)
后殖民主義以殖民時代之“后”殖民地與宗主國之間的文化權力和話語關系,以及由此產生的種族主義、文化帝國主義、文化身份等問題為研究課題,是一種具有鮮明的政治意識形態色彩的文化批判思潮。后殖民主義涵蓋了哲學、歷史、心理學、人類學、文化學等多個學科領域,同時攝取了多種理論批評方法,如女性主義、解構主義、新馬克思主義等,因此幾乎無法把后殖民主義界定為某一“理論”或“主義”。正是由于理論的包容性和延展性,后殖民主義成為各種思潮和學說的融匯交鋒之地,迸發出強勁的理論活力。后殖民主義譯論是翻譯研究發生“文化轉向”之后的重要理論緯度,深刻揭示了翻譯的文化屬性和文化功能,為譯者主體性研究開辟了新的思考視角。
一、作為共謀者的翻譯
在后殖民主義著述中,翻譯頻頻登臺亮相,成為不同文化、種族之間權力交織的矛盾集合體。按照羅賓遜的看法,翻譯在三個層面發揮了重要作用:①在殖民化過程中充當殖民主義建構主體性的工具;②在殖民主義時代結束之后,成為維護文化等級秩序的“避雷針”(lightning rod);③在解殖民化(decolonization)過程中,成為被殖民者擺脫殖民枷鎖、削弱文化霸權的工具。[1](31)殖民者借助翻譯在潛移默化之中完成了主體性和殖民話語的塑造,并逐漸為被殖民者所認同和接受。翻譯成為殖民主義借以維護文化等級秩序和不對稱權力關系的重要途徑,翻譯儼然成了“帝國的殖民工具”。在長期的殖民化統治下,被殖民者不得不在殖民者虛構的鏡像中來解讀和關照自身的生存境況,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宗主國與殖民地之間的文化等級秩序——前者高雅后者庸俗、前者文明后者野蠻,前者聰慧后者愚笨等等——進而造成了被殖民者“我不如人”的強烈自卑感甚至走向自我殖民,殖民者正是通過這種不平等的話語等級體系來維護自己的殖民統治。在赤裸裸的殖民統治結束進入經濟全球化時代之后,殖民主義改頭換面,通過大眾傳媒、學術交流、經濟擴張等更加隱蔽的形式實施其文化殖民的戰略。
尼蘭賈娜在《為翻譯定位》一書中通過考察印度殖民時期古典作品英譯史,揭示了翻譯與殖民主義的共謀關系,“殖民基業里所隱含的馴服/主體化(subjection/subjectification)的行徑,并非僅僅是通過帝國的強制機器得以實施的,它們同時也借哲學、歷史學、人類學、語文學、語言學以及文學闡釋這種種話語得以推行。……作為一種實踐,翻譯構塑了殖民狀態下不對稱的權力關系。”[2](117)傳統意義上的翻譯以“實在、再現和知識”等在場形而上學概念體系為基礎,知識就是對實在的再現。再現式的翻譯可以創造出通順的、透明的、超越的文本,并通過哲學、史學、傳記等不同話語形式參與到殖民文化的構建和定型過程中,遮蔽殖民主體構建過程中的暴力,達到延續和強化殖民統治的目的。翻譯通過再現“他者”的某些模式,呈現出另一種形態的“他者”,并藉此制定出“遏制”他者的策略。在殖民文化語境下,這種再現式的翻譯滲透到殖民統治的霸權機制之中,在再現被殖民者的過程中,抹殺其中的權力關系和歷史性,“翻譯強化了對被殖民者所作的統識性描述,促成其取得愛德華·薩伊德稱之為再現或無歷史之客體的地位。”[2](118)尼蘭賈娜以瓊斯的翻譯活動為例,“瓊斯著作里最富意味之處包括:1)由于土著民對其自身的法律和文化的闡釋不足為信,所以必需由歐洲人來作翻譯;2)極想做一個立法者,給印度人制定他們‘自己的’法律;3)極欲‘凈化’印度文化并代為其言。”[2](126)經過瓊斯文本加工之后的印度人成為“一付懶懶散散、逆來順受的樣子,整個民族無法品味自由的果實,卻祈盼被專制獨裁所統治,且深深地沉溺在古老宗教的神話里”。[2](126)殖民者通過翻譯抹殺了隱藏殖民化過程中的主體性、歷史和權力等因素,遮蔽了殖民主體構建過程中的暴力行徑。翻譯研究“所忽略的似乎不僅是貫穿于翻譯里的權力關系(power relations),而且還有譯本的歷史性或效應史(historicity or effective history)”。[2](170)翻譯淪為殖民者構建其主體身份的工具,成為不同語言、文化、種族之間不平等權力關系的載體。后殖民主義的歷史使命就是要解除這種殖民主義話語,即所謂“解殖民化”,“解除殖民化的不良影響的漸進過程,尤其是指解除殖民化狀態下的集體自卑情結……由于無法完全消除殖民化的歷史痕跡,在現實意義上,解殖民化意味著在發展中逐步超越殖民主義的精神遺存,并將其融入到轉型后的文化之中”。[1](115)解除殖民化必須首先在還原殖民主體建構過程的基礎上,揭穿殖民主義話語的謊言,還文本生成以本來面目,讓深藏其中的權力差異顯露出來。在后殖民語境下,翻譯再次成為“工具”——成為處于文化邊緣的弱勢族群抵制文化霸權、重塑文化身份的工具。
二、后殖民主義語境下的翻譯策略
后殖民主義譯論完全拋棄傳統的內部研究,將翻譯納入更為宏大的后殖民話語體系之中,揭示文本生產中的歷史的、政治的、意識形態的因素以及隱藏其中的不對稱權力關系,借助翻譯所具備的建構文化主體身份的功能,消解殖民話語、抵制文化霸權,實現“解殖民化”的歷史使命。綜合起來看,解殖民化的主要途徑有三:雜合化、食人主義以及抵抗式翻譯(異化策略)。
(一)雜合化策略
霍米·巴巴(Homi Bhabha)在《文化的定位》(The Location of Culture)一書中指出,全球化時代的文化定位既不能以普遍性為旨歸,也不可以將文化差異規范化或標準化,更不能走向狹隘的民族主義,文化只存在于不同文明接觸的邊緣和疆界處或是一種邊界協商,與之伴隨的是居間的、雜糅的“多種聲音”。巴巴正是借助這種獨特的雜糅策略向帝國主義和文化霸權發起挑戰,進而嘗試營造文化多樣性的格局,文化的雜糅(或雜合)也成為后殖民主義研究者的共識。巴巴認為,“雜合化”(hybridization)是不同種族、文化、語言、意識形態彼此混雜的過程,是殖民地和弱勢文化顛覆和瓦解文化霸權的一種抵抗性策略。基于此,巴巴創造出了“第三空間”的概念,以“挑戰文化的歷史認同感”,瓦解強勢文化與弱勢文化、“自我”與“他者”的二元對立,不存在原創的、“純潔”的文化體系,文化之間亦不存在高低貴賤,所有文化的身份只有在這個矛盾的、模糊的闡釋空間中才能得以構建,“在自由地在斷裂的、暫時的互文性文化差異中通過翻譯和協商來顯示自己的文化身份”。[3]第三空間所具備的模糊性、矛盾性和無意識性能夠去除文化的原始統一性和固定性,文化的差異性得以留存,文化間的沖突得以化解,從中衍生出一種“非我非他”的文化的雜糅話語形式。雜糅化既可以幫助弱勢文化或邊緣族群擺脫身份壓迫和文化遏制,還可以讓強勢文化意識到自身文化語言的異質性,丟掉普遍主義和自我中心主義的幻想。巴巴引入了文化翻譯(cultural translation)的概念來構建自己對文化觀,“在文化翻譯過程中,會打開一片‘間隙性空間’(interstitial space)、一種間隙的時間性,既反對回到一種原初的‘本質主義’自我意識,也反對放任于一種‘過程’中的無盡的、分裂的主體”,[4]在傳統民族疆界消失、中心坍塌之后,文化成為一種翻譯式的、邊界協商式的意義生產過程,而巴巴就是要利用這種雜糅的空間或方式來喻說一種“翻譯式”的世界主義。
翻譯成為塑造文化身份的重要途徑,成為一種不同文化差異性的商討和協調過程。譯者在這一過程中起到了協調者或斡旋者的角色,兩種文化和語言在譯者的引領下進入“第三空間”進行協商、交流、碰撞和融合。徘徊于目的語與源語文化之間的譯者本身的行為也具備了相當的雜糅性,他的文化認知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目的語文化對源語文化的態度,盡管他主觀上努力采取抹去自身痕跡的異化策略,或者采取抹去原作異質性的歸化策略,但讀者在最終的譯本中總是既可以看到語言文化的“異域性”或“新穎性”,又可看到本土文化的印跡和譯者自身的介入,譯本因此成為一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充滿不同聲音的雜合體。與其他后殖民主義學者一樣,尼蘭賈娜倡導將翻譯視為“抵抗與變革的陣地”(a site for resistance and transformation),主張運用雜合化的策略來抵抗殖民話語和文化霸權。尼蘭賈娜提倡重譯印度及其他舊殖民地的文本,但她并不主張徹底抹去殖民者印跡的極端民主主義或本土主義(nationalism and nativism),或呈現所謂的普遍主義的元敘述局面(meta-narrative of global homogenization),而是要以一種非本質主義的方式消解不同文化間的對抗性。她借鑒了德里達的引用性(citationality)理論,將翻譯視為一種重讀/重寫歷史的過程,主張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重新解讀和翻譯印度和其他殖民地文本,通過“引用”(cite)或“引證”(quote)殖民者的話語實現文化的重新轉換。尼蘭賈娜贊同本雅明為顯現“純語言”而倡導的直譯,“‘引用’或‘引證’近似于翻譯中的直譯(literalness)。對本雅明而言,直譯意味著翻譯單位不應是句子而是單詞,‘翻譯不應該用以傳達信息,而是用以反映原文的句法’”。[5]尼蘭賈娜的重譯理論是雜合化策略的一種體現,雜合化是“指向一種新的翻譯實踐的同時又顛覆了本質主義閱讀模式的一種后殖民理論的標志”。[2](154)除尼蘭賈娜以外,梅勒茲(Samia Mehrez)、謝莉?西蒙(Sherry Simon)、拉菲爾(Vicente L.Rafael)等學者都著力運用雜合化翻譯策略消解文化中心主義和普遍主義,凸顯文化的差異和多元,從不同側面繼續推進雜合化的研究。
(二)巴西的食人主義
在擺脫葡萄牙殖民統治之后,巴西人民開始反思自身的文化發展模式,并逐漸意識到在獲得政治獨立的同時,還存在著與歐洲嚴重的文化依附關系,文化身份變得越來越模糊。1928年,巴西現代主義者奧斯瓦爾德·安德拉德(Oswald de Andrade)發表了《食人主義宣言》,主張只有“吞食”歐洲文化,才能擺脫文化上的依附、尋求文化身份認同,繼而在權力關系網絡中爭取主動。食人主義源自巴西土著部落的一種儀式,食人是懷著敬意和有特殊用意的:食人是為了獲取力量,精神的或肉體的,或兼而有之。食人主義者只吞食三類人: 強壯的人、有權勢而且受人尊敬的人、通靈通神的人。[6]“吞食”意味著背離,同時還包含著對被食者的尊敬。在巴西理論界,食人主義思想逐漸內化為一種共同的精神信念。20世紀60年代,德坎波斯兄弟(Haroldo & Augusto de Campos)將食人主義引入翻譯研究領域,同時借鑒了解構主義思想,建構起了一種后現代的、非歐洲中心主義的(non-Eurocentric)食人主義譯論。德坎波斯兄弟將翻譯視為一種跨文化的侵越(transgression),或弒父的行為(a form of patricide),他們拒斥對原作的任何預先設定以及亦步亦趨的復制和再現。在德坎波斯看來,翻譯并不是將原文強行占有,而是一種讓原文得以解放的方式,通過吞食原文、汲取原文的精華,擺脫原文的束縛獲得自由。因此,翻譯成為一種汲取力量的行為(empowering act)、攝取營養的行為(a nourishing act)和具有認同功能的行為(act of affirmative play),原語文本通過翻譯獲得了重生,延續了自身的生命歷程,譯作成為原作的“來世”(afterlife),這種理念與本雅明和德里達的解構主義一脈相承。[7]在翻譯實踐層面,德坎波斯兄弟翻譯了大量東西方文學經典,如《荷馬史詩》、希伯來語的《圣經》、但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甚至還將龐德翻譯的中國古詩進行二度翻譯,帶著“愛與尊敬”(love and reverence),將異域的文學經典咀嚼、消化,為巴西文化輸入新鮮的血液。翻譯總是意味著創作和超越,異域文本進入本土文化必然意味著變形,即以本土文化框架為依歸肢解和重組原文,從而使譯文呈現出一種全新的面貌,因此食人主義通常采用類似于“歸化”的翻譯策略。譯者在翻譯過程中享有充分的自由選擇權,可以基于本土文化的訴求改造、移植甚至挪用原作中的異質成分。德坎波斯兄弟的食人主義思想在翻譯實踐中不斷得以豐富,并根據所譯文本的主題或意像創造出一套獨特的術語,如在翻譯中國古典詩詞時提出了“再度想像”(reimagination),在翻譯《神曲》時提出了“移轉光明” (translumination)、“移轉天堂”(transparadisation),在翻譯《浮士德》時提出了跨越文本(transtextualization)、再次創造(transcreation)、移植魔鬼(transluciferation),在翻譯的《伊利亞特》時提出了移植海倫 (transhelenization),在翻譯《圣經》時提出了“重譜詩歌樂曲”(poetic reorchestration),此外還有去除弒父記憶(a patricidal dis-memory)等術語。[8]在后殖民語境下,食人主義思想既可以擺脫殖民主義的文化同化和文化滲透,又可以有效規避狹隘的民族主義和本土主義傾向,因此它對弱勢文化族群解除殖民化、削弱文化霸權、重塑文化身份有極強的借鑒意義。
(三)韋努蒂的抵抗式翻譯
韋努蒂(Lawrence Venuti)將傳統的歸化、異化翻譯策略植入后殖民語境之中,賦予其強烈的權力和政治色彩,視翻譯為一種“文化政治實踐”。韋努蒂通過考察17世紀以來的英美翻譯史發現,其間的譯者大多以本土的語言文化價值觀為基點,采取歸化式的翻譯策略改寫外國文學作品。譯本通順易懂、自然流暢,甚至看不出翻譯的痕跡,也尋不見譯者的蹤跡(invisible);在原作的選擇以及內容的增刪等方面均以英美文化審美偏好為依歸,如龐德的《華夏集》便采用了歸化的策略,無視其中特有的文學和文化元素,將中國古典詩歌改造為意象派詩歌,譯本因為迎合了目的語文化的口味獲得了極大成功。然而,這種透明的翻譯背后卻隱藏著民族中心主義和英美霸權主義的價值觀,通順、易懂的譯本隱含了歐美強勢文化對弱勢文化的壓制以及不對稱的權力關系。“流暢譯法的目的在于不讓譯者介入外語文本之中,譯者主動地用另一語言重寫原文,再讓譯文在另一種文化里流傳。但這一過程帶來的卻是自我毀滅,最終把今日的譯者擠到文化邊緣,……流暢譯法也抹掉了外語文本在文化和語言上的差異。這種重寫使譯作以透明易懂的譯語的主流文化為依歸,甚至不可避免地表達了譯語的價值觀、信念和社會楷模,把翻譯牽連到不同的社會意識形態里去……在這種重寫過程中,流暢策略就擔任了一項文化移入的工作,把外語文本歸化,使譯語讀者不但明了熟識文章意義,并且從中滿足自戀情懷,在他方文化里認出自己的文化。這樣,一場帝國主義擴張話劇又在上演著,他方的意識形態通過‘透明’譯法擴充了它的版圖,進入了另一個文化領域里去。”[9](241)韋努蒂稱之為翻譯“最大的丑聞”,“不對稱、不對等、占有與依附的關系在翻譯行為中屢見不鮮,原語文化不得不俯首聽命于譯語文化。譯者成了剝削異域文本和文化的共謀”。[10]歸化的翻譯成為殖民者的“幫兇”,弱勢文化不得不聽命于英美強勢文化的擺弄,歸化的翻譯成了殖民者進行文化殖民和強化殖民意識形態的共謀,它不僅幫助殖民者撒播話語權力,實施文化侵吞,而且在被殖民一方的意識中不斷強化他們自我他者身份的認同。對譯入英美文化的外國文本所采取的歸化的翻譯策略所作的本質揭示,使歸化策略在后殖民主義翻譯批評中遭到了譯論家們的指責和唾棄。[11]韋努蒂呼吁創立一種“存異倫理”,主張運用“抵抗式”的翻譯策略,在翻譯過程中采用背離本土語言文化規范的混雜文體,向讀者呈現充滿文化異質性的外國文本,讀者面對譯本不應有“似曾相識”的感覺,而是陌生感甚至疏遠感,文化的差異由此才得以體現。“抵抗式的策略可以生成既陌生又怪異的譯文,有助于保留異域文本中的語言和文化差異性。如此就可以劃清譯入語文化主流價值標準的界限,還可以阻止這些標準把他者文化納入譯入語帝國的疆域之內。”[9](250)異化策略成為抵制民族中心主義、種族主義、帝國主義、文化自戀情結、重塑“他者”文化身份的重要途徑。
三、結語
“文化轉向”之后的翻譯研究不由自主地被卷入了文化、政治、權力、意識形態等語言之外的世界之中,翻譯的文化屬性和文化功能得到史無前例地高揚,透明式的、再現式的翻譯忠實觀被徹底拋棄,原作/譯作、作者/譯者的二元對立被拆解,原作者的權威及文本意義的普適性消解于譯者的積極介入和意義的無限延異之中。透過紛繁龐雜的后殖民主義譯論,追問“身份”成為共同的訴求,體現現出強烈的“身份焦慮”(the anxiety of identity),引發了改變自身弱勢或邊緣地位的反叛和抵抗。被殖民者和弱勢文化族群在殖民主義和文化霸權的壓制下陷入失語的境地,文化身份的日益邊緣化和模糊化。“身份”對他們而言,不是本質主義模式下面各種屬性的集合,而是一種文化的建構或話語的建構。他們一方面質疑被傳統翻譯觀念和翻譯實踐所固化的等級二元,另一方面將翻譯作為一種行為性(performative)的話語實踐,來服務于議定文化身份的動態過程。[12]后殖民主義將翻譯視為解殖民化的工具,翻譯本身就成為一種政治行為,通過翻譯的雜合化策略去除文化的普遍性和同一性,借助抵抗式的異化策略凸顯文化的差異性,甚至將強勢文化直接“吃掉”來獲得文化身份的認同。后殖民主義譯論將譯者推向了權力網絡的中心,凸顯了譯者的主體性作用,譯者及其翻譯實踐成為重塑身份、彰顯差異的最為重要的一環,或者說,譯者本身就是話語,翻譯成為譯者表達自身及其所屬群體文化訴求、重塑文化身份的載體或工具。
[1]Robinson,Douglas.Translation and Empire: Postcolonial Theories Explained [M].Manchester: St.Jerome Publishing,1997.
[2]許寶強,袁 偉.語言與翻譯的政治[M].北京: 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
[3]Bhabha,Homi K.The Location of Culture [M].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1994.
[4]Bhabha,Homi K.The Post- colonial Question: Common Skies,Divided Horizons [M].London: Routledge,1996.
[5]Niranjana, Tejaswini,Siting Translation: History,Post-structuralism and the Colonial Context [M].Berkeley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2.
[6]蔣驍華.巴西的翻譯:“吃人”翻譯理論與實踐及其文化內涵[J].外國語,2003,(1): 63?67.
[7]Gentzler,Edwin.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M].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1993.
[8]Bassnett,Susan & Trivedi,Harish.Post-Colonial Translation:Theory and Practice [C].London: Routledge,1999.
[9]陳德鴻,張南峰.西方翻譯理論精選[M].香港: 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00.
[10]Venuti,Lawrence.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 Towards an Ethics of Difference [M].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1998.
[11]葛校琴.當前歸化/異化策略討論的后殖民視閾[J].中國翻譯,2005,(5):32?35.
[12]曾記.“忠實”的嬗變: 翻譯倫理的多元定位[J].外語研究,2008,(6): 7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