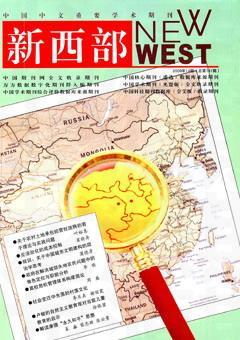生存還是毀滅
[摘 要] 生存還是毀滅?道德理想徹底破滅之后的竇娥,同樣遭遇到這一哈姆雷特式的自我拷問(wèn)。與其說(shuō)竇娥出于孝道而甘愿屈招受死,不如說(shuō)竇娥是以孝道的名義走向了死亡。當(dāng)殘酷的生存困境已經(jīng)剝奪了她生的希望,對(duì)道德的堅(jiān)守也已經(jīng)失去意義之后,死亡作為反抗生的絕望、掙脫生存困境的唯一方式,就成了竇娥的一種帶有自主性的人生選擇。
[關(guān)鍵詞] 《竇娥冤》;文化屬性;生存困境;悲劇指向
竇娥的死亡,是《竇娥冤》文本敘述中最具心理震撼效應(yīng)的事件,這也從根本上鑄就了這一文本的悲劇品格。同時(shí),我們只有通過(guò)客觀地還原竇娥走向死亡之前的心路歷程,才能對(duì)竇娥這一悲劇典型的悲劇內(nèi)涵做出比較準(zhǔn)確的闡釋。本文認(rèn)為,死亡,是竇娥的自覺(jué)選擇,也是她反抗生的絕望的唯一方式。
一、竇娥的文化屬性
痛苦和災(zāi)難,是竇娥短暫的一生始終無(wú)法掙脫的夢(mèng)魘。她三歲喪母,七歲以身抵債,十七歲完婚,當(dāng)年丈夫就死去。對(duì)于她來(lái)說(shuō),一切還沒(méi)有開(kāi)始,就已經(jīng)結(jié)束。竇娥一出場(chǎng)的唱詞,便表達(dá)了她內(nèi)心極深的痛苦:“滿腹閑愁,多年禁受,天知否?天若是知我情由,怕不待和天瘦。”([仙呂點(diǎn)絳唇])[1]P10她心中郁悶,愁苦萬(wàn)分,見(jiàn)花墮淚,望月傷懷,“長(zhǎng)則是急煎煎按不住意中焦,悶沉沉展不徹眉尖皺”([混江龍])[1]P10,生活中除了一連串不幸所帶來(lái)的心靈創(chuàng)傷與磨難,已沒(méi)有任何屬于她自己的歡樂(lè)可言。竇娥就這樣默默地忍受著難以想象的悲哀,苦苦地熬著光陰。究竟是什么力量在支撐她這備受折磨的生命?
竇娥和其他古代婦女一樣,長(zhǎng)期處于“三綱五常”封建禮教的桎梏下,逐漸形成了順從忍讓,自輕自賤的心理特征。她們很容易將現(xiàn)實(shí)苦難的根源歸諸為“命定”,她們虔誠(chéng)地相信“生死有命,富貴在天”的天命觀。竇娥相信命運(yùn):“莫不是八字兒該載著一世憂,誰(shuí)似我無(wú)盡頭?”([油葫蘆])[2]P11“莫不是前世里燒香不到頭,今也波生遭禍尤?”([天下樂(lè)])[1]P11我們看到,對(duì)命運(yùn)的無(wú)奈和屈從,使得竇娥只能從宗教中去尋找精神安慰和支撐。既然今生苦難是前世注定,為了來(lái)世脫離苦海,她告誡自己:“我勸今人早將來(lái)世修”([天下樂(lè)])[1]P11,這成了她繼續(xù)活下去的動(dòng)力和支撐。誠(chéng)如馬克思所說(shuō)“宗教是被壓迫生靈的嘆息,是無(wú)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沒(méi)有精神狀態(tài)的精神一樣。宗教是人民的鴉片”,[2]那么,如何修來(lái)世呢?竇娥的回答是:“我將這婆侍養(yǎng),我將這服孝守。”([天下樂(lè)])[1]P11顯然,遵循儒家的倫理綱常,盡孝守節(jié),就是修來(lái)世唯一的也是最好的途徑。從竇娥的心理流程及思想軌跡中,我們清楚地看到儒家的倫理道德是如何與宗教聯(lián)姻的。
基于對(duì)封建婦女道德的自覺(jué),竇娥把捍衛(wèi)貞潔當(dāng)成了生命的全部。在文本敘述中,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竇娥始終是以恪守貞節(jié)而自詡的。可以說(shuō),“‘貞節(jié)觀念,全然是支持著竇娥生存、思考、行動(dòng)的道義力量”[5]P72。在劇中反抗男性野蠻逼嫁的行為,被竇娥提升到了“烈女不嫁二夫”的高度。她對(duì)男人無(wú)端逼迫女性再嫁的荒淫、野蠻行徑的斥責(zé)——“好色荒淫漏面賊”,也是建立在這樣的婚姻觀基礎(chǔ)上的。她甚至認(rèn)為,自己之所以遭受懲罰,就是因?yàn)檫`背了這一婚姻觀。在刑場(chǎng)上被殺戮之前,竇娥除詛咒天地之外,對(duì)自己遭受殺身之禍的根源作了剖析:
[罵玉郎]這無(wú)情棍棒教我捱不的。婆婆也,須是你自做下,怨他誰(shuí)?勸普天下前婚后嫁婆娘們,都看取我這般傍州例。(第二折)[1]P22
總之,我們看到,“竇娥的感性生命及人的自然欲求,都已被儒教的理性規(guī)范及濃厚的宗教意識(shí)所代替。她立志守節(jié),以自己的苦行苦修、性似寒冰去換取來(lái)世的幸福。這使她甚至對(duì)合乎人道的生活,對(duì)人們的自然情感,哪怕是一點(diǎn)點(diǎn)的溫情,都難以接受,甚至是非常的反感、厭惡。”[3]P77只有從這一深層被異化的文化心理中,我們才能理解為什么竇娥對(duì)婆婆的改嫁持那么憤激的反對(duì)態(tài)度,就連婆婆生病,張?bào)H兒的父親殷勤照顧,她也百般看不慣:“一個(gè)道你請(qǐng)吃,一個(gè)道婆先吃,這言語(yǔ)聽(tīng)也難聽(tīng),我可是氣也不氣!”竇娥極端的態(tài)度充分表明,“守節(jié)”對(duì)于她來(lái)說(shuō),“已是一種可以為之獻(xiàn)身的宗教化了的精神情感。從正常人性的角度講,她不僅對(duì)婆婆無(wú)情,對(duì)自己更是無(wú)情,而恰恰是這一點(diǎn),讓我們今天的人們痛切地感受到古代宗教倫理的‘性禁錮對(duì)婦女心靈和肉體的殘害是多么深重!”[3]P78
通過(guò)事例分析,我們發(fā)現(xiàn)在竇娥的文化基因里,并不具有反封建的因素。由于自幼就有儒生父親的嚴(yán)格訓(xùn)教,加之在以身抵債之后為能獲得蔡婆一家的認(rèn)同,無(wú)論是出于自覺(jué)還是出于目的,竇娥終究是把自己打造成了一個(gè)三從四德的虔誠(chéng)的信奉者,她把封建禮教所鼓吹的“孝子賢孫”的孝道觀和“從一而終”的貞節(jié)觀當(dāng)作自己苦難人生的精神支撐,當(dāng)作實(shí)現(xiàn)其生命價(jià)值的理想家園,守節(jié)和盡孝成為她生命延續(xù)的最后的意義。她一生都在不自覺(jué)地用封建的道德鬼魂恐嚇自己,并有意識(shí)地要把自己打造成一架封建的婦女道德的演示器。她要通過(guò)對(duì)那套非人的道德準(zhǔn)則的“堅(jiān)守”,來(lái)生發(fā)出一種“真實(shí)”的道德優(yōu)越感,并以這種優(yōu)越感來(lái)填充自己那痛苦而虛無(wú)的生命。
在艱難的生存情勢(shì)下,竇娥只能以道德上的那虛幻的自我崇高來(lái)維持生命。在一種帶有憐憫和同情的道德評(píng)價(jià)的包圍中,一個(gè)青春的生命在“人”的層面上本應(yīng)具有的欲望和渴念,只能在道德化的軀殼中逐漸窒息并最終死亡。
二、竇娥的生存困境
在追究竇娥的死因時(shí),以往的論者多從社會(huì)批判的立場(chǎng)出發(fā),認(rèn)定以桃杌太守為代表的元代的腐敗吏治和以張?bào)H兒父子為代表的社會(huì)邪惡勢(shì)力,是致竇娥于死地的元兇。事實(shí)上,這一看似正義的定罪宣判,與《竇娥冤》的文本敘述之間并無(wú)清晰的邏輯關(guān)聯(lián)。以現(xiàn)代法律的視角來(lái)分析,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竇娥之冤是一個(gè)典型的司法悲劇。在傳統(tǒng)社會(huì)條件下,司法很難處理像竇娥這樣的案件,這種悲劇實(shí)際上不可避免。”[5]P96或者可以說(shuō),“竇娥的冤獄基本上是由于在法律上沒(méi)有確立無(wú)罪推定的結(jié)果”。[6]P128另外,一個(gè)可以被認(rèn)定的事實(shí)是,“劇本中也沒(méi)有任何證據(jù)表明甚或暗示判定竇娥死罪是因?yàn)樘诣皇帐芰藦報(bào)H兒的錢財(cái)。”[5]P98
那么,竇娥的非正常死亡的原因有該被如何解釋呢?本文認(rèn)為,死亡,是竇娥的自覺(jué)選擇,也是她反抗生的絕望的唯一方式。
自青春守寡以后,與蔡婆相依為命的竇娥,在主體意識(shí)中已經(jīng)自覺(jué)地樹(shù)起了一面守貞的大旗。因?yàn)?在她的文化意識(shí)中,對(duì)于一個(gè)年輕的寡婦而言,貞操就是她余下的生命的全部,捍衛(wèi)貞操,也就成了她在世的唯一價(jià)值。在行為的層面上,竇娥對(duì)自己的痛苦和不幸,有意識(shí)地選擇了遺忘,她不僅不言說(shuō)自己的痛苦和不幸,而且,把對(duì)這種痛苦和不幸的默認(rèn)和承受,變成了一種帶有崇高感的對(duì)封建統(tǒng)治秩序中的婦女道德的踐行和示范。她要通過(guò)這種姿態(tài),來(lái)使他人承認(rèn)自己在道德上的純潔性。
但是,市井流氓張?bào)H兒父子的闖入,尤其是蔡婆婆軟弱和最終的屈從(和張孛老在事實(shí)上的同居),使得竇娥對(duì)封建的婦女道德的堅(jiān)守失去了意義(這種“堅(jiān)守”的姿態(tài),既可以獲得來(lái)自輿論的保護(hù)和褒揚(yáng),也可以從對(duì)這種行為的“崇高”性的體驗(yàn)中,使自己那痛苦和絕望心靈獲得某種慰安)。一方面,對(duì)道德的忠誠(chéng)強(qiáng)化了生存中的絕望體驗(yàn),另一方面,流氓無(wú)賴張?bào)H兒根本不值得自己交付身心,也就是說(shuō),一方面,竇娥對(duì)所謂婦女道德的自覺(jué)事實(shí)上是荒謬的,另一方面,竇娥又無(wú)法正視自己違背“婦女道德”的罪惡(屈從于張?bào)H兒無(wú)理威逼)。
在文本敘述的層面上,本來(lái)打算在一種淡漠的凄涼中獨(dú)守百年的哀怨的竇娥,事實(shí)上已經(jīng)對(duì)苦難本身選擇了默認(rèn)的竇娥,自張?bào)H兒父子的強(qiáng)行闖入到意外地走上刑場(chǎng),其心理經(jīng)歷了由慌亂到絕望的變化。
起初,面對(duì)家中突然冒出的一對(duì)流氓父子,竇娥的第一反映是不知道該如何去繼續(xù)生活。婆媳倆寡婦同父子倆光棍在一起生活無(wú)論如何也是不正常的,而她又無(wú)力改變這種局面。(事實(shí)上,無(wú)力改變這種狀況的是竇娥而不是蔡婆婆,而蔡婆婆又不愿改變這種狀況)。在當(dāng)時(shí)的條件下,唯一可能和竇娥站在一起的就是蔡婆,蔡婆的動(dòng)搖和軟弱卻使竇娥處于孤立無(wú)援的境地。“她為了說(shuō)服蔡婆和自己站在一起對(duì)付張?bào)H兒父子的威逼,只有用‘一馬不鞴二鞍,好女不嫁二男的封建道德標(biāo)準(zhǔn)最有說(shuō)服力,因?yàn)楦]娥的守節(jié)不是為了別人,就是為了蔡婆的親生兒子。”[7]P92可以說(shuō),竇娥正是出于對(duì)封建的婦女道德的自覺(jué),才把自己的青春乃至在世的整個(gè)生命,當(dāng)成供奉丈夫亡靈的祭品。按理來(lái)說(shuō),蔡婆對(duì)竇娥的這種道德自覺(jué)和獻(xiàn)身精神應(yīng)心存感激才對(duì),至少在關(guān)鍵時(shí)刻不會(huì)由于自己的選擇而把竇娥推向道德的絕境。但這樣的一種看似極具情感力度的道德勸誡,對(duì)蔡婆這樣一個(gè)市井生存秩序中的女強(qiáng)人而言,卻沒(méi)有產(chǎn)生任何的效力。蔡婆最終的屈從,使竇娥在身份問(wèn)題上面臨空前的尷尬,也使她在“貞”和“孝”的選擇上陷入兩難的困境。
張孛老的意外死亡,在竇娥的情緒反應(yīng)中,起初根本就沒(méi)有對(duì)可能的牢獄之災(zāi)、刑逼之苦的恐懼,相反,在她看來(lái),這是使自己道德上擺脫兩難困境的一次機(jī)遇。也正是由于如此,竇娥不僅以冷漠的旁觀者姿態(tài)來(lái)看待張孛老的死亡,而且對(duì)潑皮張?bào)H兒叫囂著要“官休”的恐嚇也不以為然。甚至,綜觀《竇娥冤》全劇那昏暗、凄苦,且充斥著鬼魂和死亡氣息的敘事,我們發(fā)現(xiàn),只有在張孛老的意外死亡之后,始終被愁霧籠罩的竇娥才在言語(yǔ)中流露出些許的輕松。因?yàn)?在竇娥看來(lái),張孛老的死亡既使自己得以完成向“貞女”兼“孝婦”的身份的復(fù)歸,又使自己同蔡婆在道德層面上的潛在沖突得以化解。有論者已經(jīng)指出,“《竇娥冤》的基本矛盾,既不在于竇娥與官府之間,也不在于竇娥與張?bào)H兒之間,而在于竇娥與蔡婆婆之間一個(gè)要嫁一個(gè)要守的基本沖突。”[8]其次,在相信有“清官”存在的前提下,竇娥企圖通過(guò)訴諸公堂,通過(guò)辨明并懲辦真兇,徹底消除張?bào)H兒帶給自己的威脅。對(duì)竇娥來(lái)說(shuō),張?bào)H兒對(duì)自己的最大危害,不是來(lái)自人身安全方面,而是他可能終結(jié)自己做一名“貞女”、“孝婦”的道德理想,從而根本上摧毀自己賴以生存的精神根基。
三、死亡——反抗絕望的唯一選擇
如前所述,在后來(lái)的劇情發(fā)展中,竇娥卻意外地遭遇了一場(chǎng)在封建時(shí)代可謂司空見(jiàn)慣的司法悲劇,結(jié)果是她試圖通過(guò)“清官”來(lái)擺脫生存困境的夢(mèng)想徹底破滅,而她本人也淪為這場(chǎng)悲劇的犧牲品。事實(shí)上,通過(guò)解析竇娥自張?bào)H兒父子強(qiáng)行闖入到與張?bào)H兒一起應(yīng)訊于公堂的心路歷程,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gè)結(jié)論:與其說(shuō)竇娥出于孝道而甘愿屈招受死,不如說(shuō)竇娥是以孝道的名義走向了死亡。因?yàn)?假如被屈打成招并最終走向刑場(chǎng)的是蔡婆而非竇娥,但對(duì)活著的竇娥的而言,她在人世的痛苦只能是更加的深重。因?yàn)?一方面她曾經(jīng)所獲得的孝婦的美名將被輿論收回(封建的孝道規(guī)定了她在這場(chǎng)司法悲劇中只能替婆婆受死),另一方面,惡棍張?bào)H兒將在事實(shí)上成為她無(wú)法逃避的夢(mèng)魘。既然竇娥將“貞潔”和“孝道”當(dāng)成了生命的最高準(zhǔn)則,并試圖通過(guò)對(duì)“貞潔”和“孝道”的踐行,來(lái)獲得精神上的自我安慰,實(shí)現(xiàn)對(duì)苦難本身的有限遮蔽,那么,當(dāng)在公堂上的竇娥意識(shí)到作為活著的代價(jià),她必須放棄對(duì)“貞女”、“孝婦”這類美名的追求的時(shí)候(對(duì)竇娥這個(gè)生活在封建社會(huì)底層的弱女子來(lái)說(shuō),“貞女”、“孝婦”這一類封建婦女道德體系中的最高榮譽(yù)稱號(hào)的獲得,足可以成為對(duì)她一生苦難的補(bǔ)償,也是她文化意識(shí)中所渴望得到的表彰),塵世也就成了虛無(wú)的存在,活著也就成了禁錮靈魂的牢籠。
當(dāng)決意要做一名“貞女”、“孝婦”的自我追求破滅以后,竇娥才由一架封建的婦女道德的宣教機(jī)器,回歸到了一個(gè)真正的人的地位——一個(gè)真實(shí)、年輕的女性生命,也正是在這個(gè)時(shí)候,即當(dāng)用她人之為人所應(yīng)具有的體驗(yàn)和欲求來(lái)審視自己的人生時(shí),她才第一次發(fā)現(xiàn)了自己曾經(jīng)所經(jīng)歷和正在經(jīng)歷的痛苦、災(zāi)難和屈辱,既是如此的深重,又是如此的荒誕!然而,即使她已經(jīng)清醒了,但作為一個(gè)孤弱無(wú)依的女子,她又如何能掙脫得了自己的這非人的處境?!假如用現(xiàn)代的視角來(lái)解讀竇娥,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她跟魯迅先生所講的那類“清醒后卻發(fā)現(xiàn)無(wú)路可走的人”多少有些相似。
此外,從人性的層面上講,竇娥不會(huì)也不應(yīng)該只是某種理念教條的化身。她有人之為人所可能有的各種欲望,但更有欲望被封建的倫理教條長(zhǎng)期壓抑的痛苦。作為一個(gè)年輕健康的女人,她有正常的情欲(生理上的),有與心愛(ài)人重新組建家庭的欲望(心理上的),有被人尊重和承認(rèn)的欲望(精神的),但這些欲望都只能外化為與社會(huì)輿論和封建倫理不可避免的沖突,于是,內(nèi)心痛苦無(wú)法消除,心靈無(wú)法安靜。在劇本的第一折,竇娥用血淚唱出了積壓在心底的沉痛。竇娥在首次亮相的結(jié)尾說(shuō)道:“竇娥也,你這命好苦也呵!”這是她對(duì)災(zāi)難連綿的悲劇生命的表層感受,也是她對(duì)所處生活狀態(tài)的一種情感反應(yīng)。而她所唱的第一支曲《仙呂?點(diǎn)絳唇》有云:“滿腹閑愁,數(shù)年禁受,天知否?天若是知我情曲,怕不待和天瘦。”閑愁并非春花秋月的離情別緒,而是生命的自然欲望受阻后的情緒表白。但對(duì)自我人生歷程的這些體驗(yàn),都是以獨(dú)白的方式傳達(dá)出來(lái)的,是不使秩序干預(yù)的潛意識(shí)中的“我”的一種自憐。而現(xiàn)實(shí)中的她是根本沒(méi)有權(quán)利言說(shuō)自己的不幸的,甚至,她對(duì)不幸的默認(rèn)和承受,被闡釋為一種獻(xiàn)身于封建的婦女道德的自我表白。可以想象,像竇娥這樣一個(gè)在現(xiàn)實(shí)中被道德的鬼魂絕對(duì)支配,只能在黑暗的潛意識(shí)世界里獲得片刻的人性舒展的人,對(duì)死亡,不可能只是一種純粹的恐懼。相比于她在現(xiàn)實(shí)中的非人境遇,死亡,只是另一個(gè)神秘世界的符號(hào),甚至,是自我解脫的誘惑。對(duì)她來(lái)說(shuō),至少有一點(diǎn)是可以肯定,那就是相比于在道德的名義下存在的塵世,死亡對(duì)她的剝奪是那樣的微不足道!死亡,只有死亡,才能消解那記憶中太過(guò)深重的痛苦,才能使痛苦中瀕于絕望的靈魂安息。
在文本敘述的表層,竇娥似乎為“理”而死(保全婆婆的性命)。事實(shí)上,通過(guò)解析并還原竇娥的心靈歷程,我們可以作出這樣的一種判斷:當(dāng)竇娥意識(shí)到殘酷的生存困境已經(jīng)在道德和現(xiàn)實(shí)層面剝奪了自己生存的希望之后,死亡,就成了消解痛苦、反抗絕望的唯一選擇。竇娥的死亡,也反映出個(gè)體在非人的生存秩序下實(shí)現(xiàn)自我拯救渺茫。
[參考文獻(xiàn)]
[1] 顧學(xué)頡.元人雜劇選[C].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98.
[2] 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xué)批判〉導(dǎo)言[A].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 錢華.“本一點(diǎn)孝道的心懷,倒做了惹禍的胚胎”———竇娥冤屈的深層文化意蘊(yùn)[J].海南師范學(xué)院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03.(5).
[4] 黃克.關(guān)漢卿戲劇人物論[M].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84.72.
[5] 蘇力.竇娥的悲劇——傳統(tǒng)司法中的證據(jù)問(wèn)題[J].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2005.(2).
[6] 易延友.冤獄是怎樣煉成的——從〈竇娥冤〉中的舉證責(zé)任談起[J].政法論壇(中國(guó)政法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06.(4):128.
[7] 王志武.關(guān)于〈竇娥冤〉研究中的幾個(gè)問(wèn)題[J].人文雜志,2002.(4):92.
[8] 張維娟.從〈竇娥冤〉看關(guān)漢卿的男權(quán)本質(zhì)[J].戲曲藝術(shù),2003.(2).
[作者簡(jiǎn)介]
楊明貴(1980-)男,陜西長(zhǎng)武人,安康學(xué)院中文系講師,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國(guó)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