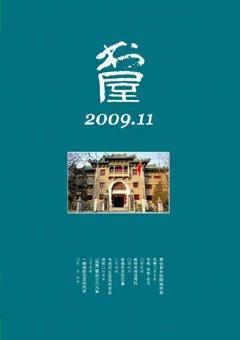張岱與陳繼儒
張則桐
一
陳繼儒(1558—1639),字仲醇,號眉公,松江華亭(今屬上海)人。《明史·隱逸傳》其傳云:
幼穎異,能文章,同郡徐階特重之。長為諸生,與董其昌齊名。太倉王錫爵招與子衡讀書支硎山。王世貞亦雅重繼儒,三吳名下士爭欲得為師友。繼儒通明高邁,年甫二十九,取儒衣冠焚棄之。隱居昆山之陽,枸廟祀二陸,草堂數椽,焚香晏坐,意豁如也。時錫山顧憲成講學東林,招之,謝弗往。親亡,葬神山麓,遂筑室東佘山,杜門著述,有終焉之志。工詩善文,短翰小詞,皆極風致,兼能繪事。又博聞強識,經史諸子、術伎稗官與二氏家言,靡不較核。或刺取瑣言僻事,詮次成書,遠近競相購寫。征請詩文者無虛日。性喜獎掖士類,屨常滿戶外,片言酬應,莫不當意志。瑕則與黃冠老袖窮峰泖之勝,吟嘯罕入城市。其昌為筑來仲樓招之至。
陳繼儒是晚明山人群體的領袖,聲名遠播。他與江浙士林聯系緊密,他的生活方式、文藝著述對晚明的士人都有導向意義。
張岱祖父張汝霖與陳繼儒交情深篤,萬歷三十三年(1605)張汝霖贈給陳繼儒大角鹿,眉公攜至西湖,竹冠羽衣,往來于長堤深柳之下,見者稱羨不已,眉公因此又號“麋公”。這樣的饋贈顯得十分風雅。陳繼儒說:“肅之與余稱三十季老友,而素心遙對,杖屨詩酒,呼吸相通”(《古今義烈傳序》)。萬歷三十年張汝霖帶六歲的張岱到杭州拜見陳繼儒,這次經歷給張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終生難忘,《自為墓志銘》特地指出:
六歲時,大父雨若翁攜余之武林,遇眉公先生跨一角鹿,為錢塘游客,對大父曰:“聞文孫善屬對,吾面試之。”指屏上李白跨鯨圖曰:“太白騎鯨,采石江邊撈夜月。”余應曰:“眉公跨鹿,錢塘縣里打秋風。”眉公大笑起躍曰:“那得靈雋若此,吾小友也。”欲進余以千秋之業,豈料余之一事無成也哉?
張岱的對句與眉公的出句對偶工整,還帶著幾分揶揄嘲諷,眉公不以為忤,稱贊張岱敏捷的才思,在這樣的細節中顯示了灑脫的胸襟和氣度。童年的記憶是深刻而堅韌的,就像埋入地下的一粒種子,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而發芽、開花、結果。眉公是當時的大名士,交際酬酢繁忙,他的記憶里并沒有留下這件事的痕跡。到崇禎元年,他對張岱已毫無印象,這一年張岱寫成《古今義烈傳》一書,托友人請陳繼儒作序,童年時代的美好記憶使他對眉公一直充滿敬仰之情。雖然他與陳繼儒直接接觸很少,但在晚明的時代氛圍中,陳眉公對于張岱來說并不遙遠。在張岱的心目中,陳眉公是一位值得效法的前輩。張岱對陳繼儒的風度和文章了然于心,他自己的詩文隨處可見受到陳繼儒影響的痕跡。陳眉公的形象已進入張岱意識的深層,參與了張岱思想的建構和人生的設計。
二
張岱的家族具有深厚的文化傳統和輝煌的科舉業績,家資豪富,在紹興和杭州擁有多處園林池沼,明亡前的張岱過著繁華精致的名士生活。陳繼儒對張岱人生方向的影響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
一是放棄科舉,專心著述。陳繼儒二十九歲焚棄儒衣冠,轉而經營自己的山人事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張岱是張元忭的曾長孫,在前輩業績的感召下,張岱從少年時代就熱衷科舉,但在屢次鄉試不售之后,他對科舉產生了懷疑。崇禎元年(1628)開始寫作《石匱書》,以這一年為標志,張岱基本上淡出科場,這一年張岱三十二歲,較之當年陳繼儒二十九歲放棄科舉,晚了三年。張岱之所以放棄科舉而專心著述是基于這樣的考慮:放棄科舉并不等于不再追逐名利,而是采取另外的方式來達到目的。張岱一生都不能忘情對名聲、功業的追求,他的最后一部著作《有明于越三不朽圖贊》,旨在表彰明代越人在立德、立功、立言方面的杰出代表,自己的向往欽慕是顯而易見的。晚明時期的江南地區商業發達,士人揚名的途徑也由過去只限于科場得意而趨于多元,從事著述、經營文化產業也都可以名利雙收,在這方面陳繼儒無疑是最成功的典范。張岱的人生抉擇正是在科舉對士人的壓力相對削弱的氛圍中,效法陳繼儒的結果。這一選擇使張岱把精力投入明史的編撰和其他著作的寫作,充分發揮了他的優長和才華,為后人留下了豐厚的文化遺產。
二是營造雅致閑逸的日常生活。相對于屠隆、王稚登等人,陳繼儒并不縱情聲色,他更注重生活的情調和品位。陳繼儒一生愛茶,在茶藝上造詣精深。他曾為夏樹芳《茶董》作序,并對該書進行補錄,于萬歷四十年(1612)前后撰成《茶董補》兩卷,上卷補錄嗜尚、產植、制造、焙瀹等條文,下卷補錄前人詩文三十七篇。他的《試茶》詩云:“綠陰攢蓋,靈草試奇。竹廬幽討,松火怒飛。水交以淡,茗戰而肥。綠香滿路,永日忘歸。”飲茶環境的清雅、茶人的相得之樂歷歷如在目前,令人神往。另一首《試茶》詩云:“此意偏于廉士得,之情那許俗人專。”只有狷潔之士才能品出茶的韻味。他還注重構造園亭、怡情書畫。陳繼儒善于把日常生活的細節打磨出藝術品位,代表晚明文人藝術化生活的典范。張岱的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與陳繼儒一脈相承。張岱精通茗飲,在茶葉的焙制、泉水質地的分辨和沖瀹的工藝諸方面都是行家里手,他與晚明制茶名家閔汶水以茶訂交的精彩過程因《閔老子茶》一文而膾炙人口。張岱也精通園林、書畫等藝術,可以和這些領域第一流高手對話。面對五彩斑斕的世界,張岱既深入其中,又能以獨具的慧眼去觀察、體味,用他的錦心繡口去表達。《陶庵夢憶》就是他在晚明生活的實錄。
三是著述的形式。陳繼儒重視史書,主張子弟讀書應先讀史,他在《全史詳要序》里說:“何以通天通地通人,曰史是也;何以立德立功立言,吾亦曰史是也。”他把史書看成是“天地間一大賬簿”,并認為:“夫未出仕,是算賬簿的人;既出仕,是管賬簿的人;史官是寫賬簿的人。寫得明白,算得明白,管得明白,而天下國家事,了如指掌矣”(《古今大賬簿》,見《白石樵真稿》卷十)。上述觀念對張岱潛心從事《石匱書》的編撰會起到激勵的作用。陳繼儒的著述帶有某些商業性質,錢謙益記述說:“仲醇又能延招吳越間窮儒老宿,隱約饑寒者,使之尋章摘句,部分族居,刺取其瑣言僻事,薈撮成書,流傳遠邇。款啟寡聞者,爭購為枕中之秘”(《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這類著作數量頗多,如《妮古錄》、《群碎錄》、《讀書鏡》、《珍珠船》等。應該說,這類著作的大量出現代表了一種新的文化方向。張岱著書并不包含商業的動機,他對陳繼儒的這種著書方式是十分欣賞并努力仿效的。他的第一部著作《古今義烈傳》就是從大量的史書擷取忠臣義士詮次而成,其他如《史闕》、《四書遇》、《快園道古》、《夜航船》、《琯朗乞巧錄》也都采取這樣的編撰形式。在這些著作里,大部分材料取自史書,文字通過作者的重新組織,每個小條目文字簡潔雋永,具有較強的可讀性。
三
陳繼儒的人生歷程給張岱的人生設計提供了成功的范例,他的文藝思想和詩文創作對張岱的影響也非常深刻,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張岱散文的文化和藝術品位。陳繼儒與董其昌是晚明畫壇松江畫派的領袖,張岱的文藝思想深受南北宗論和松江畫派藝術風格的影響。張岱與松江畫派之所以有如此深厚的淵源,陳繼儒是一個關鍵性的中介。董其昌評陳繼儒的畫作說:“眉公胸中素具一丘壑,雖草草潑墨,而一種蒼老之氣,豈落吳下之畫師甜俗魔境耶?”(《董其昌畫論輯要》)陳繼儒的山水畫既有蕭散簡淡的風韻,又有老蒼生辣的氣勢,在創作上,他把元末文人畫風與宋代院畫融為一體,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面目。陳繼儒認為書畫藝術的最高境界是“蘊藉中沉著痛快”(《妮古錄》)。張岱則強調“天下堅實者空靈之祖”,書畫藝術要“以堅實為空靈”,而不能“率意頑空”(《跋可上人大米畫》)。二人表述有所不同,而對藝術精神的理解是一致的。陳繼儒的藝術實踐對張岱形成“以堅實為空靈”的文藝思想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在文學上,陳繼儒認為:“作傳與墓志、行狀,正如寫照,雖一瘢一痣,皆為摹寫。不然,不類其人”(《太平清話》)。張岱在傳記寫作上力求達到“酷肖其人”的境界,與陳繼儒的主張一脈相承。關于詩文,陳繼儒有這樣的議論:
陳眉公嘗與山中友人談曰:“吾輩詩文無別法,但最忌思路太熟耳。昔王元美論藝,止拈《易》所云‘日新之謂盛德。余進而笑曰:‘孫興公不云乎,今日之跡復陳矣。故川上之嘆不曰來者,而曰逝者,人能覺逝者為窠臼,為糟粕,而肯戀戀于已赫之腐鼠、不靈之芻狗為哉!天馬拋棧,神鷹掣鞴,英雄輕故鄉,圣人無死地,彼于向來熟處,步步求離,刻刻不住,此謂真解脫,此謂真喜舍,此謂日知其所無。右軍萬字各異,杜少陵千首詩無一雷同,是兩公者,非特他人路不由,即自己思路亦一往不再往。”(《玉劍尊聞》卷之三)
這段論述可與張岱提出的“練熟還生”的命題相互證發。對于傳統的儒家經典,陳繼儒喜以文學的眼光來欣賞、接受,他能在古奧的《尚書》中讀出似“洞光珠”、“清水珠”、“瑯玕珠”等絕妙文章。他對《史記》的文學成就更是推崇備至:“余嘗論《史記》之文,類大禹治水,山海之鬼怪畢出,黃帝張樂洞庭之野,魚龍怒飛,此當直以文章論。而儒者以理學捃束之,史家以體裁義例掎摭之。太史公不受也”(《史記定本序》,見《白石樵真稿》卷一)。陳繼儒的觀點代表在正統儒家和嚴肅的學者之外解讀古代經典的立場,富有生活情趣,表現了晚明江南社會新興文人群體的審美趣味和價值取向。張岱深受此風影響,《四書遇》中也隨處可見對“四書”的文學解讀。
張岱散文的精神血脈與陳繼儒的散文有千絲萬縷的聯系,陳繼儒擅長在瑣細擾攘的日常生活中品出哲理和風雅,并以清言的形式抒寫其會心之悟,他的一些清言往往成為張岱文章中的點睛之筆。如《自為墓志銘》說自己的七不可解,其中“以書生而踐戎馬之場,以將軍而翻文章之府,如此則文武錯矣,不可解三”,源于陳繼儒的清言:“名妓翻經,老僧釀酒,將軍翔文章之府,書生踐戎馬之場,雖乏本色,故自有致”(《太平清話》)。由此不難看出,張岱標舉的“七不可解”是在表達一種生活情趣。陳繼儒還說:“人有一字不識而多詩意,一偈不參而多禪意,一勺不濡而多酒意,一石不曉而多畫意;淡宕故也”(《巖棲幽事》)。這只是一種理想的人生境界,而張岱筆下的民間醫生魯云谷的個性、醫術和愛好接近于斯,故張岱評論他說:“云谷居心高曠,凡炎涼勢利,舉不足以入其胸次。故生平不曉文墨,而有詩意;不解丹青,而有畫意;不出市廛,而有山林意”(《魯云谷傳》)。對于人的評價,陳繼儒通過徐庶、周處的經歷指出:“夫千里之駒,性必銜蹶;千人之英,性不跅弛”(《徐庶周處論贊》)。陳繼儒欣賞那些個性鮮明、才能卓特的異人,曾撰《十異人傳》,盲人唐士雅即是其中之一。張岱《五異人傳》是陳繼儒《十異人傳》精神的延續,張岱提出:“人無癖不可與交,以其無深情也;人無疵不可與交,以其無真氣也。”把這句話放在陳繼儒的清言小品中并不突兀,它是對陳繼儒人物品評的發揮和深化。清言小品描繪理想的人生境界、抒發人生感悟,并不具實踐性品格,而張岱則努力把陳繼儒清言中藝術化的感悟加以實踐,或者在現實生活中以具體的人物來印證詮釋陳繼儒的清言小品,這是張岱散文創作的內存動因,張岱散文的文化意義也因而突顯出來。
張岱在散文的藝術形式上也深受陳繼儒的影響。陳繼儒思想通脫,他的散文如序跋、傳記、園亭記等突破唐宋古文的規范,自由抒寫,充滿生活情趣,如《閩游草序》、《茶董小序》、《綠野池記》、《范牧之外傳》等。張岱的散文顯然是沿著陳繼儒的創作方向進一步發展,有些文章可以看到陳繼儒的印痕,如《茶史序》,作為一篇序文,全文詳細記敘了張岱與閔汶水考校茶藝而訂交的過程,其創作構思顯然受到《閩游草序》的啟發。陳繼儒的清言小品把語錄、駢偶及文采融為一體,創造出一種辭藻華美、音節和諧又明白如話的語言。從語體來看,張岱散文的語言是在語錄體的基礎上融匯創造的結果,在這個過程中,陳繼儒清言小品的語言成就給予張岱重大的影響,張岱散文語言所呈現出的清新流暢、明白透徹等特色都與陳繼儒的清言小品有著密切的關系。晚明是中國古代散文語言發生重大變革時期,古文、駢文、八股文、語錄及口語在小品這個文體里整合、創造,到了張岱的手里,他的語言離白話散文只有一步之遙。眾多的晚明作家參與了散文語言的創新,張岱是集大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