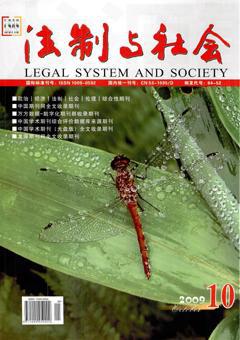入戶搶劫案件的定罪問題
趙增田
摘要最近,某地法院判決了一起搶劫的案件,該案在審理過程中,控辯雙方圍繞被告人趙某是否構成入戶搶劫等問題產生了激烈的辯論。本文認為本案對于認識搶劫罪具有一定的典型意義,有必要對其中的幾個法律問題作進一步思考。
關鍵詞法院判決 審理 控辯雙方
中圖分類號:D924.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9-0592(2009)10-111-02
一、基本案情
2004年12月20日,被告人趙某幫A村村民劉某家賣棉花,見其得款6000余元,便心生搶劫惡念。當日晚20時許,趙某為實施搶劫竄至劉某家中,先以借錢為名讓劉某之妻楊某給他拿錢,伺機窺探劉某家存錢位置。趙某向楊某提出為其岳母看病借用100元錢,楊某讓趙某打了張欠條,隨即從里屋拿出了100元錢。趙某因未看到存錢地點,便又稱再借100元,楊某轉身去里屋拿錢之際,趙某趁機拔下堂屋的電話線,并緊跟著進了里屋,趙某進去時楊某已經手里拿著100元錢了,此時趙某顯露出搶劫本意,用手掐住楊某的脖子,說“錢呢?”,楊某說在手里,趙某說“還有呢,那些錢呢?”,意思是想讓楊某把賣棉花的錢都拿出來,楊某說:“都存起來了”,趙某不相信,隨即將楊某掐昏,并與進到里屋的劉某扭打在一起。趙某用劉某家的剪刀先后將劉某夫婦及其女兒扎傷,并用木棍對劉某進行毆打脅迫劉某用電話線將母女二人捆綁起來。見其一家三口被治服,趙某便索要其家中的賣棉花款6000余元,劉某和妻子謊稱已將錢款全部存入銀行,并指出之前的存錢位置讓趙某自己去查找,趙某未找到錢款。雙方僵持至23時左右,后趙某將欠條撕掉,稱不再要錢,要求被害人也不要報警。此時已有九個月身孕的楊某謊稱肚子疼,劉某稱妻子將要生產,必須去醫院。在此情形下,趙某放棄了搶劫的念頭,同意送楊某上醫院,并將之前楊某拿出來的一直放在桌子上的200元錢放入劉某的上衣口袋中以備就醫之用。因電話線已被剪斷,趙某和劉某一起去劉某的父母家打“120”急救電話,當走至劉某家院外時,趙某為防備楊某家人報警后自己無逃跑路費就又從劉某衣服中將原先其放入劉某上衣口袋的200元錢拿走。兩人去劉某父母家打了急救電話之后,趙某發覺其家人已報警隨即逃走。后經法醫鑒定,劉某及其家人三人所受之傷均為輕微傷。
鑒于以上事實證據,檢察機關認為,被害人楊某一直處于被告人趙某的暴力脅迫之下,其將200元取走這一行為應歸屬前面在被害人家中的搶劫行為,趙某構成搶劫既遂。趙某進入被害人家中實施搶劫,且其搶劫犯意產生于入戶之前,因此為入戶搶劫,屬于搶劫罪中的情節加重犯。應當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鑒于其認罪態度較好,有悔罪表現,建議對其判處有期徒刑十年。在法庭上,趙某辯解,其到劉某家中是為了借錢,并不是搶劫。趙某的辯護人則為趙某做無罪辯護,被告人主觀上不具備搶劫的故意,指控的罪名不成立。
2007年4月2日,法院經開庭審理對本案作出一審判決,判決認定趙某構成搶劫罪,判處有期徒刑五年,并處罰金5000元。
二、問題與思考
筆者贊同法院對本案的判決結果,但是本案判決并未將案件的判決理由在判決書中詳細的加以表述。鑒于司法實踐中搶劫案件情況的復雜性,針對現實中搶劫罪在許多問題上如何定性存在較大爭議,現結合本案就搶劫罪中的一些爭議問題談點個人淺見。
(一)正確認識搶劫罪的主觀方面
根據目前刑法理論界的通說,直接故意犯罪的主觀方面包含著犯罪目的的內容。犯罪目的不僅反映出行為人主觀惡性的程度,同時還支配行為人實施行為的方向,決定行為的性質。犯罪目的雖然不是一切犯罪構成的必備條件,但是,它是某些犯罪構成的必備條件。此外,并非對于所有需要具備某種特定犯罪目的的犯罪,我國在刑法條文中都對這種特定的目的加以明確的規定,但從刑法理論和司法實踐中看,這并不妨礙必須具備某種特定犯罪目的才能構成該犯罪,此即為通常所說的不成文的構成要件。如,刑法第264條的盜竊罪、第266條的詐騙罪,還有263條的搶劫罪等等。①作為犯罪構成要件的犯罪目的,一般是與行為人實施犯罪行為所追求的結果內容相重合的犯罪目的,也有些犯罪,法律上規定的作為犯罪的構成要件的犯罪目的與直接故意的內容并不完全重合,亦即僅是直接故意內容的一部分。②
現行刑法第263條并未明確規定搶劫罪必須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產的目的,因此,理論上對搶劫罪是否必須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還存在一定的爭議。那么,搶劫罪是否要求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呢?筆者認為,判斷某種目的是否能夠確定為犯罪構成的主觀要件內容不能籠統地作出回答,而應該取決于它是否說明行為對客體的侵犯及其程度。若某種目的對決定客體的侵犯及其程度具有重要作用,即使在刑法沒有明文規定的前提下也可將其解釋為主觀要件的內容;若某種目的對決定客體的侵犯及其程度不起任何作用的話,則不能將其解釋為主觀要件的內容。而搶劫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即屬于前種情況,它是區分搶劫罪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的一個重要要件。搶劫罪必須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財物的目的,并且這一目的必須貫穿于搶劫罪的全過程。如果主觀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就不能構成搶劫罪。
本案中趙某在劉某家中對于僅以借口的名義取得的200元錢在主觀上并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這一點與先盜竊后被物主發現進而實施暴力轉化為搶劫在主觀上有很大不同,后者一開始對于財物就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只不過通過盜竊的方式來達到對財物的占有而已。而前者只是以借錢為借口來試探劉某家存款的位置,初始主觀上并無將這200元錢占為己有的意圖,這種不具有非法占有的心態從后來趙某撕毀欠條聲稱不再要錢并將200元錢塞進劉某的口袋中的也可進一步明顯的表露出來,因此對于趙某以借款名義取得的這200元錢所實施的行為不能認定為搶劫,雖然趙某此時對于這200元錢具有事實上的支配能力。
(二)如何認識搶劫罪中“暴力”的持續性
“暴力”一詞在不同的場合有不同的含義,搶劫罪中的暴力只能是最狹義的暴力。這種暴力必須針對人實施(不包括對物的暴力),并要求足以抑制對方的反抗,更不要求具有危害人身安全的性質。③對于搶劫罪中“暴力”的這一含義,學界上爭議不大,但是對于入戶搶劫中在戶內實施的暴力是否具有持續性的問題卻鮮有論著提及抑或蜻蜓點水,像本案中被告人趙某在戶內實施暴力后,跟隨被害人劉某至戶外后從被害人的口袋中將200元錢搶走是否能夠認為是入戶搶劫?筆者認為要使在戶內實施暴力后在戶外劫去財物的行為構成入戶搶劫需要滿足下三個條件:一是,以搶劫的目的入戶后并對戶內的人實施了暴力;二是,為實施搶劫將戶內的人暴力脅迫至戶外;三是,加害人對因其暴力脅迫離開戶的被害人實施了搶劫。這三個條件缺一不可,缺少任何一個均不能視為入戶搶劫。
根據以上分析,結合本案,被害人劉某離開住戶并非是由于被告人趙某實施暴力脅迫的直接結果,其能夠離開住戶是利用其妻楊某欺騙了被告人趙某,目的是為了利用出戶的機會報警,進而擺脫趙某的加害。從被告人趙某的人角度來看,其也并非是為了搶劫的目的將被害人劉某用暴力脅迫至戶外,其意圖是陪劉某去劉某父親家打電話,同時防備劉某報警。筆者認為判斷此處戶外搶劫200元錢的行為能否歸入在戶內的搶劫行為的關鍵是看被告人是否是基于搶劫的目的將被害人劉某暴力脅迫至戶外,很顯然被告人趙某與此條件并不相符,因此不能將趙某在戶外搶劫行為歸入先前的入戶搶劫。此外,被告人趙某在戶內時已經放棄了搶劫的念頭,在戶外是為了防備楊某家人報警后自己無逃跑路費才又從劉某衣服中將原先其放入劉某上衣口袋的200元錢拿走。對這里的200元錢的搶劫完全是出于臨時起意,應從新認定這里的搶劫行為,而不應將這里搶劫行為看成是戶內搶劫行為的持續。
(三)“入戶搶劫”既遂與未遂的問題
“入戶搶劫”是搶劫罪的加重情節,對于情節加重犯是否存在既遂和未遂,理論界和實務界看法不一。根據2005年6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印發的《關于審理搶劫、搶奪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的通知第十條規定:“搶劫罪侵犯的是復雜客體,既侵犯財產權利又侵犯人身權利,具備劫取財物或者造成他人輕傷以上后果兩者之一的,均屬搶劫既遂;既未劫取財物,又未造成他人人身傷害后果的,屬搶劫未遂。據此,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條規定的八種處罰情節中除“搶劫致人重傷、死亡的”這一結果加重情節之外,其余七種處罰情節同樣存在既遂、未遂問題,其中屬搶劫未遂的,應當根據刑法關于加重情節的法定刑規定,結合未遂犯的處理原則量刑。”可見司法實踐部門認為情節加重犯存在未遂狀態,與理論界存在不同。
根據刑法理論,犯罪停止形態只存在于直接故意犯罪中,落腳點是犯罪;而加重犯并不是一種獨立的犯罪,加重犯既遂與未遂的問題,實質上仍是基本犯罪既遂與未遂的問題。從這一意義上講,既然搶劫罪加重犯僅僅是由于出現了數額巨大或傷亡結果而加重處罰的一種形態,其從屬于搶劫罪,那么,搶劫罪加重犯的既遂與未遂就是搶劫罪的既遂與未遂,結論不言而喻。其次,承認入戶搶劫有未完成形態,能夠更好地實現罪刑相適應。對于加重構成的規定,是由于加重構成犯的社會危害性高于基本犯的社會危害性,而加重其刑,體現了公正與功利的統一,因其具有獨立的罪刑單位,在此基礎上不宜只作構成與否之分,而應當有基本犯一樣具有不同的犯罪形態,否則會出現量刑上的極大差異。再次,承認入戶搶劫具有未完成形態是刑事司法實踐的需要。最高人民法院在2005年6月的《解釋》中肯定了情節加重犯具有的未遂形態。據此,刑法第263條規定的八種處罰情節中除“搶劫致人重傷、死亡的”這一結果加重情節之外,其余七種處罰情節同樣存在既遂、未遂問題,其中屬搶劫未遂的,應當根據刑法關于加重情節的法定刑之規定,結合未遂犯的處理原則量刑。從中可以看出,這些司法解釋正是響應了實踐中出現許多新問題的解決措施,也是同我國刑法一般理論相一致的。最后,刑法理論將形形色色的犯罪情節分為兩類:定罪情節和量刑情節。搶劫罪的加重犯由于具有了某種嚴重情節,刑法對其規定處以更重的刑罰,其不是具備了新的犯罪構成要件的另一種犯罪,而是搶劫罪的加重處罰情節,在本質上仍是搶劫罪,因此這些加重情節都屬于搶劫罪的量刑情節。
本案中被告人趙某在戶內并沒有劫的財物,也并非沒有對對被害人造成輕傷以上的后果,根據《意見》第十條規定:搶劫罪侵犯的是復雜客體,既侵犯財產權利又侵犯人身權利,具備劫取財物或者造成他人輕傷以上后果兩者之一的,均屬搶劫既遂;既未劫取財物,又未造成他人人身傷害后果的,屬搶劫未遂。因此被告人趙某在被害人劉某家中所實施的的行為并不符合搶劫罪的犯罪既遂標準,當然也就不能以搶劫罪的情節加重犯來對待,只能按照普通的一般搶劫未遂來處理。
(四)如何看待本案搶劫罪的罪數問題
搶劫罪罪數形態的認定,主要是解決對某一搶劫案件是構成搶劫一罪,還是構成數罪的判斷問題。如果行為人只是實施了一個搶劫行為,或者實施搶劫行為后,又另起他意實施了其他犯罪,此時認定行為構成搶劫一罪或數罪并不困難。但是本案中被告人在戶內實施搶劫未遂后又在戶外針對同一人實施搶劫是應按一罪還是數罪進行處理?筆者認為此處應作為吸收犯按一罪處理。
吸收犯的成立以數個犯罪行為為前提。如果不存在數個犯罪行為,就沒吸收犯可言。④目前在理論上,對同一罪質而不同形態的犯罪行為之間,存在吸收關系是共識,由此“同一種犯罪的不同形式犯罪之間可以成立吸收犯”的觀點從這一點上說是能夠成立的;而第二種認識認為吸收犯的數行為必須觸犯不同罪名的觀點,如從共識出發來看,也可以認為是將這種并列罪名的情況也視為不同罪名。據此,上述對罪質的認識,應當說雖然在表述上有區別但實際上是相同的。由此而言,對于吸收犯罪質是否需要明確限定于同一或者不相同的數個犯罪之間,由于認識并無不同,所以并沒有實際的意義。因此,將吸收犯之所犯數罪的罪質作廣義上的解釋是比較恰當的,即同一性質不同形態的數個犯罪行為,屬于同種犯罪,可以成立吸收犯;不同性質的犯罪行為,即異質犯罪之間也可以成立吸收犯。⑤
回到本案,被告人趙某在戶內實施搶劫未遂后,跟隨被害人去劉某父親家打電話的途中,被告人趙某為防備楊某家人報警后自己無逃跑路費就又從劉某衣服中將原先其放入劉某上衣口袋的200元錢搶走。被告人趙某在戶內與戶外的行為是數個獨立的犯罪行為,并且戶外的搶劫行為是基于戶內搶劫行為的緣故而實施的,此外被告人趙某戶外搶劫的行為與戶內搶劫的行為在主觀上并無牽連或連續的故意,完全是出于臨時起意,所以前后兩次行為符合吸收犯的特征,按吸收犯以搶劫罪一罪來處理比較恰當,并且按吸收犯來處理更能夠體現罪責刑相適應的原則以及刑罰經濟的目的。
注釋:
①此外,還有第170條的偽造貨幣罪、第267條的搶奪罪、第274條的敲詐勒索罪和第382條的貪污罪.
②馬克昌主編.犯罪通論.武漢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386頁.
③張明楷.刑法學(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710頁.
④陳興良.刑罰適用總論(上卷)(第二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635頁.
⑤林亞剛.論吸收犯的若干問題.政治與法律.2004(2).第7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