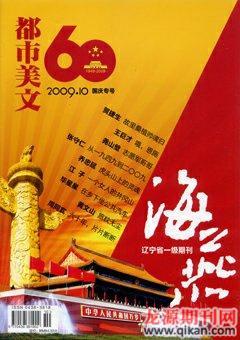廣昌蓮
任林舉 一九六二年出生。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先后在《作家》《長城》《青年文學》《詩刊》《星星》《文藝報》《文藝爭鳴》等刊物發表詩歌、散文、文學評論近百萬字,曾在《春風文藝》《新文化報》《城市晚報》等四家雜志、報紙上開設專欄,在魯迅文學院第五期高級評論家班進修。獲全國電力系統優秀著作獎、吉林文學獎、吉林省精品圖書獎等。著有散文集《輕云起處》《說服命運》,長篇散文《玉米大地》。散文《岳樺》入選二〇〇九年全國高考語文試卷閱讀理解題。
在我的感覺里,蓮是一種圣潔的花,它應該生在水里或天上,而不能生在田里或泥土里。
很久以前,我就在書本里看到過,有人說它,“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后來,又在阿彌陀佛經里看到,佛說它“微妙香潔”……種種佐證都已經明了蓮的神異與不同凡響。就這樣,不由得我在很少有蓮的北方,對蓮,常常懷有傾慕與向往。
第一次到廣昌去拍蓮,差不多被那里鋪天蓋地的蓮花驚呆了。只瞧那么一眼,收入視野里的蓮花,就抵得上半生全部所見,豈止一個奢侈所能形容,簡直就是奢靡。
一個搞攝影的人,總是要趕在太陽升起前到達某一個地方,這有一點像一種神秘的約會,有一點像某種儀式。如果想知道昨夜的黑暗里到底埋藏著什么,那么在光明到來之前,我們必須做出正確的選擇,確定一個正確的時間和正確的地點,否則,我們很有可能錯過那個答案。往往,我們所知道的,就是許給我們的那個新娘已經上轎,她的臉是美麗還是丑陋,正被厚厚的蓋頭遮于暗處,我們要和陽光合作,一同用手指挑開那層蒙昧。對于一些心里常常懷有某種美好期待的人來說,這永遠都是一件令人激動的事情,也許正是因為這一點,當初,我才無怨無悔地愛上攝影這一行。
那一天,就是在太陽升起之前,我們抵達了預定的拍攝現場。當如水的光線一層層洗去附著在萬事萬物之上的夜色時,我們看到了一幅碩大無朋的照片正在大地上顯影。
這就是廣昌的蓮了,舉目遙望,我無從判斷她們的隊列從哪里起始,又到哪里終止。她們的聲勢浩大、她們的艷麗妖嬈、她們的姿態紛呈,讓我實實在在地感到了自己的污濁、單薄與窘迫。作為一個來自于不同生存空間的異類,我找不到與蓮并立、廝守的理由。面對這樣的生命、這樣的陣容,我久久地不敢抬起頭來,不敢與那些怒放的花直直地對視。
我只能讓眼睛躲到照相機的鏡頭后面,借著可虛可實的鏡頭來掩藏自己的羞怯。這羞怯,來自于我的生命深處,來自于我窮鄉僻壤的童年。從很久以前直到今日,只要那些美好或美妙的事物映入我的眼簾,我都不由自主地想轉身逃開。我從來也做不到無所顧及,勇敢地張開雙臂去擁抱那些我認為圣潔的事物。這樣的自警或自虐,并不是因為我害怕與那些美好事物將合未合之際,會把自己的卑污映襯得更加卑污,而是怕因為自己的卑污褻瀆了那份圣潔。這世間美好的東西太稀缺了,不是我沒有勇氣,而是我總不能忍心,讓一己快慰與滿足無由地摧毀她們或改變了她們的性質。
隱于暗處的那只手,只是為我開啟了發現美的窗口,卻沒有給我插上抵達美的翅膀。從遙遠的少年時代開始,我就為那些美好的事物飽受磨難,所以我憂傷。當我面對眼前這些絢麗的蓮花,當我躲在鏡頭后面的時候,我知道我貪婪的目光就再不能傷及她們了。于是我盡情地操作,把她們的臉放大、縮小,拉至眼前或推向遙遠,定格或虛化,我一朵一朵地對她們進行著無言的叩問。我看到了,她們對著夏日的早晨,對著陽光,也對著我款款地微笑,而我卻一點都搞不懂她們微笑的含義。
不知道那微笑里所蘊藏的是眷顧、是寬容,還是嘲諷。當我在相機顯示屏上重放那些我以為千姿百態的蓮花照片時,我看到的卻差不多是同一張照片,因為每一朵蓮花都似曾相識,每一張照片都大同小異。原來我以為我曾經看見,我以為曾經發現,而實際上我什么也沒有抓住。在我的眼前,只有一望無際的荷田,卻不再有蓮,我不知道她們是什么時候,以怎樣的方式一次次從我的鏡頭下逃走的。
最初的驚喜,在我的眼里已經漸漸消失,她們那千篇一律的面容與微笑已經讓我分不出這一朵與那一朵到底有什么不同。如今,她們已經平凡而普遍得如同站在操場上翹首等待號令的中學生,或假日站臺上找不到方向擠成一團的民工。一樣的裝束,一樣的神情,一樣的目光,如同一層堅硬的外殼,讓我們無法進入她們的情感、個性、心靈和生命,無法了解她們的憂戚、快樂、夢想與身世。
當我看到那些面目模糊、衣著簡陋的蓮農隨意地穿梭于那些花朵與子實之間,并信手捋下成熟的蓮蓬或折斷礙事的蓮花時,我的心不由得一緊,雖有不甘,但卻在心里狠狠地輕賤起她們。盡管,廣昌的蓮種本是從高遠的太空而來,但面對她們沒有個性沒有選擇的容顏和笑臉,我還是把她們等同于那些沒日沒夜守候在田里,只有面容而沒有身份的農婦了。
或許,廣昌的蓮并不是為了開花,不是為了美麗而生,而是為了繁殖,為了結籽,為了讓更多的蓮蓬出生,為了經濟而生。
然而,就在我路過一處遍撒浮萍的水塘時,一朵嬌艷的紅蓮從浮萍的縫隙里映現出來,宛如夜色里的一個閃電,剎那間照亮我的心智。我的心,忽如明鏡,透過那零星的浮萍和寧靜而氤氳的水光,我看到了她五百年前的顏容與風姿,我看到了她五百年后從現實的某一個窗口向我透露的深長的意味,我也看到了她在歲月之河上蕩開一圈圈漣漪的足跡。它不僅僅是一朵蓮花在水中的倒影,而是我再度與蓮花重逢的另一個空間另一個維度。
當我懷著虔敬的心情拍下這個影像的時候,我確認,那一刻我已經捕捉到了世間最美麗的精靈,觸碰到了一種事物美麗的核心。
因為有了這樣一個超越現實的視角,我拍下的蓮花從此就不再雷同,有時就是拍同一株或同一束,所結出的影像仿佛也神情各異,姿態紛呈。
佛經里說,佛無定相卻有萬千法相。這時,我才有一點明白,那些站在荷田里的蓮,定不是天生俗物,更不會是某種刻意的隱身。那個本真的蓮,它從來就站在那里,只是我們不能夠發現,只是我們從來沒有從世俗的、現實的視角之外去參悟她們,所以才看不到她們真正的生命。而只有通過水,這與天同一形態、同一顏色的介質,我們才有可能走進蓮的秘密、蓮的真意。
《佛陀本生傳》記,釋迦佛生于二千多年前印度北邊,出生時向十方各行七步,步步生蓮花。這不能不讓人產生豐富的聯想,在廣昌這片幸運的土地上遍布著佛訪寒問苦的足跡,每一朵蓮花,不啻一個深深的祝福。是所謂佛無定形,佛無定相,佛無定法。
在一處蓮田的池埂上,我與一個樸實的蓮農“狹路相逢”,就在錯身的那一瞬,我問他,為什么蓮心是苦的,他愣愣地看了我一會兒說,那是因為它成熟了,嫩的時候蓮心也是甜的。于是,他給了我一只嫩蓮蓬。我細細咀嚼著那脆而甜的蓮籽,和被一層甜甜的汁液包裹著的蓮心,卻感覺有一絲難以覺察的淡苦,如一抹心思,悠然飄過心頭,那是蓮與生俱來的秉賦。
后來,我查了很多關于蓮的資料,才知道廣昌的蓮,不是產藕的藕蓮,也不是專為觀賞的花蓮,而是專門產籽的籽蓮。于是也知道了廣昌縣年種植太空蓮十三萬畝,年總產一千萬公斤,產值達四億多元的數據,意味著什么。這樣一個巨大的數字,會養活多少人,讓多少人過上好日子啊,廣昌的蓮讓我們知道什么叫普渡眾生。
廣昌蓮的蓮,確實不單單是為了美麗,不單單是為了開花而生,而且還為了結出更多的蓮蓬,拯救一方民眾而生。
關于廣昌蓮,我下了一個讓我自己滿意的結論,但同樣也是一個令很多人懷疑的結論。我知道,真正的美,往往是不承擔什么重量的,承擔了就會在某些領域或角度上存在著被摧毀或破碎的危險。就像我們自己的母親,在我們的眼里總是那么無懈可擊地美麗,哪怕她韻華已逝,哪怕她老態龍鐘,但在那些不相干人的眼里她肯定會被以另外的尺度、另外的態度嚴厲地考量,在那些人眼里,她定然不再美麗。
慶幸的是,在我離開廣昌時,一個意外的情景將我從一個尷尬的言說境界中解救出來。
在我們多次路過,卻從沒有留意過的荷田,我看見了一朵獨立的蓮花,那是我沒到廣昌就希望能夠看到,但卻一直沒有出現的蓮花。那是一朵開放得近于完美的白色蓮花,碩大而又純潔。就在那片無花也無蓬的蓮池邊緣,那朵蓮悠然地顯現出來,像昏暗的睡眠里突然降臨的夢境一樣,突兀而又新奇。一片芬芳的冰,從我的車窗邊掠過,清晰復朦朧,隨著車輪的遠去,漸漸化開,如若濃若淡的情誼,如若遠若近的召喚,如若隱若現的微笑……
廣昌的七月,因此而香郁無邊。
責任編輯︱孫俊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