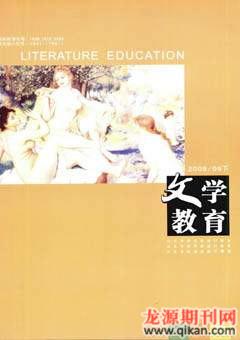《喧囂與騷動》中愛的倫理
郭海平 郭 肖
美國著名小說理論大師亨利·詹姆斯曾表明“每一個偉大的作家都有他的倫理核心”(詹姆斯 55)。那么福克納創作《喧嘩與騷動》的倫理核心是什么呢?福克納出生在一個傳統的基督徒家庭,他深受基督教義的影響。在基督教倫理中,“愛”的倫理思想在其中占據了非常重要的地位。福克納曾說基督教的傳說是每一個基督教徒,特別是像他那樣的南方鄉下小孩的背景的一部分,因此,對福克納而言,他的倫理核心就是基督教愛的倫理。基督教倫理對福克納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那么他筆下的人物是否也踐行了基督教倫理所倡導的“愛”這一倫理呢?因此,本文將關注的目光投向《喧嘩與騷動》中的康普生家人和仆人迪爾西,從“愛”的層面來審視福克納是如何運用基督教倫理這個工具來闡釋南方舊家族的解體,從而完成了他“對人和人類命運的根本看法”的(肖明翰 127)。
一.康普生家族:“愛”的缺失與生存的絕望
在一個家庭中,妻子和母親本應是愛的源泉,但康普生夫人卻是一個冷漠、虛偽、自私、自憐的女人,永不休止地哀嘆和抱怨,對丈夫和孩子毫無體貼、關心和愛。她公然說,除了杰生,其他孩子“都不是我的親骨肉……與我一點關系也沒有(118)”1。她對班吉不僅沒有一點溫情,反而為他感到羞恥,并認為他是“老天對我的一種懲罰(3)”。她總是覺得昆丁和凱蒂“老是鬼鬼祟祟地聯合起來反對我(288)”。而昆丁自殺則是為了“嘲弄我,傷我的心(328)”。她告訴丈夫,班吉“是對我所犯的罪孽夠沉重的懲罰了,他來討債是因為我自卑自賤地嫁給了一個自以為高我一等的男人(204)”。顯而易見,不論是作為妻子還是母親,她都是失職的。她的愛只指向自身而與孩子們絕緣。
在一個家庭中,如果母愛缺失了,父愛就顯得異常重要。作為一家之主的康普生先生能否用他的慈愛來溫暖他的孩子們呢?從小說中我們了解到康普生先生一方面性格軟弱,另一方面又是家中的至高權威;一方面才智甚高,另一方面又一事無成。生活和性格中的這種極大反差使他悲觀厭世,陷入虛無主義,最后在酗酒中走上自我毀滅的道路。康普生先生和康普生夫人一樣,不僅沒有給予孩子們關愛,盡到做父母的責任,沒有幫助孩子們建立其直面現實生活的勇氣和信念,沒有給孩子們在成長的過程中所需要的正確精神指導;同時也沒有做到“愛己”,即面對困難堅強不屈,給孩子們樹立一個好的榜樣。相反,前者自暴自棄,看破紅塵,后者則整日怨天尤人。
由于父母的失職所造成的家庭愛的缺失,康普生家的三個兒子都呈現出病態的特征。昆丁愛的是家族過去的榮譽,而不是他的姐弟。他視凱蒂的貞操如生命,因為他愛的是凱蒂的貞操代表的門第和榮譽,而不是凱蒂這個有血有肉的人。他沒有愛的能力,他“最愛的還是死亡,他只愛死亡,一面愛,一面在期待死亡”①(345)。昆丁最終選擇自殺結束了人生。班吉的智力水平停留在幼兒時期。由于先天條件限制,他不能愛自己,更不能給予別人愛。杰生自私冷酷缺乏信義,無法與任何人建立一種正常的人際關系。康普生夫婦及他們的三個兒子雖性格各異,但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他們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缺乏人性的交流,沒有對別人的關愛,哪怕是至親的家人。
凱蒂是康普生家族唯一具有愛心、關心他人的人,她對班吉特別的關愛體現了她的美好人性。她的悲劇在于她沒有愛己,沒有勇敢地追求自己的幸福,而是被動地接受命運。盡管凱蒂喜歡她的初戀情人達爾頓·艾密司,但她沒能解釋誤會因而失去了愛情。失去愛情之后,她自暴自棄,依靠變賣色相來撫養她的女兒小昆丁。最終淪為納粹將軍的情婦。
沒有愛的家庭環境最終不可避免地導致康普生家族的“生存的失望”,從而陷入空虛和虛偽的境地。昆丁跳河自殺了;杰生沒有了信義;凱蒂最后完全墮落了;班吉不僅被閹割而且被送進了瘋人院;康普生先生死于酒精中毒,就這樣,這個出過“州長和將軍”、曾經顯赫一時的家族敗落并消亡了。從前文中我們可以看出,基督教倫理“愛”的缺席與康普生的家庭悲劇有著直接的聯系。也正如蒂里希指出的那樣:“生命是現實性中的存在,而愛是生命的推動力量。……若沒有推動每一件存在著的事物趨向另一件存在著事物的愛,存在就是不現實的,在人對于愛的體驗中,生命的本性才變得明顯(蒂里希 308)。”
二.迪爾西:愛的在場與生存的希望
如果說康普生家因愛的缺失而導致的家庭悲劇為小說奠定的憂傷的基調,迪爾西的存在則為這部悲劇涂上了溫暖的亮色。迪爾西30年如一日地照顧康普生家的所有成員,用她的堅強和無私的愛支撐著這個搖搖欲墜的家。在傻子班吉過生日的時候,她自己出錢給他買生日蛋糕,對他的照顧充滿耐心和慈愛。當凱蒂因失貞被家庭拋棄時,她沒有鄙視凱蒂,反而充滿了同情與憐憫。對凱蒂的私生女小昆丁,她更像一個慈祥的祖母關心呵護著她,最大限度地降低杰生對她的傷害。在小昆丁受到杰生打罵的時候,她挺身而出保護小昆丁。迪爾西是個傭人、黑人,然而她正直、勇敢,能保持自尊。她不是斯托婦人筆下“湯姆叔叔”這類沒有尊嚴的善良的黑人,對于杰生的橫暴,其他人都得忍氣吞聲,而迪爾西卻敢當面責罵杰生不該對外甥那么無情。當凱蒂渴望見見自己的親骨肉小昆丁時,杰生硬是百般阻撓。面對此情景,迪爾西不畏強暴,挺身而出設法讓她們母女相見。她反問杰生:“我倒要問,讓可憐的小姐看看她自己的孩子,這又有什么不對!”面對杰生的惡毒謾罵,她斥責杰生說:“杰生,如果你總算是個人,那你也是個冷酷之人。我感謝上帝,因為我比你有心肝,雖說那是黑人的心肝”(224)。盡管她處于社會的最底層,卻沒有自暴自棄和變得自私,卻以一顆基督似的愛之心支撐著這個瀕臨破碎的家庭。有一次迪爾西女兒弗洛尼勸她不要帶班吉上黑人教堂,免得別人議論。迪爾西的回答體現了基督教愛的倫理的真諦。迪爾西說:“我可知道是什么樣的人,沒出息的窮白人。就是這種人。他們認為他不夠資格上白人的教堂,又認為黑人教堂不夠格,不配讓他去”(306)。面對女兒的顧慮,迪爾西又說:“你叫他們來當面跟我說,告訴他們仁慈的上帝才不管他的信徒機靈還是愚魯呢”(306)。這些質樸的話語是對基督教教義的最好的理解和闡釋,她將其融入了自己的生活,甚至生命之中。“在整幅陰郁的畫卷中,只有她是一個亮點;在整幢墳墓般冰冷冷的宅子里,只有她的廚房是溫暖的;在整個搖搖欲墜的世界里,只有她是一根穩固的柱石”(李文俊2004:5) 。
在這部小說中,迪爾西的愛是最感動讀者的,也是福克納所頌揚的,體現了福克納愛的倫理,即愛己與愛他人完美結合在一起。她身上所透露的尊嚴和無限的忠誠和慈愛與陰冷的康普生家庭構成了強烈的對照,更彰顯出基督教倫理“愛”的彌足珍貴。她的愛德和基督的是相通的。她是人類毅力、生命和希望的象征。
小說的書名取自莎士比亞著名悲劇《麥克白》中的一段有關人生的虛無主義的臺詞:“人生不過是一個行走的影子,一個在舞臺上指手劃腳的拙劣的伶人,登場片刻,就在無聲無息中悄然退下;它是一個愚人所講的故事,充滿著喧嘩與騷動,卻找不到一點意義”(莎士比亞:386—387)。康普生家族總體的命運與結局符合這一悲觀主義的調子,但福克納并非悲觀主義者,他對人類前途抱有堅定的信念,特別是以迪爾西為代表的人物身上所體現出的人性之美和道德力量。為這個悲劇故事增添了鮮明的樂觀主義色彩。迪爾西身上體現的基督教倫理的核心——“愛”的那種合理的超越性、普世性和利他性無疑為人情傾向淡薄冷漠的社會的希望之光。
《喧嘩與騷動》在為讀者描繪了一幅南方傳統社會解體的圖畫的同時,傳達了人類社會一個永恒的主題:人與人之間應當互相關心和愛護。他特別希望重塑家庭感情的溫暖,兄弟姐妹之間的友愛,父母對孩子的慈愛。正如《喧嘩與騷動》的譯者李文俊先生在其譯作的序言中所寫:“福克納也是要以基督的莊嚴與神圣使康普生家的子孫顯得更加委瑣,而他們的自私、得不到愛、受挫、失敗、互相仇視,也說明了‘現代人違反了基督死前對門徒所作的‘要你們彼此相愛的教導”(李文俊2004:9)。康普生家族由于“愛”的缺失而導致的生的絕望與迪爾西身上愛的在場所引發的人類對生存的美好希望形成強烈的對比,而福克納的倫理思想也得到了深刻的體現:那就是福克納在接受諾貝爾獎時所說的一段話“我相信人類不但會茍且地生存下去,他們還能蓬勃發展。人類是不朽的,并非因為在生物中唯獨他留有綿延不絕的聲音,而是因為人有靈魂,有能夠憐憫、犧牲和耐勞的精神。詩人和作家的職責就在于寫這些東西。他的特殊的榮譽就是振奮人心,提醒人們記住勇氣、榮譽、希望、自豪、同情、憐憫之心和犧牲精神,這些是人類昔日的榮耀。為此,人類將永垂不朽”(李文俊1980:254)。
注解:
1本文所引的《喧囂與騷動》譯文選自福克納:《喧囂與騷動》,李文俊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年),文中引用時只注明頁碼,不再一一說明
郭海平,武漢工業學院外語系副教授;郭肖,教師,現居湖北棗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