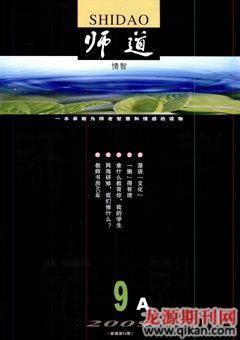人到中年急讀書
梁昌輝
讀書,在中國向來是講求實用,拿來做晉身之階的,以致現在不少學生一旦進了大學就放下心來,不再想讀書了。在我們那時,能上中專,跳出龍門的,已屬鳳毛麟角,于是考上中專就有許多人不再讀書了。
而我真正意義上的讀書卻正是從讀師范時開始的。一轉眼二十多年就過去了,如今人到中年,梳理自己自由自主的讀書生活,感覺倒有幾分像林間幽泉,曲曲折折,明明暗暗,既有素湍綠潭,懸泉瀑布,也有泄入罅隙,如墮無底之洞,幾乎斷流的險境。讀書之旅細若懸絲,如今想來,幾乎是一身冷汗。
一、曾經“硬”讀
像個讀書人,做個讀書人,一直是我內心的召喚。
我就讀的是一所農村初中,沒有圖書室,家中更是沒有書的影子。到了師范學校,學校不僅有圖書館,還有一間寬敞的閱覽室,架子上整齊地擺放著各種報紙雜志,讓人眼饞得很。圖書館學生是可以借書的,只是那間敞亮的閱覽室只允許老師們進入,讓人大為遺憾。
進入師范學校不到一個月,得悉學校的圖書館是我們地區藏書量最大的,心中驚喜異常,幾次實地“勘察”后定下了一個“堅硬”的讀書計劃:每天讀書100面。于是,讀癡了:課間讀,晚飯后讀,就寢后讀,教室里讀,走廊里讀,沙河邊讀……學校圖書館有個不太受人歡迎的規定,學生不能進到里面,只能隔著一排桌子用眼睛選書,所挑選的書大多局限在第一二排書架上的。由于我的視力較好,可以用眼睛“挑選”到第三、四排書架上的,那幾架上多是一些大部頭,或者是哲學宗教類的書。
小說、散文的可讀性最強,青年的富于幻想使詩歌一度占據了我閱讀較大的比例。其中,學校圖書館里的那一套幾十本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文庫”耗去了我幾乎一年的時間。后來,在一個朋友的帶動下,我開始接觸了一些哲學方面的書籍,開始知道費爾巴哈、黑格爾,了解到青年馬克思的艱難生活和思想淵源。世界在帶給我浩大無邊的印象時,更讓我驚嘆于那些思想者的睿智與深邃。
我貪婪地讀著,成了學校里唯一帶煤油燈的學生,晚上9點學校熄燈后,我就點亮油燈繼續讀書,以至今天我還保留著一個習慣:同室人的鼾聲越響,我讀書精神越好。每天讀書100面的“硬”計劃和每晚的油燈給同學們很深的印象,畢業留言時不少同學提起它們。
這一階段成為我一直引以為豪的一段時光。
當年的師范學校現已與當地的一所學院合并,我曾回去看過。但每當憶起師范學校時,我想到的總是那座高臺階的灰墻灰瓦的圖書館,那一排排森立的書架仿佛就站在我的眼前。或許我早把她當成了自己的書房了吧。
二、也曾“悅”讀
回到家鄉小鎮工作的那幾年,值得一讀的書籍不多,記憶中好像只有《白鹿原》和《廢都》印象深點,閑空時讀點《讀者》(那時還叫《讀者文摘》)、《遼寧青年》和省城的一份晚報。后來學校得到田家炳基金會的支持第一次建立了圖書館。雖然并沒有什么直接關系到教育教學的書籍,但總算有了圖書館。
這類的閱讀,基本不會“磨”腦子,就是讀著玩,但絕不是玩賞那一類的讀法。今天回顧起來,這樣閑散的閱讀似乎除了增加酒茶時的談資外,幾乎無足稱道者,不僅隔斷了與學術界的絲絲縷縷的聯系,也使自己浮躁起來,無論口味和心氣都經歷著日漸下墜乃至滅絕的危險。
唯一的與外界的教育聯系是《中國教育報》。我工作的那十年學校年年訂閱《中國教育報》,這在一所鄉村小學幾乎就是奇跡了。我是每期必讀的,這份權威的教育大報始終保持著最敏銳的觸角和教育覺察力,幫助我較早地感受到教育的脈動。它對世紀末的那場教育大討論的全程關注引發了我對教育現狀第一次較為深入的思考。當然,《中國教育報》還給了我一個重要的影響,就是它連續刊登的招聘廣告最終促使了我的“逃離”。
在家鄉工作的十年,我有了自己的房子,并辟了一間書房。書房不大,六七平方米的樣子,好在只有一只書櫥,也就不顯得太擁擠。書櫥里文學類書籍居多,我反復閱讀的是一套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刊印的文叢,收錄了卡夫卡、海明威、托爾斯泰等十位歐美文學大師的各一部作品。這套作品對社會觀察之深刻,對人性思考之深入,以及大師們所抱持的對人性的同情和悲憫的情懷,深深地影響了我的文學審美趣味和觀察問題的基本態度,是一次真正意義上的文學啟蒙性閱讀。錢鐘書的《人間詞話》和司空圖的《詩品》,我是硬啃下來的,還有朱自清的一本小書《經典常讀》,它們一起奠定了我的一點中國傳統文藝理論的基礎。大約是1995年,我第一次完整地閱讀了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新華字典》,也算是補了一點“小學”的課。
遺憾的是那時的書房里除了讀師范時的幾本教育學、心理學和教學法的教科書,沒有真正的教育類書籍。如今想來,仍有幾分心痛,深深體會到了明朝宋濂的那份“益慕圣賢之道”的渴望和“又患無碩師名人與游”的惶恐與憂慮。
三、而今“急”讀
“而立”的古訓令三十歲時的我下定了外出的決心,應聘到了江南,繼而來到華士、英橋。這里學術氛圍比較濃厚,經常舉辦各類教育交流活動,可以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專家、國內的教育教學專家包括特級教師們面對面地進行交流。更有身邊的一群熱愛教育的朋友們,他們經常在教育類報刊上發表文章,其中好幾位還有個人專著行世。
在這樣的一個群體之中,在這樣的一個氛圍之中,感覺機體的每個細胞都被經歷了“核裂變”,一股向上的偉力將我完全裹挾了。在個人的激情被激發起來的同時,一種焦慮始終縈繞左右:我在進行教學研究和寫作時,理論的淺陋、知識的割裂時時阻滯著自己。于是猴急似的尋書來讀,一頭扎進偌大的學校圖書館,只揀教育教學類的書籍、刊物,結果發現自己所缺太多,簡直無從讀起!
幾經周折,決定溯源窮流,即從教育的源頭一路讀來,教育哲學、心理學、教育史、課程論、教學論以及各種文論,一本本讀著。
2008年暑假,妻兒回老家了,我獨自一人留守讀書。床頭柜上,沙發上,桌上,椅上,甚至樓梯上,廁所馬桶的水箱蓋上,哪兒都是書,走到哪兒拿起一本就可以讀。這是一個瘋狂的讀書假期,除了睡覺和每天簡單的三餐外,全都用來讀書。冰箱里塞一點食物就好幾天不出門。一個暑假,粗略算了算,大約讀了兩千萬字。讀了,有了靈感了,就打開電腦敲一點文字。
不僅讀,也買。有些書,圖書館沒有,朋友們也沒有,就自己買來讀;有些書,也許圖書館有,也許朋友們有,也要自己買來。不僅讀,還要作為珍存的資料,以備查閱。我不抽煙,不喝酒,買書是我最大的個人開銷。外出聽課,開會,總要抽點時間逛一逛書店,看到心儀的就要買過來。近幾年學會了網上購書,就方便多了。這么一來二去,家中的書就多了起來,租住的房子的書柜放滿了,就用紙箱裝,擺得到處都是。雖然床下都塞滿了,還是會去買書,讀書,因為近二十年的教學實踐有著太多的困惑,太多的理論虧欠,也有著太多的“饑餓”。
這一次的集中閱讀帶來更多的是一種怡然的享受,如一次麗景佳致不絕于目的游歷,有契合自己思考的會心,有柳暗花明的豁然,有條分縷析的梳理,更有開路架橋的交通。
四、獨門“站”讀
中年,無論是家庭還是工作無疑都是要挑重擔的階段,讀書的時間簡直細如一隙,能否撐出一條縫來全賴個人的毅力與耐力。在這樣的夾縫中我則練就了一點“獨門絕技”,“站讀”便是其一。“站讀”的靈感來自法國作家巴爾扎克的站著寫作,“站讀”可以更專注更投入。清晨妻兒尚在酣睡時讀上十分鐘,午間昏昏欲睡時“站讀”一會兒,晚飯后站在走廊上在“落日圓”的陪伴下看上幾分鐘,這兒“站”一點,那兒“站”一點。一天天積累,一年下來,面對估算的千萬字以上的閱讀量,心中的那份竊喜真有點像葛朗臺吹聽金幣響時的情狀。
這樣趕集似的閱讀,提升了我教育教學實踐的理性。我主張并努力實踐著教育克制的理念,即教育的本質和師生生命質量的提升以及學校作為精神家園的價值追求,都要求我們教師在實施教育教學時,要學會克制,多一些教育性理解,多一些人性溫暖,讓教育閃現著充滿魅力的迷人色彩。我期待“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的理想教育景象,期待教育更從容,教師更優雅,學生更靈動,學校真正成為師生的精神家園。
讀書引導著我的教育實踐,同時我也通過寫作來整理和提升讀書所得、實踐感受,使一些混沌的思想得以清晰,讓一些似是而非的做法在理性之篩上進行過濾。汗水過后也有了一點老農“喜看稻菽”的快樂,近幾年,我開始有一些教育教學文章獲獎,或在教育教學類刊物上發表。
從借書到借、買結合,從寥寥十幾本到數百本,從“雜然而前陳”到逐步“專業化”,從無到有,我的書房和我的專業成長同頻共振著。從隨意閱讀到專業性閱讀,從著眼茶余飯后的海闊天空到立足于教育實踐的溯源、解惑,從單純讀書到讀寫做結合,我感覺自己正在成為一個讀書人,享受閱讀,并逐漸超越閱讀。
(作者單位:江蘇江陰市英橋國際學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