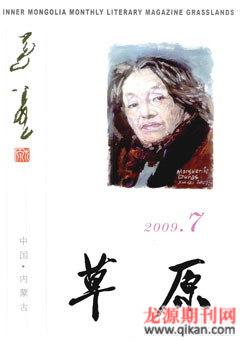博爾姬·塔娜散文小輯
博爾姬·塔娜(蒙古族)
第一次招待媽媽
兒子上幼兒園中班的時候,有一次我接到老師的電話:開家長會。我按照規定的時間,和別的家長一起坐在一個教室里等老師。
一會兒,門輕輕地推開一條縫,兒子的小臉出現了,原來于伯樂上衛生間路過這里。意外地發現了媽媽的“蹤跡”,哇!怎一個“喜”字了得!
他滿面笑容地看著我。站在門口不走啦!我再三保證,開完家長會一定接他,他才不情愿地回去了。開完會,我去中一班,兒子讓我看:這畫著大紅碗的小拒是他的(小孩們不識字,都用鮮艷的圖形做標志)。里面的小碗也是他的(我怎么會不知道呢,可還是很高興地聽著)。兒子用他的不銹鋼小碗從保溫桶里接滿水。端給我喝。他大概覺得這種“在自己平時待的地方招待媽媽”的感覺很受用,也很新奇,就一碗接一碗地給我喝水(能多聽幾次謝謝),他自己仿佛也覺得今天的水格外好喝。也一碗接一碗地喝,最后,母子倆喝得動一動胃里就會有“嘩啦”的輕響,差點走不動了!
這次“招待”的結果是:晚上兒子尿床了。
掙紅包
舅舅結婚那天,兩個外甥偉丹慕和于伯樂歡天喜地承擔了一些任務,最主要的是領紅包。什么給新郎新娘戴紅花、端湯圓碗、給新郎新娘壓床,都有紅包。
他倆跟隨舅舅接新娘,新娘一出門,倆人又一人得了一個紅包。路上。因人員需要調整,偉丹慕坐到了舅舅的車上,另一個車上的于伯樂立刻看到了。擔心地說:“哥哥肯定多領了一個紅包。”小白阿姨看于伯樂眼圈紅了,獻計說:“你呀,一下車就往里跑,拿好毛巾洗臉盆,舅舅、舅媽一到,讓他們洗洗手。”
“他們不去衛生間洗嗎?”于伯樂問。“那你就別管啦。聽阿姨的沒錯!”小白阿姨說。
車停了,于伯樂不顧震耳的鞭炮聲,從阻擋新郎新娘的人群中拼命擠進屋里,直奔衛生間,然后肩搭毛巾、手端臉盆,前腿弓、后退蹬,虎視眈眈地站在了客廳(這形象留在了婚禮錄像里,大家最愛看)。當舅舅沖破“千難萬險”橫抱著舅媽沖進來時。于伯樂飛快地迎了上去。自然迎來了又一個紅包。
兒子的小招數
自治區60年大慶的前一個月,我為內蒙古電視臺的一個片子寫解說詞,時間太緊,導演要求大家都住在賓館,以便隨時溝通、改動。
寫啊寫啊,我想兒子,兒子想我。摘錄一部分兒子給我發的短信:“媽媽我愛你”、“媽媽我想你”、“媽媽你在哪里?”、“媽媽你不回家?”、“媽媽快來呀!”……那天晚上都10點多了,最后一條短信讓我大吃一驚。問兒子怎么了,其實,兒子正在他爸的監督下寫作業。老公怕影響兒子的功課。不允許他放學后來找我(我就住在天元對面,離家不遠),于伯樂吃不慣他爸做的沒滋沒味的面條,晚飯沒吃好,又見不到媽媽。有點受不了。我也受不了啦!
夜深人靜,我趁導演不注意,溜出賓館,直奔24小時營業的麥當勞,給兒子買了雙層吉士漢堡、熱巧克力、麥樂雞塊、雀巢冰爽茶,打道回府。
唉,自己的家,弄得跟賊似的,我躡手躡腳爬上4樓開門。聽見北面房間里老公在打呼嚕。兒子在南面的屋里眼巴巴地等我。
看著兒子像小狗一樣狼吞虎咽地低頭吃著,我差點哭了。才幾天啊,怎么就像個吃不上喝不上的孩子了呢!兒子吃飽了。又有媽媽摟著。心滿意足,很快就睡著了。
本打算早上神不知鬼不覺地溜走。可老公怕兒子睡過站。早早來叫。于是發現了我們的秘密:“嗯?你啥時候回來的?”
“半夜。”我說。
“唉!你這是干啥呢……慣……慣吧……”老公嘀嘀咕咕發泄著不滿,我和兒子偷偷地笑了。
第二天,兒子提出要到媽媽那里寫作業。他爸勉強同意了。但條件是做完作業后必須回家。傍晚,兒子終于如愿以償來媽媽這里了,小臉上寫滿了高興。我安頓兒子吃賓館的特色菜,然后回房間寫作業。
兒子一會兒說渴了要喝水,一會兒說累了要休息片刻。我覺得這孩子在拖延時間,就連連催促他快寫。趁我沖涼,兒子說再休息一會兒。我出來時,發現兒子在閉著眼睛假寐,長長的睫毛卻在動。啊!他在耍小心眼兒呢!他想盡量睡著。造成“既成事實”,我也就留他在這里住了。
可是。兒子的這些小招數。不就是為了扣媽媽在一起嗎?當媽的想想真心痛。那天,我和兒子一起回家了。
夜晚的呼和浩特城華燈璀璨,我和兒子格格地笑著,手拉手走過新華廣場回家,在每一個攤點都買了小吃。吃著大碗酪、稀果干、冰淇淋、烤肉串。我們像走在一個巨大的水晶宮里,滿心的甜蜜。
我橫下心想,不管那么多了,明天的事明天再說吧!
我的妹妹卓娜
我的妹妹卓娜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媽媽說,我出生后,爸爸特別喜歡我,就說再不要孩子了。這一個就夠了。可那時軍區大院哪一家都有一堆孩子。互為玩伴,其樂融融。媽媽覺得我都快上學了,還形單影只,好可憐。鄰居家的賽娜比我小3個月,可人家已經有3個弟弟妹妹了。后來。在我下面。曾有一對雙胞胎剛出生一周就因醫療事故死去。所以我的弟弟妹妹都比我小好多。現在我常向他們擺老資格:你們都是我抱大的!
我上中學時,卓娜才上小學,我當兵了。妹妹小學還沒畢業。
軍醫學校畢業實習的時候。聽說我所在的城市要地震。妹妹的小心眼兒里裝滿了擔心。小小的弦子,甚至為此而睡不著覺。她給我寫了好多信,其中一封竟然包著一綹漂亮的黃頭發和一枚碧綠的戒指。還畫了一張她對著我笑的頭像。一看那小黃頭發就是妹妹的。她很愛惜自己的頭發。可聽說這兩樣東西能保佑姐姐平安,就毫不猶豫地剪下寄來了。終于,她和小妹妹偉娜偷偷商量,要瞞著爸爸媽媽坐火車去看大姐。讓偉娜送她。
星期六中午放了學,兩個小女孩子背著書包直接去了車站,偉娜一向膽小。看到卓娜用平時攢的錢買了車票,真的要走,臉都嚇白了,結結巴巴話都不會說了。卓娜給家里留的條子上寫著:“我想姐姐。要地震了,我要和她死在一起。”
當我看到妹妹出現在營區時,簡直驚呆了,兩個人都哭了。妹妹在我這里住了一天,我領她逛街,盡我所能給她買了當時的好東西麥乳精、奶粉、巧克力豆、水果。帶她去食堂吃飯。我很高興妹妹趕上了周末改善伙食。記得是紅燒肉、西紅柿炒雞蛋、土豆絲、大米飯。
怕影響她的功課,星期天下午,我送妹妹回去。結果上了火車,妹妹是一路哭著回去的。回到家里,爸媽沒有懲罰她,他們也被這個重感情的孩子感動了。
以妹妹的聰明和堅強意志,考上重點大學應該沒有問題。可是妹妹要像姐姐那樣去當兵,于是,妹妹成了一名軍人,她是通訊兵。
那年。我去海拉爾參加解放軍總政治部組織的筆會,途經張家口。那時妹妹已考上軍校,在張家口上學,得知這個消息時。正趕上考試。妹妹看時間不夠了,放棄了一道20分的大題不做。請假直奔車站。妹妹是全隊成績拔尖的優秀學員,這么做,實在
是因為姐姐在她心日中的分量要比榮譽重得多。
還清楚地記得,列車駛入張家口站,一起打撲克的作家忘了徐揚還是白雪林說,站臺上,有個小女兵捧著西瓜和冰激凌不知在等誰。我跳起來就往外跑。
我永遠記得那個美麗的夏天。一個大眼睛、白皮膚、身姿纖細挺拔。齊肩秀發飄拂在微風中,在陽光下對我笑著的女兵。我可愛的妹妹卓娜!
我倆對著笑、笑……可不知何時笑變成了眼淚。鈴響了,我紅頭漲臉地回到車上(我常納悶,影視劇中的人為啥怎么哭都不會像我這樣狼狽呢),怕人看到我這副樣子。在風擋處站了好長時間。
我給爸爸媽媽寫信說了見到妹妹的事,爸爸回信說:“你們兄弟姐妹感情這樣深,爸爸媽媽真是欣慰。以后,當我們老了,不在世了,知道你們彼此牽掛惦念,也可安心上路……”
因為是家里的老大,我對卓娜的影響很大,這些影響有好的也有不好的。
卓娜的生活軌跡幾乎和我一樣。我畢業于北京軍區軍醫學校。因創作上有些成績,內蒙古軍區送我到中文系學習,后改行。卓娜畢業于北京軍區軍醫學校,因創作上的成績改行做宣傳工作,寫稿、攝影、攝像。她的文筆清新幽默大氣。一些隨手寫的小文章常惹得我哈哈大笑。她的長篇通訊寫得好。一些抓拍的圖片特別漂亮!果然,妹妹因成績突出立了三等功。對于一個女孩子來說。能在部隊立功受獎是非常不容易的。
說到對妹妹消極的、不好的影響,我滿心慚愧。
我們都在二十多歲就提干了。按照通行的規則,就可以考慮戀愛的事了。可是我常向妹妹灌輸“女人經濟獨立、能養活自己,就完全可以不結婚”的思想。兩個妹妹深信不疑。不知為什么,爸爸對我的這種偏激念頭居然持贊成態度。現在想起來。爸爸是覺得寶貝女兒只有在爸媽的羽翼下才能保證不受委屈,誰知道她們會碰上什么男人呢?部隊本來就男多女少(小妹妹偉娜也在卓娜考上軍校那年當了兵,是衛生兵),我們堅持這種理想還真不容易,也傷害了剮人,搞得現在磕頭碰臉的好像盡是有過“曾經”的人,其實還真不是那么回事。(關于我家女孩子里的“人尖兒”小偉娜。就是另一個長長的故事了。弟弟對小敏評價他這個小姐姐的時候說:“偉娜是塊金子,放到哪里都會閃光”。)
從北京軍區調回內蒙古軍區之后,我被分在253醫院工作。離家近,我越來越懶散,經常不回宿舍,愛回家住,不值班的時候就睡懶覺(每天看書到深夜,實在起不來),常挨老媽批評。一次,老媽趕我起床,我聽到爸爸說:“別叫啦,讓她再多睡會兒吧。以后出了嫁,就睡不成懶覺了。”媽媽不高興了,說:“她都27歲了,我跟你結婚時才20歲。你怎么沒這樣關心關心我呢?”
后來我結婚了。仍然一直睡懶覺。老公比我大3個月,過去。他醒了看到我還睡著,很不甘心。總想法子揪揪頭發捅捅臉弄醒我。遭到我的激烈反對后,他就認命了。這些年他積極做早點,然后故意贊嘆他的關食如何香甜,吸引我和兒子。其實他的早點并不好吃。但為照顧情緒。我們做出狼吞虎咽的樣子(過后俺倆就直奔麥當勞),他就會特別高興,笑咪咪地看著我們。只有這時,我覺得他很像我的爸爸。
卓娜的愛人特別好!她的愛人畢業于東北財經大學,高大英俊,不抽煙不喝酒,現為萊公司副總。最為難得的是。人家愛做家務!愛做飯!不愛應酬!卓娜家有精神、有物質,老媽說,這是她為父母、兄弟姐妹無私付出的回報。只是。受我的“毒害”。我們都結婚晚。孩子也小。
我們三姐妹經常做蔓夢:弟弟有個孩子該多好呀!弟弟結婚兩年多了。弟媳如果生了孩子,我們商定一起去伺候月子,不讓他倆累著一點兒。為此,我們都不休假,什么時候弟弟那里需要。我們再休。
生日這一天
11月1日是我的生日,一早,弟弟打來電話“祝賀大姐生日快樂”。他說。重慶在下雨。盡管我特討厭時下人們動不動就把有魅力的男人聲音稱作“有磁性”,可我還是要說。弟弟的聲音真是有磁性的,那樣陽光,那樣健康。充滿魅力。他的笑,一定照堯了山城陰暗的天空。
比我小十幾歲的弟弟是全家人的寶貝,爸爸媽媽對這個惟一的兒子不知怎么愛才好。在他小時候,放學回家抱弟弟是我每天必做的功課。我成天抱著這小胖子,抱不動了就背著,給他唱各種歌。直到現在,我叫兒子還總是一不小心就叫“五一,過來一下”。小妹偉娜也常把兒子偉丹慕叫成“五一”。大妹卓娜生了女兒,很奇怪地。她也常常一著急就把女兒彭一禾喚做“五一”,這聰明可愛的小弟弟。也是我們姐妹3人的寶貝。
在北京的小妹偉娜發來短信,“祝贅深少女生日快樂!”落款“一個崇拜你的老同志”。我笑出了眼淚。回復她:“你這‘老同志還是俺抱大的呢。”我給他們3人回短信說:“真感激勇往直前的老媽生了咱們4個(老爸當年思維超前,準備只要我1個,可老媽不同意),使咱們4人每人都有3個最忠實的死黨,而且是‘不用宣誓永不叛黨型的……”
在生日這天。我想起了弟弟妹妹,想起許多往事。我想他們。
弟弟長得好看。眉毛濃黑,眼睛大而黑亮,高鼻粱,寬額頭,黑皮膚(我們姐妹仨都隨了爸爸的白皮膚,對他的黑很羨慕)。
弟弟特別聰明,學什么像什么。研究什么就一定研究透徹。他上中學時翻我的書,翻到一本瑜伽方面的書,居然琢磨懂了,每天都做。后來能做許多高難度動作。他對戰爭史、兵器知識、蒙古史了解很多,也很深,一談起就滔滔不絕。我當了13年兵,號稱中文系文研班畢業。還免不了從他這里汲取養料。弟弟說話特別幽默,他的同事告訴卓娜。平常的話到他嘴里。不知怎么就逗得人前仰后合。弟弟性格剛烈,嫉惡如仇,上學時就愛打架,那時。總有家長找上門來告狀。(我兒子在班里總受欺負,曾3次被勒索,嚇得不敢上學,當舅舅的氣得要去揍那小霸王,我們說。一個營職軍人去打孩子。豈不成了新聞?他只能哀嘆外甥怎么不像舅舅?)弟弟個子不高,但因常年練拳擊、踢足球,身體特別強壯。在上海軍醫大學學習期間,一次在公交車上,看到一個扒手掏錢包,弟弟一把抓住那人的手,當時就覺得那人的手指特硬,每根都有小胡蘿卜粗。弟弟感覺有些抓不住似的。那小偷身高1米82以上,很壯,所以也很狂,弟弟把他的指頭使勁向后掰。扒手因痛受到制約。兩個人僵持很久,車上無人相幫,眼看天色將黑,車停靠一站,又上來3個小偷的同伙。弟弟思忖再下去要吃虧。就將扒手從敞開的車門一腳踹下去。自己迅速從另一個門下車上了出租車返回軍醫大。
弟弟尊重女性(爸爸家族的男人都是如此,爸爸對性格粗糙的媽媽從未說過哪怕一句重話),他常說,男人欺負女人是很惡心的。
弟弟和軍醫大學的同學小教相愛了,小敏在放假時來呼和浩特,我們才見識了南方女孩的漂亮!
小敏1米69的個子。腰細腿長。體重還不到100斤。她皮膚雪白,一張干凈的小嫩臉上,眼睛又黑又大,眉毛長而黑。小敏
平時從不化妝,穿一身軍裝,是那么美麗。在結婚那天。畫了新娘妝的小敏,穿上雪白的婚紗,簡直美得驚人!老媽開心得笑個不停。我當時看得眼睛都直了。淚水悄悄涌出來。我想,爸爸若是能看到他的寶貝兒子和仙女般的兒媳該有多么好啊!(結婚后,小敏在幸福中長了10斤體重,弟弟因而管人家叫“陳胖子”,真無恥,他自己那么胖還說別人。)
弟弟最讓人佩服的是孝順。老媽愛嘮叨,說話特狠(我因此而害怕哲里木盟科左后旗的女人,尤怕那種煙酒嗓的)。一次,老媽把弟弟罵得臉色煞白,他一聲不吭。我想起爸爸當年挨罵臉色煞白的樣子。十分心疼。怕弟弟氣壞身體。就在事后給他打電話,建議他再遇到這種情況就頂回去或走開。弟弟聽了。只說了一句帶有怒氣的話:“她是我媽!”就把電話放下了。我頓時感到自己差弟弟遠了!在干休所院里。媽媽有個綽號叫“福疙瘩”,大家說她的4個兒女一個比一個孝順,這里首當其沖的便是卓娜、偉娜和弟弟,我愛和老媽記些“小仇”,耍些小性子,真是不應該。從今天起,真的要向弟弟妹妹學習。
弟弟婚后兩地生活,是小敏來還是弟弟去?他們倆都表示可以到對方的城市去。最后,為了愛,弟弟決定去重慶。也許是上天保佑,那一年,重慶有一個很好的單位接收轉業軍人,機不可失,卓娜替弟弟積極爭取,弟弟當年成功轉業,隨即進了那個單位。
重慶的熱對弟弟來說是一個艱巨的考驗!他幾乎不能適應。也難怪他,當年,蒙古人最厲害的時候,沒怕過世界上任何人,但卻有兩個弱點:一怕熱,二怕水。怕水的問題好解決,大宋的水軍將領被俘投降后,就可幫助訓練蒙古人并帶兵打仗。但熱的問題一直困擾著他們,因此,一些酷熱的國家,蒙古人無心去征服。打下來也無心久呆。蒙古人在涼爽的地方生活了幾個世紀,哪遭過這樣的罪?
弟弟畢竟是好樣的。去年夏天,弟弟在零上44度的高溫中,穿著制服皮鞋穿行在大街小巷,弟弟的破案、結案率全支隊最高,不久就升職做了副支隊長。小敏說,弟弟每天早晨一睜眼就開始進入工作狀態,盤算這一天該干些什么,每天必提前半小時上班。“他敬業得讓人害怕!”卓娜問過他,為什么這樣拼命干?弟弟說:“為了讓老媽提起我的時候高興。”
老媽,你真有福氣!
我的城市
我很高興我住在呼和浩特。尤其慶幸我住在北郊的賽馬場。
我和妹妹有晨練的習慣。
晨光熹微。后勤干休所這一帶像是深深的海洋底部的一片空地,波瀾不驚。靜謐如夢。
天空是勻凈的青黛色,而東方天際卻是一片淡淡的晶藍。影影綽綽的霧(隨著一些商業性的什么“大營”、“二營”的安營扎寨,曾在烈日下為我們投下綠蔭的樹木被砍伐,酒肉的濁氣吞噬了負離子。霧。越來越少了),像仙女的飄飄衣袂,從松林、柏墻那里,從玫瑰花樹和金銀花藤那里帶來清香清香的味道,讓你全身的每一個毛孔都想歡暢地呼吸……百米開外。云堆霧繞之處,有位蒙古武士靜靜佇立在天地之間,他的巨型“頭盔”有36米高,他寬闊的“家”,面積有30多公頃——你看。賽馬場主樓頂部的穹廬型蒙古包,看上去多么像從800年前策馬疾馳回到現代的蒙古勇士,甲胄森然,眉宇含笑,正準備向圣主報告前方的好消息。
向北望去,這么多年來,我一直都能清楚地看到蜿蜒的大青山,我熟悉它的樣子,就像熟悉一個老朋友。它有時洗澡,暴雨云團懸掛著簾幕;有時跳舞。小草和矮樹捕捉著狂風;它有時歌唱或沉思,或喜或悲,我都能與它心意相通。今年我看不到它了,摩天大廈遮住了北面的天空。我忍著失戀般的落寂與難過想著,今后。就讓大廈與它交談吧,也許是個不錯的朋友。
晨跑過,早飯去哪里吃?去“格日勒阿媽”那里去。那里能喝到滾燙香濃的奶茶,還能吃到奶皮子、鮮奶油、炸油餅、干牛肉。去百年老字號“麥香村”?那一定要吃燒麥!燒麥皮薄,晶瑩透明,味莢不膩,實在好吃。這里的許多漢族人吃蒙古美食上了痘,說幾天不喝一次羊肉湯就渾身不舒服。好多蒙古人也常常簇擁在“麥香村”等座位。戶口簿上的“蒙古族”和“漢族”。分不開人們的胃啊!
這里有黃沙蔽日的時候。當天空的咆哮遠去,頑強的綠色就會露出笑靨。5年前,呼和浩特園林綠地景觀開始大發展,我們建成了長43公里、面積197公頃的二環路綠化帶和阿爾泰游樂園、春度公園、樹木園等。完成了青城公園、滿都海公園、公主府公園、八一游園、四千米游園的改造。2006年。建設了扎達蓋公園、大青山野生動物因、蘇雅拉公園、濱河公園、仕奇公園、北郊公園,綠色在伸展,綠色在覆蓋。我的好多朋友住在南國、海濱、山城、春城,我知道,那里很好,可是,我們也很好。我們的家在這里。親人在這里,我們的奮斗、我們的回憶、我們的生死歌哭都在這里,我們已和這親切的所在融為一體了,能不好嗎?還記得那首北朝古歌嗎?“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蘢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現牛羊……”這是我們的祖先詠唱過的心靈之歌呵!如果能請當代中國最優秀的蒙古族作曲家三寶再為它譜曲。那我們的耳朵和心靈就又要享受一場了不起的盛宴了。
你們上班騎馬嗎?
清晨,當我們在餐桌上喝著香濃的牛奶時,你可知道,中國人每消費兩杯牛奶,就有一杯來自內蒙古。
夜晚。古老而又年輕的北京華燈璀燦,流光溢彩。你可知道。裝扮這座城市的每10盞明燈中,就有7盞是由來自內蒙古的電燃亮的。
2007年,是內蒙古自治區成立60周年。昔日“天蒼蒼、野茫茫”的內蒙古。正在向世人展示她的力量和歡顏。
17歲那年,我離開父母。離開家鄉到遠方去當兵。那時。“皇城根兒”的子民們對來自偏遠地區的人有著淡淡的優越感和好奇。同室的戰友甚至領來別的連隊的女兵拜訪我這個蒙古族女孩。她們爭相索取我穿蒙古袍的照片,她們的談吐、見識、不同的生活方式也確實讓我耳目一新。可是。我還是無法抑制想家的念頭。一次。我有事去連部,剛進門就看到了墻上的一張列車時刻表。那上面一排站名的后面赫然寫著——呼和浩特,頓時,心像是被什么撞了一下,我哭了。這4個字代表著爸爸媽媽、弟弟妹妹、熟悉的軍區大院和以往的一切,有著非同一般的意義。正如一首民歌所唱:“這里好嗎?那里好嗎?哪里有家哪里好。”
1987年8月,在北京飛往廣州的航班上,一個皮膚粗糙、眉骨突出的南京女人竟然問我:“吃過餃子嗎?知道烙餅嗎?你們有父親嗎?”
1998年3月。我持旅游簽證由珠海去香港,海關一個年輕的工作人員久久看著我的名字。讀了幾遍之后笑著說:“我第一次見到蒙古人。”
是啊!他們不熟悉我們。
常見到一些發達省市的同胞。對美國的50個州如數家珍。甚至對那里的小鎮、小城都像自家菜園子一樣熟悉。可他們就是不知道、不熟悉、不了解內蒙古,最經典的一句話就是:“你們上班要騎馬嗎?”過去
這樣問。現在仍這樣問。這引起了我的好奇:他們真的不知道?
在一個晚宴上。一位白認為英俊瀟灑的有錢人又向我請教這個問題,我不動聲色說:“是啊!每天騎啊!”
“那……你在幾樓辦公?”
“10樓啊!我們那里的電梯都是特制的。有馬的地兒。上了樓,把馬拴在消防栓那里,我辦公。下班一起坐電梯下來……”
沒等說完,大家都笑倒了。那有錢人尷尬地咳了兩聲,指著我說:“淘氣拐(鬼)。”
其實。完全不必如此意氣用事,我們過去的貧窮落后是真的。現在的發展也有目共睹:最近5年。內蒙古GDP增速連續保持全國第一;呼和浩特市連續6年在全國省會城市中競爭力名列第一。被經濟學家稱為“內蒙古現象”,令人刮目相看。我想,任什么人也不應該裝作不知道內蒙古了。
在這片誕生過無數英雄和詩人的土地上。時間不會白白流過。這僅僅是第一個60年釀造的芬芳奇跡,我相信,奇跡的后面還會有奇跡。
我的怪力亂神體驗
這些事真真切切地發生了,我反復地想,始終不得要領,我曾講給朋友,她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第一件:幼年,約四、五歲,媽媽牽著我的手,在軍區司令部院由西向東走。在過了中門崗哨約十幾步之后,我忽然覺得后背有一把巨大的扇子打開了(既是后背,就看不到,可腦后就有這樣的感覺:這扇子好像對我不利,在覬覦著什么),我很害怕。那時,媽媽很愛打扮我,光是小辮子一天就換好幾次。那天,媽媽給我接了長辮子,一甩一甩的細辮子讓一只大公雞誤會了。以為是蟲子,就尾隨著我們,等待機會。在我害怕的時候,正是大公雞要發力的時候。它跳起來咬住我的辮子一拽,我的腦袋向后一仰,就大哭起來。媽媽大驚失色,和站崗的叔叔一起趕走了那只可怕的公雞。
問題是:我為什么會有災難即將來臨的感覺呢?長大之后,就再沒有過那樣的感覺了。
第二件:爸爸去世后的第一個“五四”青年節(爸爸3月18日去世)。我因為無法處理一些可怕的人和事,準備“逃走”。我拿了一大瓶新買的安眠藥和兩瓶水,計劃先去青山公墓看爸爸,然后一路進山,找個山洞。喝水吃藥。山間地形復雜,等找到我,我估計早走了。因為在這之前不久,軍區291醫院有一男一女兩個戰士成功自殺了,也是在山洞里。
我到青山公墓時,發現一個人也沒有。只有陵園門口有一個看大門的老頭,他說,沒人,都出去過“五四”青年節了。拿不上鑰匙,回哇!我想最后看一眼爸爸。就哭著往里走。
果然,門窗都緊鎖著,園內一片寂靜,我沿著各室的外圍走了兩圈也找不到人。就小聲叫著“爸爸”坐在了西面的窗下。
坐了一會兒,忽然聽見東面的某個房間人聲喧嘩,男女老少都有。說笑中還有一串鑰匙的聲音“嘩啦嘩啦”在響。我想,人不是都在嗎?看門老頭干嘛撒謊啊。就慢慢向那里走。想跟人家說說,看能不能給我鑰匙。
一間一間走過去,每一個房間都是空的!尤其感覺最可能有人的最東面的房間。桌椅擺設都蒙著一層厚厚的塵土!我頭皮一炸。感覺特別害怕,就回到原來坐著的窗下重新坐下了,我想,實在見不到爸爸,趕緊走吧,別誤了時間。剛這樣想,我頭頂的窗子像被一個很大力氣的人推了一把似的,“砰”一聲開了!
我當時也沒顧上想一想,沒有風,窗子怎么會開?可我只是高興,想著可以從窗子爬進去看爸爸了,就站起身來。但我立刻發現這是雙層窗,打開的只是外面,里面插著。還是進不去。
后來回想這些事。大家都說是爸爸救了我,人聲、鑰匙聲、窗子,這些事讓我多停留了近一小時。使別人在天黑前找到了我。
那些聲音。我到現在還清楚地記得,難道說爸爸的愛能夠穿越時間和空間保護我嗎?這世上真的有鬼魂嗎?
第三件:這是我不愿意面對的事。
那時,一個惡棍的糾纏讓我想不出對付的辦法(各種雅的俗的好笑的辦法都用過)。我要和曉思結婚了,可他不顧一切,不要臉。可我要臉。更難的是我不能讓曉思知道他的惡,不能讓家人知道他的惡。尤其不能讓弟弟知道。爸爸不在了,弟弟如果因我而觸犯法律。我還算是什么姐姐!我一輩子都會受良心的譴責。
諸多顧慮。惡棍更加囂張,說要用硫酸潑我的臉(他甚至給我看過一瓶硫酸),要劈死我等等。一天晚上,正在家看電視,聽到一個熟人的死訊。我想,這壞蛋怎么不死呢?生一場大病也行呀!可想到那惡棍身強力壯。連感冒都很少得,怎會得大病……就迷迷糊糊睡了。
第二天,他慌慌張張告訴我,他在家看電視,燈關著,11點多時迷迷糊糊睡著了,忽然頭頂上狠狠地挨了一巴掌,腦袋從墊得高高的被子上滑下一截。他大喊:“誰?”趕緊開燈四處看。房間里沒人。
后來。他那“挨巴掌”的地方得了重病,年輕輕的人不久就死了!
我真的不知道這一切是怎么回事。
一只叫小寶的小猴子
觀察過動物嗎?進而觀察過動物的眼睛嗎?不知為什么,我總是覺得。動物的眼睛和孩子的眼睛有相近之處。它們都干干凈凈,像沒有掛窗簾的明亮的窗子。喜怒哀樂,一覽無余。
曾經有一段時間,我天天去青城公園去看一只小猴子。一呆就是幾小時。小猴子那張嫩嫩的臉上。常常呈現出類似于人類的憂傷的神情。我很心痛,總是問它為什么不高興,可它不會說話。我只能猜測。
每次去,我都會帶許多好吃的給它:切好的蘋果塊、香蕉、紅蛋糕、白蛋糕、奶豆腐、砸出來的核桃仁、燒好的瘦肉、酸奶、爆米花,可東西丟過去,那些大猴子總是發出恫嚇的聲音撲過來搶,小猴嚇得魂飛魄散。迅速逃走。是啊,以它瘦小的身體,怎能搶過那些身強力壯的大猴子呢!我氣得罵那些大猴子“怎么不讓著小的”,自然沒有效果。后來,我想了一個辦法:爬進欄桿,用手遞給小猴子好吃的,看誰敢搶。
這樣,小猴子每天都能安心享受一頓美餐。可我發現,它拿到食物,總是先塞到兩頰存著。塞得鼓鼓的,才吃我另外給的食物。它是害怕大猴子再卷土重來。存糧以備不時之需呢!
小猴子認識我,每次去公園,我也有意識地總穿那件黑色長風衣,圍白紗長圍巾。它能分辨出我的聲音,遠遠的,我喚一聲“小寶”(我給它起的名字),它就飛竄而來,掛在籠子上,眼睛一眨一眨地盯著我肩上的包,手臂向著我伸出老長,它的小手總是涼涼的。我遞給它吃的,霸道的大猴子試探著也想搶。我就把它們呵斥走,等小寶吃完了。才給大猴子吃。
那幾個月。小寶快樂極了。我也快樂極了。后來。有人告訴我猴子們得了傳染性肝炎,我就不再去了。再去時,小猴子已不見了,可我已經把它當作生命中一個重要的朋友珍藏在心底,不會忘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