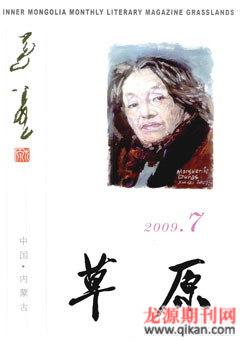孤獨(dú)的吶喊
辛 杰
說(shuō)實(shí)話,最初看到《跨越世界末日》這個(gè)書(shū)名時(shí),我以為又是一本俗不可耐的恐怖小說(shuō),且丟過(guò)一邊不提。待得有人告訴我這是一部赤裸裸描寫(xiě)官場(chǎng)的“官腐小說(shuō)”時(shí),我是大跌眼鏡,這樣沉重的主題似乎只有“生死抉擇”之類(lèi)語(yǔ)不驚人死不休的題目才壓得住陣腳,《跨越世界末日》怎么看怎么有點(diǎn)害怕,我不知道它會(huì)如何去述說(shuō)一個(gè)嚴(yán)峻的現(xiàn)實(shí)。
好罷,我們還是先讀起來(lái)再說(shuō)。
對(duì)我來(lái)說(shuō),閱讀慶勝的《跨越世界末日》這部書(shū),是對(duì)自己閱讀生涯的考驗(yàn),同時(shí)恐怕還是一次驚心動(dòng)魄的心靈歷險(xiǎn):在自己不能算短的閱讀過(guò)程中,在自己所經(jīng)歷的生存體驗(yàn)中,還從未感到會(huì)與一顆同樣在這個(gè)世界“飄泊”的靈魂如此貼近過(guò),雖說(shuō)我與慶勝?gòu)奈粗\面,但我們卻早已息息相通了。
官場(chǎng)是什么?如果說(shuō)官制是一個(gè)國(guó)家政治制度的一部分,那么,官場(chǎng)則是社會(huì)關(guān)系的一部分,是所謂的官吏們?yōu)榱俗约豪娌皇芮趾蚴亲约豪孀畲蠡Y(jié)成的關(guān)系網(wǎng)。官制是死的,官場(chǎng)卻是活的,生動(dòng)的,可以觸摸和感知的。《跨越世界末日》為我們描述的恰恰是另一種眼光的官場(chǎng)生活,這與以往的以官場(chǎng)為題材的作品相比是截然不同的。但我們無(wú)法懷疑它的真實(shí)性。這篇小說(shuō)最大意義在于它突破了“官場(chǎng)”小說(shuō)的程式化的固有模型,凸現(xiàn)了現(xiàn)代生活下孤獨(dú)人物的內(nèi)心世界,以及與此有關(guān)的各種物質(zhì)欲望和誘惑,這在以往同類(lèi)作品中是不多見(jiàn)的。對(duì)于一個(gè)職業(yè)編輯來(lái)說(shuō),選擇這部作品,是不需要任何理由的,而作為一個(gè)讀者,感覺(jué)到愛(ài)的震撼和直面生命的思考,是做出自己選擇的最好解釋。
小說(shuō)的主人公王倩妮來(lái)自窮鄉(xiāng)僻壤,卻胸懷大志,通過(guò)自身努力完成學(xué)業(yè)。她的人生道路布滿荊棘,情感生活出人意料,她的律師職業(yè)生涯中見(jiàn)證了社會(huì)生活的方方面面。真善美在慶勝的作品中淋漓盡致地表現(xiàn)出來(lái)。從形式上說(shuō),慶勝通過(guò)對(duì)主人公王倩妮存在的一連串疑問(wèn)而否定了自己:然而,從實(shí)質(zhì)上講,他卻通過(guò)對(duì)自己勇敢的否定而證實(shí)了自己的存在。在這部觸及靈魂的省思錄里,另一個(gè)悲劇人物陳學(xué)義躍然而出,力透紙背的沉穩(wěn)的思考和藝術(shù)家的感性判斷,憑著慶勝常人難以企及的勇氣和毅力。在經(jīng)過(guò)一次又一次文字煉獄般的煎熬之后。終于用自己的手,用自己的文字和思想,催生下了這本讓人驚嘆,讓人深思的《跨越世界末日》的書(shū)。
聽(tīng)朋友說(shuō)起,他先后干過(guò)工人、刑警、大學(xué)教師、商人、律師,并且還在錫林郭勒草原插隊(duì)當(dāng)知青。坎坷的經(jīng)歷,深厚的文化底蘊(yùn),促使他終于拿起筆,寫(xiě)下了這本厚厚的書(shū)。如果說(shuō),慶勝在他的小說(shuō)中還是以律師身份進(jìn)行陳述的話,那么,作者經(jīng)過(guò)深刻的反思。對(duì)自己的身份——自己的“知青身份”、“工人身份”、“警官身份”、“教師身份”、“律師身份”,乃至自己的肉體存在——進(jìn)行了一次次地否定。這種否定是他對(duì)人類(lèi)、對(duì)社會(huì)、對(duì)民族、對(duì)自我的最透徹的剖析和最勇敢的表述。真的,我很久沒(méi)有讀到這樣令人激動(dòng)的故事了。這部書(shū)的新意和精神上的刺激,蘊(yùn)涵在作家的勇敢之中。慶勝正是憑借著這種勇敢環(huán)視今日的社會(huì),并且如數(shù)家珍地羅列出什么是應(yīng)該存在的,什么是不應(yīng)該存在的,什么是合理的。什么是不合理的,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惡丑等。他不恪守任何東西,即非大家的痛苦,也非所得的知識(shí),他什么都沒(méi)有。假如他真有什么的話,那就是作家的良知。尤其是當(dāng)代小說(shuō)。與其是在講故事的發(fā)生過(guò)程,不如說(shuō)是在探究故事的消失過(guò)程。也即是著名作家?guī)烨兴嗫嘧非蟮囊粋€(gè)道理:小說(shuō)表達(dá)思想的方式是敘述而不是論述,是敘述的方式?jīng)Q定了思想的存在。其實(shí)。作家寫(xiě)作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完善一個(gè)人的生命。只有當(dāng)這段經(jīng)歷成為文學(xué)的一種,也就是生命對(duì)文學(xué)的想象,作家才能以同情、尊重甚至疼愛(ài)自己筆下的人物。最終寫(xiě)出真正屬于自己的作品來(lái)。從體例上說(shuō)。《跨越世界末日》通過(guò)女主人公王倩妮和男主人公陳學(xué)義通俗曲折的故事設(shè)置并探討了倫理、愛(ài)情、生命等諸多重大因素問(wèn)的矛盾沖突。像上帝和人類(lèi)開(kāi)了一個(gè)惡意的玩笑。把主人公毫不客氣地推到一個(gè)難以擺脫的困境之中。拯救即是扼殺,這把雙韌劍永遠(yuǎn)懸在每一個(gè)人的頭頂之上,時(shí)刻準(zhǔn)備著隨時(shí)落下來(lái),只要稍稍一動(dòng),就會(huì)毫不猶豫地落下來(lái)。將之?dāng)貍€(gè)萬(wàn)劫不復(fù)。但作家永遠(yuǎn)通過(guò)自己的方式傳達(dá)著自己的思索和憂慮。作家熟悉他筆下所有的人,駕馭他們就如活動(dòng)十分手指頭一樣自如,每個(gè)人到什么時(shí)候干什么,怎么表現(xiàn),說(shuō)什么話,都切合各自的身份個(gè)性,而且也寫(xiě)出了人物的復(fù)雜。羅蘭·巴特曾說(shuō):“作家不能喋喋不休,要學(xué)會(huì)掌握語(yǔ)言撩撥的技巧,要使在場(chǎng)的敘述本身和不在場(chǎng)的意義之間保持張力。”慶勝正是這樣在眾多的麻煩中理清頭緒。步步為營(yíng)揭示真相,故事的可看性也由此大大地誘惑著人。
閱讀慶勝的小說(shuō),使人興趣盎然還不在此——小說(shuō)在“沉淪”的主題中敘述著一個(gè)重大的主題——你明明可以感覺(jué)到誰(shuí)在犯罪。你明明可以意識(shí)到誰(shuí)是罪犯。誰(shuí)是受害者,但一切都如同霧里看花,走近了。眼看要觸摸到關(guān)鍵了……一剎那間卻蹦出另外一個(gè)人物來(lái),打破了時(shí)空界線,使月白風(fēng)清的朗朗乾坤又變得撲朔迷離了。讀下去。再讀下去。你會(huì)發(fā)現(xiàn)自己陷入了~張鋪天蓋地的黑網(wǎng),看到的卻永遠(yuǎn)摸不著,也無(wú)力去撕破這張網(wǎng),因?yàn)槟愀緵](méi)辦法,反而會(huì)被這張網(wǎng)纏死。我第一次在慶勝的小說(shuō)里找到了這種悲涼的感覺(jué),非常到位,正是這點(diǎn)讓我對(duì)這部作品刮目相看。在這個(gè)故事背后,是對(duì)一個(gè)嚴(yán)峻的社會(huì)主題的深入思考和洞察——我們的社會(huì)除了呼喚官員們的責(zé)任和良知之外,還需要更多不以人的意志為轉(zhuǎn)移的法律條文來(lái)規(guī)范我們的生活。否則,悲哀與無(wú)奈將伴隨著永遠(yuǎn)的守株待兔。
當(dāng)我終于一氣呵成地讀完慶勝的小說(shuō)之后,我突然感到一種如釋重負(fù)的感覺(jué),仿佛在另一個(gè)星球里,突然聽(tīng)到“自己”的語(yǔ)言,而這種語(yǔ)言,自己卻從未聽(tīng)到過(guò),更不曾使用過(guò)。正如英國(guó)小說(shuō)家戴維·洛奇所言:“小說(shuō)家的媒介是語(yǔ)言,無(wú)論做什么,作為小說(shuō)家。他都是運(yùn)用或者通過(guò)語(yǔ)言來(lái)完成的。”也就是說(shuō),小說(shuō)是語(yǔ)言的藝術(shù),所以羅蘭·巴特才強(qiáng)調(diào)“文學(xué)應(yīng)成為語(yǔ)言的烏托幫。”所以汪曾祺才直言“寫(xiě)小說(shuō)就是寫(xiě)語(yǔ)言。”準(zhǔn)確地說(shuō)。當(dāng)我借助——這位未曾謀面的老兄的這部作品時(shí)。我突然意識(shí)到:自己原來(lái)是一個(gè)多么天真的孩子!我突然發(fā)現(xiàn),自己所經(jīng)歷的生活竟然是一個(gè)孤獨(dú)孩子的童話小世界,一味地鉆在書(shū)房中,除了讀書(shū)寫(xiě)作外,對(duì)什么都不太懂,尤其是所謂人情世故的現(xiàn)實(shí)生活,真是觸目驚心,不禁大汗淋漓,噢,生活原來(lái)是這樣一種生活。
現(xiàn)在把慶勝的小說(shuō)冠以“官腐”小說(shuō)已經(jīng)貶低了作家,可我卻固執(zhí)地認(rèn)為一個(gè)作家寫(xiě)什么都是天生的,像聾子為什么那么聾也是天生的。好作家與壞作家之分就在于一個(gè)找著了自己只能寫(xiě)什么。一個(gè)還以為自己什么都能寫(xiě)兩下。作家創(chuàng)作的作品本身是靠天賦去寫(xiě)作的。真要認(rèn)真評(píng)論這本書(shū),我發(fā)現(xiàn)自己很難勝任。每部作者都認(rèn)為傾其心血的小說(shuō)其實(shí)都是瑕瑜互見(jiàn)的,只有職業(yè)批評(píng)家才敢直言不諱地評(píng)說(shuō)作品的好與壞。至于我自己。權(quán)當(dāng)批評(píng)的門(mén)外漢,這在某種程度上可以抵消我直達(dá)人性部分的軟弱或堅(jiān)強(qiáng)。一個(gè)人的吶喊是孤獨(dú)的,需要更多有良知的作家的吶喊才是真實(shí)和有效的。
記得當(dāng)代評(píng)論家李建軍說(shuō)過(guò),我們當(dāng)代作家缺乏對(duì)偉大的向往,缺乏對(duì)崇高的敬畏,缺乏對(duì)神圣的虔誠(chéng)。缺乏批判的勇氣和質(zhì)疑的精神。缺乏人道的情懷和信仰的熱忱,缺乏高貴的氣質(zhì)和自由的夢(mèng)想,缺乏令人信服的真,缺乏令人感動(dòng)的善,缺乏令人欣悅的美,缺乏為誰(shuí)寫(xiě)得明白,缺乏為何寫(xiě)得清醒,缺乏如何寫(xiě)得自覺(jué)。缺乏少得可憐的真正意義上的文學(xué)。如果說(shuō),誰(shuí)記住了痛苦和不幸,誰(shuí)就會(huì)沉重,誰(shuí)的內(nèi)心就會(huì)有更多的不安和憂患,那么,誰(shuí)若忘記眼淚和鮮血,他就會(huì)因此而遭殃,就會(huì)陷入更大的災(zāi)難。肖斯塔科維奇在他的回憶錄中說(shuō):“我應(yīng)該為所有死去的人。曾經(jīng)受難的人寫(xiě)一首《安魂曲》。”活著,并且記住。這是俄羅斯作家拉斯普京一部小說(shuō)的名字。其實(shí)應(yīng)該成為所有小說(shuō)家的文學(xué)信念。成為我們面對(duì)苦難的一種堅(jiān)定不移的敘事態(tài)度和寫(xiě)作立場(chǎng)。而那些脫離現(xiàn)實(shí)。胡編亂造,迷戀經(jīng)驗(yàn)、小事的寫(xiě)作潮流。或埋頭故紙堆中的為帝王將相的寫(xiě)作,是蒼白而淺薄的,是經(jīng)不起歷史推敲和考驗(yàn)的。
依照我的閱讀口味,慶勝的小說(shuō)還是流于粗糙,許多細(xì)節(jié)其實(shí)是經(jīng)不得推敲的,但整體設(shè)計(jì)和構(gòu)思不錯(cuò),套用的是現(xiàn)流行的最通俗的故事模式。頗有環(huán)環(huán)相扣。步步緊逼的架式。即使撇開(kāi)所有重大的主題,它仍不失為一部好看的小說(shu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