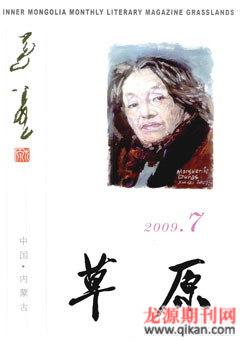八十年代一首詩
我要命地懷念八十年代,因為詩,因為愛,因為青春。
人生最美的年華,與世間最美的藝術,交匯于20歲的那一年。
在20歲的時候,如果你的心里,沒有愛和詩這兩棵幼芽,你的人生已經開始失敗了。
就這層意義來說,我是幸運兒。
一
1982年7月,我在《長春》月刊上,發表了第一首詩《邂逅》。刊物出版時,正是暑假。我在家鄉的小鎮沙洋,找到文化館的圖書室,問管理員:“您這里訂有《長春》月刊嗎?”說實話,我不抱什么希望,撞大運而已。
管理員說:“訂了的。”
“第七期來了沒有?”我的心開始急跳起來。
“昨天剛來。”我的心跳得更快了。
“能不能讓我翻一下?上面發表了我的詩。”這樣說,一則為了順利拿到刊物,二則。虛榮一下。
在管理員走到里間取刊物時,我的腿有點發軟。當刊物交到我的手里時,我的手也在發抖。這種來自肉體的激動,只有幾年后第一次吻一個女孩子時,才再次發生過。
急切地翻開目錄。卻沒有找到我的名字。難道刊物正式通知我的那封信,弄錯了?
一頁頁翻過去,在最后幾頁。總算找到了那首十幾行的詩。編在一個“銀河集”欄目中。我與自己的鉛字姓名第一次相逢。我相信,這個名字不會一直躲在這樣的角落里。它要上目錄、上頭條、上封面……
開學了。坐火車回到北京時。是凌晨四點鐘。兩位同宿舍的同學,在火車站候了一夜,只為了接我。這樣的事情,在今天,完全當得起一個“蠢”字。在八十年代初,卻時常發生在我們同學之間。
一個同學,在拂曉的晨光中,摸出一本從圖書館借來的《長春》月刊,說:“快看你的詩!”為了不讓同學失望,我裝作第一次看見的樣子,驚叫一聲:“哇!”
另一個同學說:“告訴你一個不好的消息。你上學期的哲學課,考試不及格,要補考。”
考辯證唯物主義理論。斯賓諾莎能考得好!
不久收到第一筆稿費:8元人民幣。同宿舍的同學,吵著要去吃北京烤鴨。此后的幾年,我厚著臉皮,一毛不拔。家里太窮了,弟妹又多。我不僅要靠稿費完成學業,還陸續給家里寄回了500多元錢。
詩歌恩惠我,只是開始。
二
1984年3月,我們班上的10名同學,到四川日報實習。時間為一學期。
過了幾天。報社團委,組織我們實習生到著名的都江堰游覽。同學們都上車了。坐在前面。報社團支部書記和三位前來陪我們的報社女孩子,走到車的后面坐下。
看到自己的同學和這些主人沒有打招呼,我很過意不去,便走到后面,坐在三位女生的前一排,和她們聊起來。
旁邊的兩位女孩,和我聊得起勁,以為我是大城市來的。騙我說:“你看,外面種了多少畝韭菜!”那是麥苗正青的時候。我甚至可以用麥稈做笛子呢!
坐在中間的那位。最漂亮,卻一言不發。對我小丑一樣的表演、表現和殷勤,毫無興趣。而我說出的任何一句話,其實,都是說給她聽的。
不久。一位同學過生日。這三位女孩子。也來參加聚會。輪到我出節目時,我拿出1984年3月號的《青年文學》,上面刊登了我七首詩,足足占了近4個頁碼,還配發了作者簡介。
我朗誦了上面的一首詩。然后。刊物就被大家傳閱起來。
不言而喻。我想炫耀的對象。其實就是那個漂亮的川妹子。那個從未和我說過話的人。
過了幾天。下班很久了。看到她辦公室有燈(我們宿舍和她們的辦公室在同一棟樓),門半掩著,便大著膽子,進去和她聊天。
她桌上擺著一本書:《唐宋名家詩詞選》。
我說:“你隨便翻到哪首詩,讀出上句,我一定能背出下句。”
她不信。于是。一首一首讀下去,我不等她念完。就能背出下句。
她還以為,凡是名牌大學學文科的學生。都有這樣的才學呢。直到今天,我也沒有告訴她:我讀中學時,正好有這本書,早已背得滾瓜爛熟。
我告訴她:“千萬人中,一人而已。”
不久。收到了稿費,140元。在八十年代初,這不是一筆小錢。我花70元,買了平生第一套西服,記得是黑色,帶細微白格子的那種。
賽詩之后,壯著膽子。邀請她去郊游。
郊區油菜花開得好燦爛。雨后的土地,松軟、甜蜜。走累了,她想歇一會兒。我馬上將身上的西服脫下來,墊在泥巴地上,完全沒有經過思索,自然毫不猶豫。
她在幾年之后,做了我的老婆,而且,將這一頭銜保持至今。
“現在。讓我逐一清點
我遇見過的那些女孩
屈指算來
只有一個人
還跟在我的身邊(程寶林詩《三八線》)
三
1984年秋,中國作家協會舉行了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會上,官方首次準許了“創作自由”這一石破天驚的口號。
想到惠特曼、艾青、臧克家等詩人,第一本詩集都是自費出版的。我動了這個念頭。
一個念頭,竟然在全國詩壇,引起了強烈反響,產生了劇烈的連鎖效應。
我有一個親戚。我稱“黃叔叔”,在家鄉的一家印刷廠工作。我寫信給他。問他可不可以印刷詩集。他去找廠長商量,決定給我最便宜的價格:3000冊。132頁,照片一幅(照片須用銅版紙印刷),需要1800元。
在1984年底。對于一個每月只有18元生活費補貼的農村大學生來說,這是天文數字。我開始了艱苦卻充滿溫馨的籌款活動。
第一筆捐款。來自我的家鄉,湖北省荊門市煙垢鎮,賬目如下:煙垢區區公所(現為鎮政府)、糧管所、財管所、教育組、供銷社、煙垢中學,各100元;吳集中學:50元。負責到各單位將捐款收齊并寄給我的,是煙垢中學的羅懋勛老師。
一張650元的存款單,被我鎖在箱子里。
我打印了一封信,寄給全國的詩人。信上寫道:“這是新中國第一本在校大學生自費出版的詩集。每本的成本,大約為六毛錢。您是詩歌界的前輩、老師,書出版后,我將寄贈給您,請求指教。書是免費的,但如果您能夠贊助五角錢以下的郵資,減輕作者的經濟壓力。則不勝感謝。”
詩集的宣傳材料和這封要錢的信,都是借系里的滾筒油印機制作的。當時,油印機這類設備。還被當作是政治敏感物品,一般不借用的。
10多天后。大量的信件,雪片一般飛來。寄錢給我的,最多10元、最少2元。
素不相識的寄錢來的讀者中。有安徽望江縣汽車修配廠的一位老工人。
湖南的老詩人弘征、崔合美、鄭玲,都寄了錢來。
我記得,弘征老師寄的是10元。1987年湖南出版的《科學詩刊》,詩人彭國粱在寫我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了這件事。他寫道:“就憑他兩手空空卻耀武揚威地出版了全國第一本大學生個人自費詩集。便可見出他的能耐。他向全國的詩人和詩友寄出了一封言辭懇切的信,請求給一個想出詩集的大學生以五角錢以下的贊助。他知道,收信人要么不理他,要理。寄五角錢就不好意思。”
我是湖北人。在湖北。最傻的人,也傻
不到哪里去,畢竟是“九頭鳥”的故鄉啊!
我還記得,舒婷和流沙河各寄了2元錢。是夾在信封里寄的,并附有親筆簽名的詩集。
很快,一張1000元的存款單。就在宿舍同學中間奪來奪去。大家都想將它揣在懷里,體會一下“有錢”的感覺。
四
詩集編好了,找誰寫序呢?
我想到了被稱為中國詩歌評論家第一人的北京大學教授謝冕。作為“三個崛起”理論的主要論家,遭受官方壓力的謝冕教授,在中國詩壇可謂舉足輕重。
謝教授在北京大學開設“中國現代詩歌名篇欣賞”課程。由于選課的人很多,給外校的旁聽者提供了機會。我在人民大學校門口。搭上332路公共汽車。混入課堂聽課。據我觀察。一百多人的大教室里,坐在后排的大約1/3的聽眾。都并非北京大學的學生。
有一天,下課了,謝教授正在收拾講義。準備離開。我抱著編好的詩稿,走上前去。自我介紹,并請求謝教授幫忙寫一篇序言。
謝教授說:“我最近很忙。這樣吧。稿子我先拿回去看看。兩個星期后給你答復。”
一周以后,下課了,謝教授走到我的座位旁,拿出一個舊的牛皮紙信封。說:“序已經寫好了,我留了底,這是我老伴抄下的。你看能不能用。”
三千字的長序,標題《雨季已經來臨》。字體秀麗。一筆一劃。
謝教授是這樣寫的:
“程寶林詩作的可貴之處,在于他以現代人的心胸,擁抱著并融化了綿延數千年的民族心理文化傳統的因襲。他能以青春的流行色調、當代生活的節奏感來再現這片古老土地以及吾土吾民的淳厚鄉風民俗。并把二者加以融會貫通,體現出獨創性。
程寶林以經過精心錘煉加工的提高了的口語化語言,以流動的活潑的節奏。平易地展現了當代大學生的生活和情感。他以同代人的身份,表現同代人的心靈世界。無疑是最引人注目的成就。”這篇序言,發表在1985年4月8日安徽《詩歌報》的頭版頭條。
兩年后的1987年。我已經畢業分配到四川日報工作。謝冕教授和夫人,到拉薩參加“雪域之光”詩會后,途經成都返京,住在我家附近的一個賓館。我提著一瓶四川名酒,去看望他們。謝教授寫序之后。我們便再無任何聯系,替我抄寫序言的師母。更是從未謀面。三人正在交談。忽然,服務員來敲門,說樓下大堂里,有北京來的重要電話,找謝冕夫婦接聽。當時,賓館房間里。還沒有普及電話。
我們交談的客房桌上,放著一個信封。一些鈔票露出來,大約有300元左右。大概是兩位老師的旅費。我看得出來,師母臨出門時,略為猶豫了一下,不知道。將這個初次見面的年輕人單獨留在這個桌上放著錢的房間里,是否妥當。
謝教授也看出了師母的猶豫。說:“走吧。有寶林在屋里。放心!”
給我的詩集寫跋的,是詩人李小雨。當時,我已經在《詩刊》發表了好幾組詩,都是她的責任編輯。
熱情、誠懇、鼓勵和希望,洋溢在她的每一句話里。
跋的末尾。記下了寫作日期:1984年12月25日深夜于北京。
圣誕節的半夜,這個快要臨產的詩歌編輯,給一個大學生的詩集寫跋。最令我感動的是,不久,她竟然挺著大肚子,換乘幾路公共汽車(80年代初,北京公共汽車的擁擠程度,居全國之冠),在嚴寒路滑的北京,從虎坊橋的《詩刊》編輯部。找到西郊白石橋路的人民大學,將跋文送到了我的宿舍。不巧,我尚未回宿舍,同學替我收下了這篇跋。
在奉行利益交換原則的今天,這樣的事情,完全不可思議。
但是,在八十年代初的中國詩壇上,這樣的事情卻很多、很多。
五
1984年的寒假來臨了。我的親戚,囑我給印刷廠的廠長送點禮。我推著自行車,車頭上掛著兩只老母雞。后架上。馱著一袋糯米。路上泥濘,無法騎行,我必須隨時拿一根細棍子,清除車輪上的泥巴。才能將自行車推走。30里的土路,從鄉下到小鎮。我走了幾乎一整天。
當天晚上。在“黃叔叔”的陪同下。我參觀了這家印刷廠。它的名字叫“荊門市裝潢彩印廠”。一切就緒,1000元預付款已經交給工廠,當晚開機。
在這位叔叔家吃過晚飯,我們來到位于郊外的印刷廠。當印刷機開始飛速旋轉時。我走到廠外去散步。那是江漢平原的腹心地帶,土地肥沃。這時,大霧升騰起來。在彌天的大霧里,行走著一個正等待自己的詩集印刷完畢的22歲青年人。我突然覺得,青春是這樣美好,還不曾體驗過的愛情和激情。是這樣美好。
“我對世界懷著難以抑制的情欲。”
這樣的詩句就涌上了腦海。
20多天后,開學了,我帶著200本書,坐公共汽車到了武漢。
找到分別在中南財經大學和華中師范大學讀書的同學王長城、范軍。他們買了紅紙。寫了廣告,抱著書,來到武昌火車站的一盞太陽燈下。開始賣書。
我很驕傲:前者,現在是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的教授、系主任;后者,是華中師師范大學教授、出版社社長,雖然我什么頭銜都沒有。
第一本書是一個旅客買走的。定價九角。他給了一元,叫我們不要找零。后面的故事,我已寫在散文《旅途賣書記》中,就不重復了。
我回到大學后,20包書也已托運到了北京海淀區。我到大學的食堂里,找到負責人,說明原委。食堂負責人慷慨地借給了我一輛平板大三輪。我從未騎過這種車,居然騎得非常熟練。在同學的幫助下,順利將書運回宿舍。
那一天中午,全班同學一起出動,在學校食堂前面。出售詩集《雨季來臨》。
同學們常在校刊上看到我的詩,一看廣告,馬上將食堂前面的馬路圍得水泄不通。
限額出售300冊。300冊在40分鐘內賣光。
至少有一半的書款,是學校的菜票,要拿到后勤處,兌換成現金。
前不久。在美國馬里蘭大學任副教授的一位人民大學校友。路過舊金山。分別20多年,異國相逢,吃飯時,他突然拿出一本《雨季來臨》。書已經變黃,封面也破損了。他說:“當年買書時人太多,沒能找你簽名。現在,請你補簽一個。”這位校友叫鐘夢白。
六
《詩經》里說:“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瑤。”
我沒有瓊瑤可作回報,只有一顆崇敬、感恩、祝福的心。
我不是象牙塔里自我陶醉的詩人。我是大地的詩人。是民間的詩人,是人的詩人。
高揚人的旗幟。是我全部文字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