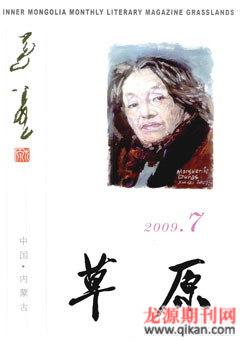蘭和昌的故事
楊維永
蘭和昌是同村人,同年同月同日不同時生,同班同學,他倆從小青梅竹馬,兩小無猜。
那年國家的政策未變,職工退休子女接班,蘭和昌都是初中沒畢業接的班,倆人都同時進了國營糧庫當了國家正式職工,蘭當了名劃碼員,昌當了名倉庫保管員。那陣子吃商品糧當國家職工吃香。蘭和昌當上糧庫職工后煞是風光了一陣子。村民們無不交口稱贊說蘭和昌真是天生的一對,地設的一雙,雙雙能吃上皇糧當上國家工人,也真是村上幾十年來罕見的一件大喜事。逢著夏征秋購的時間了,和蘭好的女伴家和與昌和睦的男友戶送糧庫的糧食。總要受到蘭和昌的親熱關照。交糧順利能驗高級取錢便當,這樣一來就讓蘭和昌兩家的親屬們在村上的口碑也更加響亮了。
夏秋收糧旺季過去后,蘭和昌倆人在茶余飯后的閑暇時間里,常常肩并肩到糧庫那條方土路和泥溝水渠邊,眺望田野的莊稼和垂下的柳絲。心曠神怡地欣賞著春花和秋實,卿卿我我互訴衷腸,好不自由自在。瀟灑浪漫。在那漫長的歲月里,村上曾有媒人到蘭和昌家牽線搭橋提說蘭和昌的終身大事,雙方二老也很滿意,只是蘭和昌還沒來得及多想此事,僅在心里埋下了情愛的種子。仍處在孕育萌芽期間。
斌是城鎮戶口,父親是糧庫會計。斌不是接班。是高中畢業后糧食系統內部招工安排進糧庫工作的,晚蘭和昌一年后進糧庫的。當了名過磅員。
這年夏征季節,蘭和斌被分在了一個糧倉收購組,蘭雖是第二年參加夏征,但由于初中沒畢業,學識較淺,加上算盤學得不怎么熟練。劃的碼單和初算的結果間或出現差錯。斌曾跟著父親學過算盤,算盤打得嫻熟。再加上自己高中畢業,每遇蘭劃碼初算有差錯時,主動借著過磅空閑時幫助蘭把錯誤糾正過來。就這樣在一來二去的糾正錯誤中。蘭對斌逐漸產生了愛慕之情。
夏征結束后的一個傍晚。天剛落下一場雷陣雨,空氣的悶熱被雨濕所驅逐,代之而來的是雨后晚霞的炫彩和大地的一片新綠。新出土的玉米、黃豆、芝麻等秋作物像干渴的兒童喝下一杯解熱的清茶一樣。歡蹦亂跳“嗖嗖”躥升著。昌特意換了身新滌確良短袖白衫。在糧庫食堂吃過晚飯后特意約邀著蘭來到糧庫院外的水渠邊。倘佯在晚霞的余暉中。蘭卻沒有打扮,仍穿著上班時的那身勞動布褲子和淺紅色滌確良短袖上衣。倆人邊走邊攀談著。
昌開門見山地說:“蘭,咱倆從小就是好友,村上的媒人也曾給咱二老提過咱倆的婚事,現今咱倆也來糧庫上班一二年了,我看不如今年夏征過后,咱倆就正正經經領個結婚證。再等一年半載。俺家里寬裕了咱就把婚結了算了。結婚后咱倆還能跟糧庫要兩間房子。往后就不用住那集體宿舍了。你看咋樣?”
這時的蘭有些為難。頭歪在左肩上,耷拉得像秋天快成熟的谷穗。右手摳著左手的指甲,雙腳在地上左右搖擺著。直把濕潤的地面踩出了兩個腳窩窩,好像一面凹陷的哈哈鏡,把蘭的心透視了出來。
蘭的心里也確實矛盾。她和昌在童年的拾柴生活中,在小學初中的校園生活中,在糧庫這二年的頻繁交往中的確建立起了深厚的情意。若真是舍昌跟斌,也確實難為情。可她又深深知曉,昌的文化和她一樣實在有些淺顯,如果還在農村的話,和昌完婚,建立家庭。男耕女織還算是很美滿幸福的婚姻。然而這是糧庫。如今成了糧庫的工人,要和昌成婚,昌以后的前途和她新家庭以及子女的前途都將是暗淡無光渺無希望的。那么斌呢,就不一樣了,斌的父親是糧庫會計,現在斌已是預備黨員了。蘭曾聽人說斌黨員轉正后就可以接任糧庫庫長的職務了。斌若當上庫長后再努力干上幾年,晉升到糧食所所長也是有可能的,倘若那樣的話,和斌建立個家庭,那以后的生活肯定是充滿陽光的。蘭思索到這里后,就直起了頭,分開了兩手,站穩了腳跟,佯裝猶猶豫豫實為心意已定,她對昌說:“昌哥。我……我心里這陣子老在想著斌幫我糾正劃碼初算時出現錯誤的事,再說,斌有文化。以后他……他會……咱……咱倆這事就先擱擱吧……”
昌不禁打了個愣怔,遲疑在那里了。這突如其來的變故委實讓昌難以接受。可這是事實,昌也不得不面對這嚴酷的現實明智起來,他深深地知道,強扭的瓜不甜,而且也挽回不過來了,遲疑好大好大一陣子才緩過神來。緩過神后。昌結結巴巴地哽咽著說:“蘭……蘭啊,既……既然你……你心里在惦掛著斌,那……那咱倆這事就散伙算了,免……免得你……你以后再……再后悔……”說罷,昌扭過臉,十分認真的又審視了一下蘭。此時他覺得眼前的蘭和過去的蘭判若兩人。昌情不自禁地伸出了自己的手對蘭說:“來,蘭。咱倆最后再拉一次手,那……那我就祝你和斌婚后幸福了。”昌拉罷蘭的手,轉臉朝回糧庫的方向飛一般跑去。蘭佇立那里良久后才回了糧庫。
痛定思痛后,昌悟出了在蘭眼里他弱斌強的癥結在知識上,于是他坐立起來。擦干了眼淚。直恨得他用力把自己的嘴唇咬出了血,像《紅燈記》里的李奶奶給李鐵梅說的話那樣自言自語著,生活是不同情眼淚的,眼淚救不活你爹,要擦干了眼淚埋藏了尸體還上戰場。
挺立起來的昌把悲憤的力量轉嫁到了書本上,他利用夜晚和節假日的閑暇時間,到糧庫西邊的鎮中學補習班學習起了功課。
功夫不負有心人,兩年后。省糧食學校招生,昌以優異的成績考取到省糧校。畢業后留校任了教。成了家。
二十幾年間,昌曾因家中紅、白喜事。或過年過節時回至家中,但那都是匆匆而回,然后就又匆匆而歸了,從沒打聽過蘭的情況。家人也自知昌仍在生蘭的氣,更詳知蘭的不幸遭遇,卻仍沒有啟齒的理由。終也沒和昌提過蘭后來的情況。
這年秋天,昌的父親病逝,昌特意從省城回來守孝父親,在村口無意遭遇了正在村路東邊收割黃豆的蘭。
此時的蘭瘦骨嶙峋。弱不禁風,頭戴一頂灰黑灰黑爛了半邊的草帽,草帽上的帽帶在下巴額上綁著。整個臉蠟黃消瘦。眼窩凹陷。下巴尖小,牙齒脫落大半,剩下的幾顆稀牙黑黃黑黃的爬滿了牙垢。整個臉型和身子像縮減了三分之二,骨瘦如柴。
蘭看清昌后。無力地站在路邊的墑溝旁。仰著脖子對著昌那被太陽親吻得滿面紅光的大胖臉蛋。怯怯地微弱地囁嚅了一聲說:“昌,昌哥呀。你,你回來了……”
這一聲昌哥,使昌聽清楚了,他循聲轉過臉,朝路邊的墑溝望去,猛然和蘭的眸子相撞了,并且撞擊出了共鳴的火花。昌從蘭那殘留的神韻里,慢慢地找出了當年蘭那眼里還殘留的一絲微妙的情愫。
昌繼續凝神望著蘭,頗有感觸地說:“二十幾年不見,你怎么衰老成這樣了,如今的你和那時糧庫的你相比,真是天上地下判若兩樣了。我……我要不仔細看你。還……還真認不出是你呢?”
蘭低下頭沉默了許久許久。然后簡明地講述了這二十幾年的情況。
昌走后的第二年。蘭向斌提出婚事,斌說:“蘭哪,我幫你改正劃碼初算錯誤,是出于工作和同情。可……可沒別的意思。實話告訴你吧,我……我并不愛你。”
于是蘭就沒有再愛過任何人,一直單身過著。
后來,國家又實行新的政策。國營糧食系統的單位轉制為企業,實行自負盈虧,蘭就下了崗,回家務了農。在敘述中,蘭流露出那時沒能和昌成婚的遺憾時,昌曾幾次想直接告訴蘭心里話。但看著蘭的身體已經殘損衰敗到如此地步,再念起當年自己讓黃豆茬扎著腳。蘭背著他回家的情意。昌怎么也不忍心使蘭的心靈受到新的創傷了。
于是昌就語重心長在心里自語說:“蘭哪,假若我要在那時死纏硬磨著真的和你結婚的話,那……那你會后悔一輩子的。現在很可能你會埋怨我說。是……是我耽誤了你和斌的婚姻,如果沒有我的追纏,你會和斌結婚。并且想象著斌和你婚后的日子肯定會幸福美滿,甜蜜無邊的。然而,再說,要……要真不是你舍棄我的話。我……我或許不去補習學習功課,也考不上糧校。倘若那樣的話。那……那可能咱倆一齊都下了崗。都在這田間勞作哩,啊!蘭,你……你說是吧?”
自語后。昌佯裝愧疚似地說:“蘭哪,都怨我不好。是我棄你而去省城上的糧校。那時我要不去上糧校,咱倆要結婚,那現在咱倆的日子過得才是數一數二的幸福美滿哩,嗯,蘭,你說是吧?”
蘭聽罷昌這感人肺腑的知己話。激動得雙眼的淚水像斷了線的珍珠似的嘀嗒嘀嗒不住勁地往下淌。嘴里喃喃著說:“是的,是的呀,昌哥。你可算說到我心坎里了。你不知道吧,昌哥,我這……這二十幾年都在惦掛著你呢……”說罷一頭扎進了昌的懷抱里。然后陡然轉悲為喜,仰天大笑起來,笑著絮叨著:“咱倆過的日子才美滿,咱……倆……過……的……日……子……才……美……滿……哩……”昌和蘭都一起哭了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