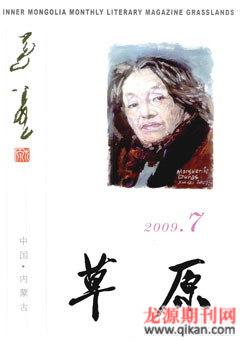佛爺
遲鳳君
佛爺做起了他們家族歷史以來最大的官——鄉護林員。
選這個角色的時候,鄉領導很費了一番腦子。這之前,鄉里曾有過幾任護林員,可是護來護去。林木護少了,草場護光了,鄉長氣得罵林業助理:你除了能摟女人睡覺還能干點別的不?林業助理知道自己失職,干張嘴答不上話來。
也是。這個角色不好找,特別是能夠負起責任的更不好找。真正精明強干的人,不是外出打工。就是做起生意來了,屈屈一個月幾百元錢,而且又是得罪人的差事哪有人愿意干呢?最后,林業助理便挖空心思地想起了我們村的佛爺。
佛爺不是真正的佛爺,他的小名叫石頭。
石頭有弟兄五個,他是老二。這弟兄五個一順兒常年剃著光頭,原因除了當時很難找到一個正式理發人外,還有其他方面的考慮,比如剃禿頭是不用任何花費的,一把剃頭刀足矣。
這弟兄五個其余四人即使是光頭也并不顯得十分難看,惟獨這石頭,由于小時候長過很嚴重的頭瘡。禿頭上明明白白地暴出了斑斑點點,像受過戒的和尚一樣。所以,人們就送他一個外號叫佛爺。至于為什么叫佛爺而不叫和尚。給他起綽號的人是站在哪個基點上考慮的,我就不得而知了。
開始的時候,佛爺似乎很惱火,據說他曾對他爹提出過留起頭發的強烈要求,他爹狠狠地瞪了他一眼:“留起來。憑啥你留起來,都禿著!”佛爺摸了一下禿頭:“他們叫我佛爺。”
“佛爺?佛爺不好嗎?”他爹用吼牛的聲音吼著他:“是把你燒得!你留起來,留啥?平頭?分頭?那都是干部留的!不剃禿頭就把腦袋割下來吧!”
佛爺再講不出什么道理來。暗暗地卻憋起一股怨怒。當別人再次叫他佛爺的時候,他就進行了堅決的反擊。他說:“誰再叫我佛爺我就罵娘了!”
“啊哈!你罵誰的娘??正在呼喊以及曾經叫過“佛爺”的家伙們立刻揮著拳頭圍攏上來。佛爺只好斂言不語,瞅準一個空子,忙忙地鉆出重圍。如喪家之犬逃之夭夭。自此,佛爺二字叫得更響,久而久之,佛爺也就悉聽尊便。
對于佛爺的情況,我是比較熟悉的,因為我曾搶過他的奶吃。
什么叫搶奶?就是我媽媽的奶水不夠我吃,而他當時也正在哺乳期,我吃了他媽媽的奶水,也就是搶了他的奶。那不是一次兩次,是一天三次,整整一年。因而,后來佛爺發育得很不好。我想與我的搶奶肯定有著必然的關系。但是,也正因為這個原因,爸爸媽媽不止一次教導我,永遠不要忘了這一家人的恩情。當然。我至今不敢忘。就在當時,我們家對他們也做到了力所能及的接濟,并不是讓我白白地搶了奶吃。
他們家實在是太窮了,特別是在佛爺身上有著最明顯的體現。一鍋粥,要別人盛完他才盛;一碗菜,別人吃剩下才輪到他。過年的時候。他的爹媽當然也總是擠兌出幾塊錢扯幾尺布給孩子們做件新衣。先給大的裁,再給小的裁,輪到他的時候,不是缺個袖子,就是缺一截褲腿。只好接一接吧,顏色又難以搭配上。在這些方面,佛爺似乎并不挑剔,穿出來總是一臉得意的樣子。
佛爺的命運也曾有過一次輝煌。那是由于他媽媽的病逝。
他媽死于肺病,死前瘦得如一把干柴棒。不但不能走路,甚至坐也坐不住。想不到她咽氣幾個小時之后卻忽然坐了起來。此時正值午夜,守靈的幾個男人正在打牌,忽聽有異樣的喘息聲。隨之便有人大喊:“詐尸啦!”
幾個男人驚慌失措,匆忙跳窗。他們剛剛跑到院子中間,就聽屋內喊:“沒事了,沒事了!”回頭看時。見佛爺正站在窗前喊:“沒事了!”幾個男人抖抖索索地返到窗前,果然見死者躺下了。這才收心定氣地回來。
原來,佛爺一直在看人們打牌,聽見喊聲。回過頭來見媽媽已經坐了起來,他就上去將她放倒。事后,人們說如果不是佛爺上去將死者摁倒,死者就會站起來,就會碰物物傷,觸人人亡。但這件事除了幾個守靈者和佛爺再無證據可尋,是否真有此事發生?曾有人提出質疑。不過。佛爺的名聲卻由此傳開。
自此,街坊四鄰,前村后店,誰家死了人必請佛爺前去坐鎮靈棚。事畢,再貧困的人家也免不了送他一只雞或幾斤肉。佛爺的穿著也起了變化,時常見他穿著很像樣子的衣服往來于街上,只是頭依然禿著。應該說他完全可以蓄起頭發了,但有好心人告訴過佛爺說:“你的運氣就在你的頭上,萬萬不可破了運。”佛爺也好像感到這顆頭禿得可貴。于是,也就不再想留頭發的事情了。
佛爺時常到我家里來,特別是在我放學回來,他只要無事干必來不可。開始他只和我玩耍,后來就讓我教他識字。我由于搶過他的奶。對他的要求也就沒有拒絕。因而,我讀完小學四年級的時候,他差不多也有二年級的識字水平了。
暑假的時候。我們倆就相約著去挖野菜。或是去割草,寒假的時候就一起去拾柴。他總是將最好的野菜讓我挖,最好的草讓我割。最好的柴讓我拾。如果這一次我的收獲小,他就定要將他的分給我一些,并且替我擔著,一直送我到家。為了表示對他的尊重,我從不叫他佛爺,只叫他石頭。他也似乎明白我的意思,在我面前從來都是十分的馴順,而且經常露著微笑。
“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時候。村里也有了紅衛兵組織,他們在公社“革命戰斗隊”的直接領導下,開始尋找“封、資、修”的突破口。找來找去,就把佛爺推上了批判的臺上。這時佛爺才15歲。佛爺說:“我沒罪!”批判他的人說“你沒罪。你為什么叫佛爺?這名字本身就是和無產階級水火不相容的!”
佛爺說:“那都是大伙叫的,我還罵過,誰再叫我罵他們的媽呢!”
于是又有人質問他:“那么你為別人守靈是事實吧?說你媽詐尸是事實吧?死了的人怎么就能再坐起來呢?這不是宣揚封建迷信是什么?”
佛爺只好低頭認罪。連續兩天兩夜,佛爺在輪番批斗中挨了兩鞭子。小臉被批得蠟黃。后來,批判者似乎覺得實在也沒有什么可以再批的東西了。就說佛爺已經被批倒批臭了。佛爺身上的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的東西已經被批得體無完膚了,就放他回來。佛爺回來后生了一場病,媽媽讓我去看看他,并給他帶去兩個雞蛋。走在路上我想佛爺見到我一定要痛哭一場的。誰知他見到我竟然笑了起來。
第二年深秋。天氣一天比一天冷起來的時候,有一天,佛爺和我,還有佛爺的爹爹,我們坐在一架牛車上。我們去到幾十里外的煤礦去拉煤。這煤是給我們家拉的。
我們裝好煤往回返的時候,太陽就已經滾到山的后面去了。佛爺的爹爹在前面趕著老牛。我和佛爺坐在車子后面。車子吱吱呀呀地向前移動著,路兩旁的景物越來越模糊。那天晚上沒有月亮。車子行至中途的樹林旁,佛爺的爹爹就讓牛停住,對我倆說,牛太累了,歇一歇,讓牛吃點草再走。我看著黑黝黝的樹林。聽著樹林深處不時傳出一兩聲不知什么鳥的怪叫,心中有些害怕。我悄聲問佛爺:“你怕鬼嗎?”佛爺說:“鬼都是人鬧的。我守靈看了那么多死人,也沒有看見鬼。”
我問佛爺:“你媽死了又坐起來是真的嗎?”
他說:“真的。我那個時候看見我媽那
么躺著好像不舒服,我就把她扶起來,把她身下的褥子鋪展平,他們就喊了起來。”
我長長地舒了一口氣。也不知佛爺說的是真是假,總之,覺得膽子大了一些,又想果真有鬼,有佛爺,還有他爹,總是能抵擋得住的。牛還在吃草。佛爺他爹正在抽煙,煙袋鍋子里不時進出幾顆火星,像流星一樣。一下子撲到冷風里就不見了。我漸漸地睡著了。
我們的牛車又爬過了一道溝的時候,我被顛醒了。我不知道車子是什么時候又走起來的,睜開眼睛的時候發現身上多了些東西,原來是佛爺把他穿在外面的棉襖蓋在了我的身上。他緊貼著我,抱著膀子瑟縮著。為此。我一陣子感動。我想起他穿的鞋子已經破了,我有一雙雖然穿過但還沒有穿舊的膠鞋,我一定要送給他。
回來后,我便拿出那雙鞋來,可是他說什么也不要。我說你要是真不要我就不和你好了。他看著我的態度異常堅決,才勉強接過鞋,咧咧嘴,說:“那就等我有錢再還你。”
后來我到城里工作,由于父母相繼辭世,故鄉也就回得少了,再后來十幾年也沒有回去一次。但是,我卻不斷地打探著故鄉人的消息,特別是對于佛爺,每次我遇到故鄉人首先問起的就是他。有一次聽說他成親了,妻子比他小五歲,長得好。人也勤快,雖說是離婚的,卻沒有生過孩子。到他家沒有給他帶來任何負擔。我很為他高興。可是,不久又傳來消息說,那女子是個騙子。騙了佛爺一萬多元錢跑了,報告了派出所,也沒有結果。我聽了又為他慨嘆一陣子,這個佛爺。怎么就沒有好運呢!
又過了幾年。佛爺在我的情感中也漸漸淡化得幾近于可有可無的時候。他突然出現在了我的面前。他說他承包了土地,日子已經不愁了,說著,臉上洋溢著喜色。我沒好意思問他被騙錢的事情。但談話中知道他還是獨自一人。
說實在的。他的到來并沒有給我帶來愉快。他不來。我或許有時還想起他。他這一來,我就真的知道自己的情感和他的確是已經很遠了。他說話的時候還總是不時地帶出“操他媽的!”并且,從他的神態來看。恐怕也不單單是為了來看看我,一定是有什么事要我幫著辦才來的。近些年來。農村的土地糾紛和林木糾紛都不時地出現,鄉鄰之間有時也弄得紅頭漲臉,他們各說各的理,就是法院也難以斷得清楚。盡管我知道佛爺還不至于與誰有糾纏不清的糾紛,但也真的說不清,至少會有些什么麻煩,不然,他怎么會突然地就來了呢?
盡管如此,飯總還是要請他吃的,誰讓我小時候搶人家的奶吃呢!我要請他去飯店,他執意不從,我只好帶他回家,親手炒了幾個菜。并拿出一瓶二鍋頭酒來。
他說他不喝酒,我說那你就吃飯。總之,這頓飯吃得很沉悶。我們談上幾句就再也找不到共同的話題,是啊,我們明顯地不是同路人了。我又沒話找話地問了他一些家鄉的人和事。然后就十分擔憂且有些恐懼地問他。是不是找我有什么事?他仍然說沒有,說只是來看看我,并反復地說他的日子好過了,鄉親們的日子也都不愁了,說完就用極其專注的目光看了看我,好像再也看不見我似的。
我淡淡地笑了笑,說:“我很好。”意思是你也大可不必來看我的。
吃完了飯,我就希望他快點離去,我問他有住的地方沒有?他停了一下說:“車票都已經買好了,晚間的車。”我這才有些如釋重負,話也又多了些。我說你要不忙就在這呆一天,去公園玩一玩,看看老虎。還有猴子,商場的價格也都不高。他說不去了,老虎猴子在電視上也常看。商場也不去,農村現在啥也不缺,去年還去過北京。公園也都看過了。但是。他還是不走。那么。我們還說些什么呢?我忽然看見了他眼眶上的那個疤,就指著說:“那還是我打的吧?”
他摸了一下,笑了笑說,你還記得,其實你也不是故意的。他的話讓我的心又動了一下,就又說,小時候拾柴或是割草。你總是把你的分給我一些。還替我擔著。他又笑了笑。訥訥地沒說什么。
我看了看表,覺得他應該走了。就說:“要么我送你去車站吧。”他停了停。很是遲緩地站起來,問我什么時候回去,我說我很忙,說不準。他好像想說什么,但又沒有說出來。
我們下了樓。來到街上。他說:“你回去吧,我打個車過去就行了。車站挺遠的。”
我心想,我正不愿意去車站呢,就說:“那你走好,有時間再來。”他依然笑了笑。
車來了。車門打開了。他一腳踏上車踏板。又返過身來。我催促著說上吧上吧。只見他從懷里拿出一個信封,遞給我,說:“你回去看。我的字都是你教給我寫的,你別笑話我。”我不明白他這是什么意思,但還是接了過來。車門一響。車子箭一般駛入了蒼茫的暮色里。
我一邊上樓一邊想。他寫的什么?是他寫的文章?不可能。是上訴信,似乎也不是。我覺得有些好笑,心想這個佛爺,還會搞什么名堂!
我進屋后把信封打開。里面僅有一張四折的紙,中間夾著一百元錢。信紙上寫著雖然工整但卻是很難看的兩行字:我欠你一雙膠鞋,我一輩子都感激你,我說過要還你的,這一百塊錢夠吧?
這個佛爺!我的手顫抖了,眼睛也有些濕。想起剛才我的一些想法,就覺得自己很卑鄙,又覺得有點對不住他,心想再見到他時一定要好好對待他。
不久就聽說他當上了鄉里護林員,我暗暗為他祝福,知道這護林員的差事應該是很不錯的。誰知沒有幾天,又得到了一個我根本想不到的消息:佛爺被拘留了。原來是他在護林中,竟然把一個人給打死了。據說,那一天他正在山上轉,幾個偷樹的人讓他碰上了。偷樹的人并不怕他,雙方在爭執中交了手。佛爺手中拿著一根鐵棍,一頭很鋒利,當對方向他大打出手,并揚言要把他廢了的那一瞬間,佛爺的鐵棍竟在對方沒有防備的情況下捅人了對方的胸膛。
鄉長又把林業助理大罵一頓。說:“你選誰不好,偏偏選這么個人!現在好,弄出人命來了!”
林業助理說:“這是誰也想不到的。自從佛爺護了林,偷樹的人少多了,誰想就出了人命呢!”
鄉長想了想也覺得自己對林業助理發火不應該,佛爺的確是很負責任的,如果不負責任也不能出這種事。于是找到公安機關去保釋。公安局的人說:“這是人命關天的事,誰敢輕易放人啊。”
最后,佛爺被判了無期徒刑。
在佛爺被移送另一個地方去服刑的那一天,我去看了他。
他對我的看望并沒顯得激動。但這一次沒有笑,也沒有哭。
我說:“你好好改造。還有減刑的希望的。”
他看了看我,又摸了一下他那光禿的頭。什么話也沒說。
我隔著鐵欄,模糊地看見佛爺腳上穿著的正是我給他的那雙膠鞋。很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