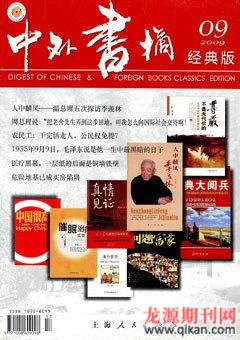家之脈
2009-08-31 07:45:26陳忠實
中外書摘
2009年9期
關鍵詞:寫字
陳忠實
女兒和女婿在墻壁上貼著幾張識字圖畫,不滿三歲的小外孫按圖索文,給我表演:白菜、茄子、汽車、火車、解放軍、農民……
1950年春節過后的一天晚上,在那盞祖傳的清油燈下,父親把一支毛筆和一沓黃色仿紙交到我手里:“你明日早起去上學。”我拔掉竹筒筆帽兒,是一撮黑里透黃的動物毛做成的筆頭。父親又說:“你跟你哥伙用一只硯臺。”
我的三個孩子的上學日,是我們家的慶典日。在我看來,孩子走進學校第一步,認識的第一個字,用鉛筆寫成的漢字第一畫,才是孩子生命中光明的開啟。他們從這一刻開始告別黑暗,走向智慧人類的途程。
我們家木樓上有一只破舊的大木箱,亂扔著一堆書。我看著那些發黃的紙和一行行栗子大的字問父親:“是你讀過的書嗎?”父親說是他讀過的,隨之加重語氣解釋說:“那是你爺爺用毛筆抄寫的。”我大為驚訝,原以為是石印的,毛筆字怎么會寫到和我的課本上的字一樣規矩呢?父親說:“你爺爺是先生,當先生先得寫好字,字是人的門臉。”在我出生之前已謝世的爺爺會寫一手好字,我最初的崇拜產生了。
父親的毛筆字顯然比不得爺爺,然而父親會寫字。大年三十的后晌。村人夾著一卷紅紙走進院來,父親磨墨、裁紙,為鄉親寫好一幅幅新春對聯,攤在明廳里的地上晾干。我瞅著那些大字不識一個的村人圍觀父親舞筆弄墨的情景,隱隱感到了一種難以言說的自豪。
多年以后,我從城市躲回祖居的老屋,在準備和寫作《白鹿原》的六年時間里,每到春節前一天后晌,為村人繼續寫迎春對聯。
登錄APP查看全文
猜你喜歡
學生天地(2020年27期)2020-06-09 03:09:46
閱讀(低年級)(2019年8期)2019-10-10 12:11:07
快樂語文(2019年12期)2019-06-12 08:41:54
中國生殖健康(2019年11期)2019-01-07 01:27:50
創新作文(小學版)(2018年19期)2018-11-30 01:56:14
七彩語文·寫字與書法(2018年10期)2018-11-19 08:32:08
七彩語文·寫字與書法(2017年8期)2017-09-06 00:52:54
小學生優秀作文(低年級)(2017年5期)2017-05-17 05:52:54
作文大王·低年級(2017年4期)2017-04-10 20:38:14
少年文藝·開心閱讀作文(2015年9期)2015-09-28 07:43: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