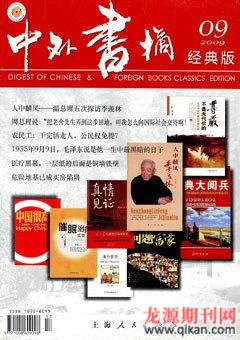中醫的悲哀
2009-08-31 07:45:26韓起
中外書摘
2009年9期
關鍵詞:中藥
韓 起
也許是家教的影響,我越來越感受到中醫深沉的悲哀。
父親大半生行走杏林,所以我自幼年便與中醫結下不解之緣。母親生育六胎,僅存活最后兩胎,就是姐姐和我。生我時,父親已過不惑之年。母親常對鄰人說:俺這孩子,可是十八畝地一棵苗。
一棵獨苗,自然嬌貴。父親盼我成才,繼承家學。3歲就教我背誦《藥性賦》、《湯頭歌訣》、《非訣》等。我不識字,背書如老太婆念經,并不知道其中意思,因此實在沒有興趣。也許是物極必反,后來上學了,識字了,我堅決不學中醫。但父親還是給我講一些他號脈、治病、制藥材的經驗。父親15歲拜師學醫,青年時在河南鄭州開過八九年藥鋪,自己賣藥,又充坐堂大夫,留下不小的名聲。
父親是一個非常倔犟的人,人送外號:“杠子頭”。他認定的事情,誰都扳不過來。他行醫仔細,開藥鋪、制藥材,尤其認真。比如熟地,他要求把生地九蒸九曬——絕對照此辦理,伙計想少蒸一次都不行。他說:藥材不用功,神仙難治病。在炮制藥材的問題上,他常常訓斥伙計,所以伙計們不喜歡他。背后罵他“老牛筋”。他開的處方也非常講究,體現了他的“老牛筋”性情:凡熟地,他一定寫的是“九熟地”;貝母,一定寫作“川貝母”;當歸,他一定寫明是“歸頭”、“歸身”或“歸尾”——他認為當歸頭藥效趨于補血,當歸身偏向活血,當歸尾則趨于破血,這是絕對混淆不得的。就是現在鬧得沸沸揚揚的中藥木通,父親繼承師傅衣缽,一生都拒絕用關木通;他一定用南方產的木通——他叫南木通。……
登錄APP查看全文
猜你喜歡
中老年保健(2021年5期)2021-12-02 15:48:21
中老年保健(2021年4期)2021-12-01 11:19:40
中老年保健(2021年4期)2021-08-22 07:08:32
中國現代中藥(2020年10期)2020-12-16 08:53:18
金橋(2020年7期)2020-08-13 03:07:00
基層中醫藥(2020年12期)2020-07-22 06:34:38
中國現代中藥(2020年4期)2020-06-10 09:56:34
基層中醫藥(2018年6期)2018-08-29 01:20:20
長春中醫藥大學學報(2017年1期)2017-04-16 05:56:49
肝博士(2015年2期)2015-02-27 10:4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