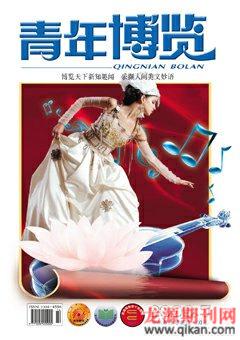閱讀死亡
徐蘊蕓
這個全國知名的醫院傳說有三件寶物,其中之一是積累了近百年的病歷,病歷中不乏一些在中國歷史上響當當的名字,但那當然不是我注意的對象。
有段日子為了寫論文,我每周都去病案庫檢索。病案庫在地下三層,明亮而陰涼。架子帶滑軌方便移動以節約空間,乍一看和圖書館沒什么兩樣。黃色牛皮紙包裹的病歷厚厚薄薄地矗立著,有時會割傷我的手指,里頭是發黃變脆的紙張,上有褪色的墨水字,記錄著一個人的姓名、出生年月、家庭住址、可能已經無效的電話號碼、為什么來到這里、經歷了怎樣的痛楚、帶著什么結果離開,歡欣還是悲傷……
由于我當時的課題,涉及一種起病較隱匿的婦科腫瘤。幾乎所有的患者都需要接受創傷很大的手術,身體的一部分隨之離去,然后就是無休無止入院治療出院修養然后等待下次入院,生命變成無趣的重復,間雜著痛苦的化療,偶爾有意外的嚴重副反應。出院記錄里總是歡天喜地地寫著:手術順利,患者一般情況好,無明顯不適,傷口愈合滿意。或是:化療過程順利,患者出院,定期隨診。我忍不住會想,什么叫順利,如何叫滿意?一個永久殘缺的人如何會好?化療時撕心裂肺的嘔吐聲猶在耳際,紅色筆標明的輸血記錄分外刺眼。如果在這里寫作的人是她們,我們又會讀到怎樣的言語、抑或是絕望的沉默?
厚厚的化療記錄中,也有二次手術的記錄。教授們畫的術中示意圖不像第一次手術那樣星星點點,因為根本也沒剩下什么。這是腫瘤的妥協也是醫生的妥協。然后便要在打擊中繼續積攢精神和意志戰斗下去,更大的化療劑量更重的副反應……
說到恐怖,我們可能立刻想到披著濕漉漉黑色長發的貞子爬出屏幕變成現實,想到聊齋里面的女鬼陰笑著描畫人皮,我們對著電視驚聲尖叫,但是只要一關上電源就可以立刻告訴自己,這些毛骨悚然的家伙并不存在,全都是假的。這些不幸罹患惡性腫瘤的人,卻不能通過切斷電源來讓它們消失,她們是否在無人的時刻驚聲尖叫,每天從她們床前輕松走過的醫生們,被平穩的生命體征和整潔傷口愉悅著的醫生們,又如何能知道呢?
我之所以如此好奇,是因為我自己也只有這么一點兒承受能力。見過太多悲劇,同事聊天的時候都故作輕松地說,輪到自己就自行了斷算了吧,哪有那么多的力氣去保持最后的尊嚴等待被擊潰。可這些黃色紙張上的人物不還是一次一次地從手術臺上下來,回到生活里,再等待下一次戰役。
令人意外的是,有本病歷里面竟然還夾著病人出院后寫給醫生的一封信,按理說這種“不科學”的東西不會出現在這里。信上說:“這次手術后,我想在貴院再做化療,不料貴院堅持說我已是生命無時了,我萬般無奈只能轉到××醫院繼續治療,然后回家休養,病情完全沒有按貴院的預言發展。我一日三餐,每餐1~2個饅頭,精神飽滿,思維、記憶、反應都很正常,我經常到街上走走,買些東西……我知道我的病是不好治的,但我希望院方再遇見這種病號,也不宜把話說得太絕,讓病人從而放棄治療坐以待斃……我不會說話,希望諒解。今后有什么新的醫療手段時,再望施恩!”
不能評論,無法評論,有什么資格評論。也許前輩們把這封信夾在病歷里,是為了讓看到信的每個醫生肅然:病人都沒有絕望,我們怎么能放棄。所能做的就是努力努力再努力,你不是一個人在戰斗。
選自《城市快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