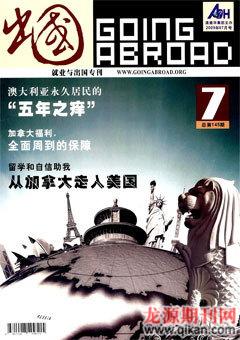冷漠成都今方信
程寶林,1962年出生,湖北荊門(mén)人。1985年畢業(yè)于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新聞系。2005年畢業(yè)于美國(guó)舊金山州立大學(xué)(SFSU)創(chuàng)作系,獲藝術(shù)碩士(MFA)學(xué)位。曾任《四川日?qǐng)?bào)》編輯、記者,美國(guó)世界日?qǐng)?bào)編譯,現(xiàn)任舊金山美國(guó)華文文藝界副會(huì)長(zhǎng)、《美華文學(xué)》季刊執(zhí)行主編。1982年開(kāi)始發(fā)表作品。1994年加入中國(guó)作家協(xié)會(huì)。著有詩(shī)集《雨季來(lái)臨》、《未啟之門(mén)》、《春之韻》、程寶林抒情詩(shī)拔蘋(píng)》、《紙的鋒刃》(英漢雙語(yǔ));散文集《燭光祈禱》、《托福中國(guó)》,《國(guó)際煩惱》、《心靈時(shí)差》、《一個(gè)農(nóng)民兒子的村莊實(shí)錄》:長(zhǎng)篇小說(shuō)《美國(guó)戲臺(tái)》等。詩(shī)歌《未啟之門(mén)》獲四川省第二屆文學(xué)獎(jiǎng),詩(shī)集《程寶林抒情詩(shī)拔草》獲成都市第三屆金芙蓉文學(xué)獎(jiǎng),散文集《托福中國(guó)》獲成都市第四屆金芙蓉文學(xué)獎(jiǎng),新聞專(zhuān)著《星光做證:中國(guó)藝術(shù)節(jié)》獲1998年四川省五個(gè)一工程獎(jiǎng),《一個(gè)農(nóng)民兒子的村莊實(shí)錄》入選2004年信息網(wǎng)絡(luò)杯上海市民最喜愛(ài)的20本書(shū)書(shū)目。20多年來(lái),其詩(shī)歌、散文作品被收入約100部選集,并被譯成英文、日文和越南文。
成都9路公共汽車(chē)火焚事件,已經(jīng)過(guò)去幾天了。雖然我內(nèi)心哀痛,卻并沒(méi)有打算寫(xiě)一篇文章,直到今天早晨,我在湖北荊楚網(wǎng)上,看到了這場(chǎng)大火的一段視頻。我的悲哀沒(méi)有減少,憤怒卻油然而升。
當(dāng)?shù)氐拿襟w,都在談?wù)摴财?chē)是否配備有“安全錘”的問(wèn)題。試想一下,在定員30多人,卻擠滿了120多人的公共汽車(chē)?yán)铮蠡稹昂衾病币幌侣悠饋?lái),即使有錘子,怎么能夠找到它?又哪里有足夠的空間,可以揮舞錘子,將那樣厚的玻璃砸開(kāi)?
安全錘,至少有幾把,應(yīng)該固定在車(chē)窗外面。一旦發(fā)生火災(zāi),車(chē)門(mén)無(wú)法打開(kāi),車(chē)外的救援者,可以用它將窗戶砸破。
公共汽車(chē),所有玻璃,都應(yīng)該設(shè)計(jì)成美國(guó)公共汽車(chē)上,將安全手柄反拉即輕易脫落的那種。越是高檔的公共汽車(chē),逃生設(shè)備應(yīng)該越先進(jìn)。
話題回到這段視頻上。視頻開(kāi)始時(shí),汽車(chē)剛剛冒煙,還沒(méi)有見(jiàn)到明火。在冒煙汽車(chē)的旁邊,一輛白色面包車(chē),以極其緩慢的、勝似閑庭信步的速度,觀賞式地駛過(guò)。一個(gè)路人,徒勞地繞著冒煙的汽車(chē),試圖救援,但赤手空拳,毫無(wú)辦法對(duì)付密閉的玻璃。周?chē)鷰讉€(gè)路人,也在不緊不慢地張望著那輛黑煙滾滾的公共汽車(chē),好像在看西洋鏡。
那輛慢悠悠駛過(guò)的白色面包車(chē)的駕車(chē)人,難道沒(méi)有聽(tīng)到震天的哭聲嗎?那錐人心肺的“救命”聲?你的工具箱里,難道沒(méi)有任何鈍器,可以用來(lái)砸玻璃嗎?
對(duì)危害公共安全因素的容忍,甚至視而不見(jiàn),是中國(guó)災(zāi)難頻發(fā),且每次災(zāi)難都傷亡慘重的根本原因之一。
2003年6月26日,我寫(xiě)了一篇《無(wú)話可說(shuō)》(已收入思想隨筆集《洗白》中,紐約柯捷出版社2009年5月出版),其中有這樣一段,涉及到公共汽車(chē)和長(zhǎng)途汽車(chē)的安全問(wèn)題,現(xiàn)抄錄如下:
我清楚地記得,10多年前,我從四川回老家探親,在荊門(mén)市搭上長(zhǎng)途客車(chē),見(jiàn)到兩名農(nóng)民打扮的青年男子,用麻袋抬著一個(gè)沉甸甸、鋼桶一樣的東西上車(chē)。我一看麻袋口,原來(lái)是從荊門(mén)市煉油廠灌的天然氣,準(zhǔn)備運(yùn)回家里。我仗著自己的記者身份,對(duì)這兄弟倆說(shuō):“這是危險(xiǎn)品,不能搬到客車(chē)上來(lái)吧?”兄弟倆瞪了我一眼,其中一人說(shuō):“司機(jī)都讓我們上車(chē),你管什么閑事!”我轉(zhuǎn)而對(duì)司機(jī)說(shuō):“你們這樣將危險(xiǎn)品和旅客混運(yùn),違反安全規(guī)定啊!”司機(jī)斜了我一眼,不屑地說(shuō):“我們這里都是這樣的,你怕死就下車(chē),自己坐小車(chē)嘛!”那時(shí)真窮,買(mǎi)好的車(chē)票又不能退,我和新婚的妻子,就這樣和全車(chē)旅客一起,守著這個(gè)隨時(shí)可能因震蕩而爆炸、燃燒的“炸彈”,朝我的故鄉(xiāng)駛?cè)ァ0肼飞希?dāng)這兄弟倆終于將那個(gè)“炸彈”抬下車(chē)時(shí),我和全車(chē)人都松了一口氣。在我的身上,也有這樣的奴性和惰性。在退回去不過(guò)20多年前,僅僅說(shuō)錯(cuò)一句話,就可能倒霉一輩子的社會(huì)環(huán)境里長(zhǎng)大,人們對(duì)于不公平的接受和忍耐能力,也是我們民族文化傳統(tǒng)中的糟粕之一。如果全車(chē)的乘客發(fā)出怒吼,那兄弟倆斷然不敢將天然氣罐搬上客車(chē);如果我當(dāng)時(shí)立刻下車(chē),找到汽車(chē)站的負(fù)責(zé)人,出示自己“黨報(bào)”記者的記者證,向他抗議,甚至,向市政府書(shū)面反映情況,或許,情形會(huì)大為不同。
據(jù)報(bào)道,這次成都的公共汽車(chē)火災(zāi),是有人將一桶液體帶上了擁擠不堪的汽車(chē)。
不僅要迅速制定法規(guī),禁止將任何易燃液體帶上公共汽車(chē),而且,要對(duì)公眾進(jìn)行安全教育,培養(yǎng)公眾的安全防范意識(shí),讓全體乘客,對(duì)威脅到自身乘車(chē)安全的隱患因素,如其他乘客試圖帶上車(chē)的不明液體等,產(chǎn)生自覺(jué)抵制的意識(shí)。如果看見(jiàn)有人將瓶裝的、桶裝的不明液體帶上車(chē),車(chē)門(mén)前的乘客,都有權(quán)拒絕其登車(chē),除非那是可以打開(kāi)就喝的飲用球。
在我的博客上,鏈接了幾位成都作家的博客,他們都是我關(guān)注的作家。他們生活在那座被稱為“來(lái)了就不想走的城市”。
災(zāi)難發(fā)生后,朋友冉云飛寫(xiě)道:成都成了一座“來(lái)了就跑不脫的城市”。
在博客中寫(xiě)到這場(chǎng)災(zāi)難的,只有他一人。其實(shí),我希望看到其他的朋友,對(duì)這一悲劇的評(píng)論和建議、呼吁。
每個(gè)作家關(guān)注的重點(diǎn)自然不同,但現(xiàn)在而今眼目下,那些文字與血肉之軀、與引車(chē)賣(mài)漿者息息相關(guān)的作家,如冉云飛兄,更為急需和稀缺。
在一個(gè)現(xiàn)代化的大城市里,這樣的人間煉獄,原本是不該發(fā)生的。一旦發(fā)生,一定是某個(gè)或幾個(gè)環(huán)節(jié)出現(xiàn)了嚴(yán)重的錯(cuò)誤。找到這幾個(gè)環(huán)節(jié),將它們嚴(yán)厲杜絕,這遠(yuǎn)非一日之功,但要持之以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