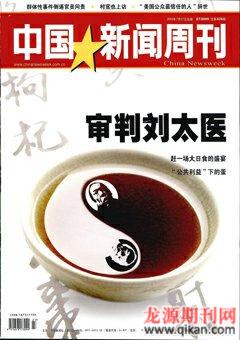華裔作家張翎:在加拿大寫唐山
楊 時
當中國大陸的作家與寫實主義創作已揮別多年的時候,旅居海外20年的張翎卻在用最為傳統的考證和寫作方式講故事

在《非誠勿擾》不可思議地攬獲超過3億4千萬票房之后,馮小剛的下一部電影《唐山大地震》已于7月初正式開機,在發布會上,導演更是放下豪言,希望電影能賣5億。
除了自己的“御用”搭檔王朔、劉震云等,馮小剛電影的原著一般來自不大出名的作品。如上一部《非誠勿擾》,改編自臺灣作家陳玉慧的《征婚故事》;《集結號》來自海軍退伍老兵楊金遠的《官司》。
這一次,被導演看中的作家是一名來自境外的中文作家。它改編自旅加華裔女作家張翎的小說《余震》。
作為海外華人作家中的一員,已年過50的張翎借助《余震》的改編,從文學圈內開始向大眾擴散,逐漸被關注。
別人沒有這樣寫唐山地震
《余震》的創作靈感,來自張翎的一次“意外”。
2006年7月末的一天,一場突來的暴雨讓北京地下排水系統幾近癱瘓。
正要從北京赴加拿大的張翎,車子在一片河澤中突圍趕到機場后,才得知飛往多倫多的航班推遲了9小時。百無聊賴的她開始在機場書店閑逛。那段時期,這個平時充滿成功學書籍的書店里突然擺滿了關于“唐山大地震”的各種回憶錄。張翎猛然想起,這天是7月28日,剛好是唐山大地震30周年祭日。
仿佛冥冥之中的相遇,已經從事寫作近10年的她,決定寫一部有關唐山大地震的小說。
在已完成的小說《余震》中,主人公王小燈是一名旅居加拿大的華人作家,常年因嚴重焦慮失眠,多次企圖自殺。她來到了一家心理診所。在醫師的引導下,她學習哭泣與傾訴,嘗試與30年前地震的那一天遭遇。所有的慘痛經歷在漫長幽深的記憶隧道中復活,她開始直視將她擊倒的命運——在地震中,王小燈與弟弟一起被掩埋在廢墟下,一根梁柱如同命運的天平般懸置在二人頭頂,撬起一端,另一端的人就會被永埋地下。王小燈透過瓦礫聽到自己的媽媽向施救者表示她的選擇是弟弟……但是她卻活了下來,雖然眾人都以為她早已不在人世。從此,命運開始了對于她的放逐——被收養的生活、成長、上大學、出國……可那一天的傷痛卻更加刻骨,直到崩潰。
“我終于推開了那扇窗。”在小說的結尾,張翎給了王小燈一個溫暖的轉機。張翎在加拿大找來各種唐山大地震的文獻,她才發現,自己當年居于溫州小城時聽到的關于地震的信息,全部都是過濾后干癟的傷亡數字和空泛的口號。而事后,對于孤兒的記述,也永遠缺乏血肉,這些經歷了厄運的孩子總是被一些句子概括一生——“某某以優異成績考入大學”“某某成為技術骨干”。曾經難以想象的傷痛似乎從未在他們身上心里留下任何痕跡。
張翎對這些冷酷的句子充滿了反叛。
“我想寫的是,有的時候苦難可以把人打倒,永遠讓人站不起來。”張翎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并不是所有苦難都能成就一個人。它也可以摧毀一個人。”
于是,張翎開始著力于一個人內心和精神上的余震,以及他們從未消失過的顫抖和內部無法愈合的創口。
寫作之初,有文學雜志的朋友勸她,“關于唐山大地震的文字太多,不要寫了。”張翎拒絕了。她覺得能寫出與已有回憶錄不同的東西。《人民文學》副主編李敬澤評價說,“《余震》幾乎是僅有的一部‘這樣寫唐山大地震的小說。這么百感交集的經驗和大事件,國內作家竟然沒怎么涉及,需要一個旅居加拿大的作家去寫。”
為“豬仔華工”書寫文本
其實,《余震》是張翎寫作中的一次異數。在她的寫作脈絡中,更多的作品圍繞著是一個人,或一個家族跨越大洋之后的生活,由此牽連出的人物命運和背后更為深厚的歷史背景。
《余震》屬于張翎中后期的作品。她從1997年開始寫作,那是她到達加拿大的第十個年頭。她早期的長篇如今被作家自己歸納為“江南系列”,一般都是根植于家鄉溫州和南方的故事,主人公從小城來到加拿大,身后的家族和歷史的記憶與加拿大的現實生活相互纏繞沖撞。那段時期,她寫了《望月》《交錯的彼岸》和《郵購新娘》。
1997年之前,張翎不寫作。
在加拿大之初的10年,她到處奔波,只為生計,就像她后來小說中的某些人物那樣。那段日子和大多數“庸俗的中國人”在國外的奮斗史沒有兩樣:1986年,張翎因為自己的性格與國內的人情氛圍格格不入,她離開北京穩定的部委機關,遠赴加拿大。憑借曾經的英文專業她開始重新學習新的專業。
在拿到英美文學與聽力康復師兩個學位的過程中,張翎搬家超過20次,嘗試了從賣熱狗到行政秘書的多個職業。直到有一天,她發現,聽力康復師這個她不討厭也不熱愛的工作能帶來逐漸穩定的生活。
之后,她開始白天工作晚上寫作。張翎說自己并不勤奮,有時旅游,有時聚會,只是寫作進入狀態后比較有效率。寫完后,她把稿子打印出來,直接寄往國內的《收獲》雜志社,這個幾乎不看自由來稿的大牌文學雜志,卻莫名其妙地發表了她的小說,而且一連五部。
于是,張翎又增加了海外華人作家的身份,雖然直到現在,她仍需要靠診所謀生。
逐漸地,張翎開始厭倦了書寫江南的陰郁和梅雨。于是,她固執地寫出了《余震》和《向北方》,不熟悉的北方讓她感到舒服和新鮮。寫不下去時,她就無目的地閱讀,比如讀納博科夫或者克萊齊奧。她喜歡體驗那些移民作家文筆下的暗流。
直到她想起初到加拿大時,在一次旅行中見到的墓碑。那些荒廢的石頭上刻著發音古怪的拼音名字,照片中的人高顴骨、臉色發黑。張翎了解到,這是一群晚清的中國僑民,被人稱為“豬仔華工”,他們在加拿大挖金子、修鐵路,積攢了錢財寄回家中,自己卻活在生死一線間。
張翎決定為這群“豬仔”留存一個文本。她開始駐扎圖書館和檔案室。可那些不識字不懂英文的華工沒有自己的歷史,張翎只找到很少的英文文獻。她仔細地考證那個時代的每一個細節:衣服的紐扣、肥皂的香氣、相機可拍照的數量……她還去加拿大的港口尋找華工登陸的地點,特意回到中國廣東,聽華工的后人講述故事,進入那些用命換來的家族的碉樓去觸摸墻壁。
于是,有了小說《金山》。
這是一部龐雜的家族史。繁復的細節勾勒出的故事,橫跨了海峽,講述百年來種族、文化、制度沖撞下“豬仔華工”的家族命運。
從國門外回看自己的家族與歷史
《金山》后來在《人民文學》發表。在虛構的故事背后,是作家精耕細作的歷史考證,嚴謹得如同歷史調查。作家這種近乎嚴苛的歷史細節考證,以及跨越海峽寫作家族史的視角,迅速區別出了她與大陸作家的本質差異。(《金山》后被改編成同名電影)
有人這樣形容中國與國外作家創作的不同:中國大陸作家是在書房寫作,而外國作家是在圖書館。或許這也是長期旅居加拿大的張翎與國內作家不同的原因。
作為非職業作家,張翎似乎缺乏玩弄文學技法的興趣。她不先鋒、不現代、不魔幻、不解構,她缺乏任何一種“主義”的氣質,只講故事,如同執拗的說書人。但這反而讓人在她的作品中被小說最本色的東西吸引——故事。
“張翎寫作方式的這種傳統,中國大陸作家已經忘記了,不會了。”批評家李敬澤對《中國新聞周刊》說,“人們總在說現實主義。而現實主義怎么做?現實主義的藝術品質和工作倫理,從張翎這里可以看到。”
作為旅居海外的華人作家,張翎不可避免地接觸那些生活在異鄉、被連根拔起的人。這些人對于異國的心態總是處在攀爬和仰視的視角,身份認同的焦慮成為揮之不去的噩夢。
也因此,國內某些評論稱海外華人的文學作品為“第二次傷痕文學”。
還好,這沒有在張翎的書中成為常態,在加拿大經歷長達10年的沉默和心理適應之后,方才拿起筆的張翎,在作品中少了控訴的語調,尤其后期的作品。
“我更關心的是人的命運,首先是人,然后才分白人、黃種人和印第安人。”張翎說,“只是客觀上,有一些人被命運拋到了一個叫外國的地方。文化沖突客觀存在,但我下筆時從來沒關心過這樣的話題。”
嚴格來說,張翎的小說更多的是對于家族歷史的回溯。由于她身居海外,熟悉了旅居家庭生活的圈子,故很多作品都以海外華人的帽子和外衣作為由頭,但根仍盤纏在國內的泥土。“我偏愛從歷史延伸到當下。只寫當下我就會很迷惑,沒經過時間的考驗(的事),我寫著很沒底氣。”張翎如是說。她深信,成年后的敘事都只是對于童年各種版本的回溯。同時她也承認,在國外久了,即使書寫故鄉,視角也會不同。她拿自己的文友、海外華人作家嚴歌苓的作品作為“佐證”,“像《第九個寡婦》《小姨多鶴》,是國內作家也可以寫的題材,但是味道就是不一樣。”其實,張翎自己的作品也大抵如此。
在國外居住的華人作家分為兩類。一類用英文寫作,有些已進入西方主流,但在國內無甚名氣,比如譚恩美、哈金等;另一類,就是以嚴歌苓、張翎為代表的,旅居國外多年,但一直用母語寫作,他們或在國內文學圈內尚有人知曉,但因無英文版本,在國外文學圈了無痕跡。
如今,張翎每周在聽力康復診所工作4天,閑時寫作。她準備按照《金山》的路數再寫幾部關于家族歷史的小說。國內出版社要為她出一套文集,她覺得今年是她的小豐收年。但張翎仍然覺得,自己是一個“國內國外兩邊都不入流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