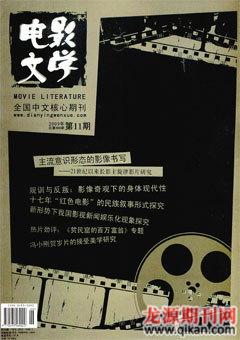“民族寓言”與“政治神話”
余愛春
[摘要]可以說,《芙蓉鎮》是謝晉電影中的巔峰之作。在影片中,導演充分調動多種電影語言、手法和技巧,透過歷史和現實的表層深入到民族文化的深層內核,從民族文化根性和歷史哲學的高度,對這一特定歷史時期中國歷史進行重寫,建構起幻覺化的“民族寓言”和“政治神話”。
[關鍵詞]《芙蓉鎮》;意識形態;政治神話
在謝晉導演生涯中,《芙蓉鎮》是讓謝晉獲得巨大聲譽和產生深刻反響的一部影片,是謝晉電影中的巔峰之作。影片很好地秉承謝晉電影以嚴謹的現實主義手法給觀眾以強烈的情感沖擊和審美愉悅的特點,充分調動多種電影語言、手法和技巧,透過歷史和現實的表層深入到民族文化的深層內核,從民族文化根性和歷史哲學的高度,對這一特定歷史時期中國歷史進行重寫,建構起幻覺化的“民族寓言”和“政治神話”。
一
電影作為社會意識形態的產物,常常與當時的主流意識形態話語和現實的社會主題契合統一。謝晉就說:“一個比較重大的作品,總歸是要跟國家的命運、時代特征、人民關心的東西聯系在一起的。”與以往那些專注于表現兩種政治力量之間的奪權斗爭不同,《芙蓉鎮》不再拘泥于政治斗爭本身的展現與渲染,而是從女主人公“芙蓉仙子”胡玉音的人生遭際和坎坷命運入手,通過惡劣政治環境中人性的摧殘、異化與扭曲和多元對立的影像奇觀,展現了20世紀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末這一特定時期的中國社會現實和政治狀況,在人道主義立場和時代的高度對這段“荒誕的歷史”進行深層次的反思與拷問,再造了這段民族苦難歷史。
如果說十七年、“文革”時期影片主要表現為簡單的階級對立、敵我對立關系的話,那么,《芙蓉鎮》則表現出對立關系的多元復雜性和豐富性,既有階級的對立、政治上的革命與反革命的對立,又有善與惡、壓迫與被壓迫等的對立。胡玉音和李國香是影片中的主要人物,她們之間的對立關系成為貫穿全片的主要線索,影片圍繞著她們構成了錯綜復雜的網狀關系結構。胡玉音是一個美麗大方、勤勞善良的農村婦女,她與丈夫每天起早貪黑、拼命苦干,逐漸擺脫貧困過上了比較富裕生活,成為芙蓉鎮勤勞致富的代表;然而,歷史和政治運動的荒謬性在于,正是她那合情合理的“勤勞致富”,“四清運動”的到來使她成為批判的對象,被劃為“新富農”,導致家破夫亡,受盡十多年凌辱與折磨,甚至連最起碼的愛的權利也被剝奪;影片不止于對胡玉音外在的人生悲劇的展示,還深刻揭示出她對悲劇根源的麻木與無知,在她看來她之所以陷入悲劇境地,不是由于極“左”政治運動而是“右派分子”秦書田所致;可見,胡玉音的悲劇既是人的悲劇,是社會的悲劇,更是民族文化的悲劇。與胡玉音的悲劇處境不同,作為政治運動健將的李國香,依靠縣委書記舅舅關系步步升遷,由國營飯店的經理一工作組組長一公社主任一縣革委會常委,成為芙蓉鎮實際上的領導者和政治運動的發起者,她沒有女性應有的溫柔,有的只是鐵的政治。她借革命的名義對無力抗爭者任意踐踏和傷害,對欲望挑戰者瘋狂報復,她實際上是一個被極“左”路線桎梏和扭曲了心靈的悲劇人物。特別是她被紅衛兵批斗時堅持不與所謂的階級敵人“黑五類”站在一起,無不彌漫著極“左”路線的陰影,顯得荒誕而悲哀,引起我們對“文革”的深沉反思。
與胡玉音形成鮮明對照的另一人物是“土改根子”王秋赦,如果說胡玉音被劃為“新富農”和“黑五類”顯示了極左運動不合理和荒謬性的話,那么王秋赦成為芙蓉鎮政治運動的積極分子和新的領導者就進一步凸顯了“文革”的荒誕和民族文化中先天的劣根性。王秋赦是一個懶惰成性的流氓無產者,他每天懷揣著觀音像在“白日夢”里生活,他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改變貧窮現狀,而祈求于政治運動,正是這樣的人物反而成了極“左”政治運動的“中堅”,成了芙蓉鎮百姓熱烈歡迎的“公社書記”;“文革”結束后,發瘋的王秋赦仍然敲著破鑼“運動啰”的叫喊,無不讓人深思和警醒。在王秋赦身上不僅形象地展示了那個年代“越窮越光榮”“越窮越革命”的荒謬邏輯和政治運動對人心靈的毒害與異化,而且也讓我們認識到了那個時代“革命”的真正含義和民族文化的痼疾所在。《芙蓉鎮》正是通過人物的悲慘命運和人性的扭曲對極左政治運動進行了透入骨髓的批判,并引導我們對社會歷史與現實進行深刻反思,進而匯成一股渴求變革現實的輿論與氛圍。
與此同時,對立反差的情境畫面和無所不在的援助者也實現著《芙蓉鎮》對意識形態的支持與傳達。影片開頭就呈現了一組對立的畫面,胡玉音米豆腐攤前熱鬧繁忙和諧景象與國營飯店冷落清靜無聊形成強烈的對照,這雖然有夸張和渲染成分(因為在1963年的農村不可能如此),但導演正是運用這種夸張來強化“大鍋飯”和國有經濟模式的弊端,暗示小私有經濟、自由經濟存在的合理性和進行農村經濟改革的必要性,也正因如此,影片結尾時再一次呈現米豆腐攤前熱鬧景觀,這既是對前段荒誕歷史的否定,也是對新政策和前景的肯定與展望。以及影片中“黑五類”秦書田和胡玉音真心相愛而被判刑坐牢,而李國香與王秋赦偷雞摸狗的奸情卻堂而皇之;胡玉音被劃為“新富農”前后的人情反差等等對立反差的情境,無不對缺乏人道的極“左”運動予以了有力的批判與反諷。同時,《芙蓉鎮》與謝晉的其他影片一樣,影片中有一個正義的化身、黨的化身的“援助者”來幫助主人公價值的實現。但又與《紅色娘子軍》《春苗》《天云山傳奇》等影片無限神化或夸大個別幫助者不完全相同,《芙蓉鎮》所夸大的既是個別扮演者,又是一個無所不能的缺席者即改革開放的社會。影片中對胡玉音始終給予幫助的有兩個具體的人,一個是正義的化身、黨的化身的谷燕山,一個是知識化身的秦書田;而最終使胡玉音等人重新獲得做人的權利,使芙蓉鎮又恢復昔日繁榮景象的,正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改革開放的新社會。這種對極“左”政治運動的批判,對改革開放新社會的充分肯定,無不隱含著鮮明的主流意識形態話語。
二
電影作為社會文化的一種載體,不僅反映和再生產著特定國家、民族、社會的意識形態,而且還“再現了個體與其實際生存狀況的想象關系”,引導觀眾在想象中認同并接受其傳達的意識形態。郝大錚曾指出:
“電影語言就是電影意識形態范疇中的一種話語因素。電影生產是由意識形態決定的行為,電影生產通過用什么語言和如何使用語言傳遞意識形態信息,表明電影同意識形態的關系。”
在《芙蓉鎮》中為實現其意識形態的有效傳達,使觀眾在想象中產生強烈的共鳴和認同感,導演充分調動各種煽情的敘事手段和電影語言。為了使觀眾不至于對意識形態的傳達產生反感情緒,影片并沒有對極左政治運動進行濃墨重彩的渲染,而是以1963、1966、1979等時間概念把“四清運動”“文化大革命”和“撥亂反正、改革開放”等歷次政治運動作為人物生存的現實背景表現出來,并把筆墨重點投射人物命運、思想、情感和心理沖突上。同時,為了突出影片的悲劇效果,大量運用長鏡頭鋪墊和渲
染氣氛。為了突出胡玉音夫婦勤勞致富那場戲,影片在序幕和開頭兩次使用三分多鐘的長鏡頭對他們起早貪黑賣米豆腐和拼命苦干建新屋進行了渲染鋪墊,這樣就為后面胡玉音悲劇命運的不合理、不合法性找到支撐,從而使觀眾產生同情心和悲憤感,在充分認識到極“左”政治運動的荒誕與錯誤的同時,對“文化大革命”予以了否定。不僅如此,影片還借助獨特的電影語言來反思歷史,反思政治運動給社會和人性刻下的傷痛。影片對色彩的運用很有特色,通篇都是那種陰郁的青灰底色,特別是胡玉音知道丈夫去世后獨自去墳地的那場戲,不僅使用五分多鐘的長鏡頭,而且始終以灰暗的色調和哀戚的民歌小調貫穿始終,這種凝重、壓抑、陰冷的青灰色色調與哀怨、凄涼民歌曲調相附和,把胡玉音失去丈夫之后傷心欲絕、悲痛凄楚和孤獨無助襯托出來,既凸顯了人物命運的悲慘,強化了影片的悲劇色彩,又加強了影片的政治批判力度,取得了獨特的煽情效果和藝術感染力。
如果說長鏡頭和青灰色色調為影片烘托出陰郁悲劇底色的話,那么,閃回鏡頭和象征手法的運用使影片產生強烈的差勢效果,有效地傳遞了意識形態信息。影片中多次運用閃回鏡頭,增強了電影的表現力和感染力。如胡玉音被劃成“新富農”后思念丈夫那場戲,首先用一個特寫鏡頭突出神情木然的胡玉音,慘淡的青灰色月光映照著她那呆滯可怖的臉,接下來就用充滿溫暖調子的閃回鏡頭把胡玉音和丈夫桂桂由相識一戀愛一結婚的幸福時光展現出來,這一悲一喜、一冷一暖的強烈對比,既映襯出胡玉音極度的痛苦、悲哀與孤寂,又折射出極“左”路線與人性、人道的背離。又如谷燕山醉酒后風雪歸途那場戲,蒙冤受屈的谷燕山,喝得酩酊大醉踉蹌在漫天飛雪清冷無邊的夜色中,此時插進一組火紅的戰斗生活畫面,這種冷曖對照閃回鏡頭,構成一幅凄清悲愴、催人淚下的油畫,從而對荒誕的政治運動進行了有力的反諷。同時,象征性鏡頭的運用也大大深化了影片的主題。石磨和鑼是貫穿影片始終的兩個富有象征意義的意象,石磨的“使用一廢棄一偶爾使用一使用”,既是胡玉音悲劇命運的形象表達,也是歷次政治運動的象征性演繹;而鑼由最初的“完好”到結尾的“破舊”,既折射出政治運動的頻繁又暗示了政治運動已經“破”了。而最具有象征意蘊要數那座建立在水上破敗臟亂的吊腳危樓,它不但是懶漢無賴王秋赦的“狗窩”,是培育民族惰性的溫床;而且也是芙蓉鎮“四清”“文革”運動的策源地,而“建在水上”本身就說明了歷次運動脫離實際,得不到大眾支持,暗含了政治運動的荒謬和錯誤,最后危樓的倒塌,既象征著“四人幫”的倒臺,宣告了“文化大革命”荒謬歷史的結束,也寄寓導演改造和重建民族文化的美好愿望。可見,影片正是通過獨特的電影語言的運用傳達著主流意識形態話語,對歷史進行批判反思的。
總而言之,《芙蓉鎮》可以說是上個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主流意識形態的一種形象化解說。影片以直面現實的手法和影像奇觀,再現了那段荒謬凄愴的歷史,對極“左”路線和“文化大革命”進行了有力的批判與深刻的反思,對民族文化的劣根性予以了審視與追問,獲得了獨特的政治美學意義和歷史文化價值,成為“謝晉電影模式”的最好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