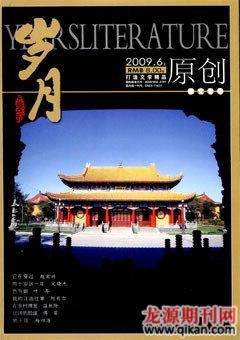在鄉村理發
溫新階
人一輩子從嬰兒“剃胎頭”開始,大約要理幾百次發的,不論你老到什么程度,很多方面不斷萎縮,唯有頭發卻依然頑強地生長,我們今天在城市的很多“大眾理發廳”常常可以看到許多老者躺在椅子上,隨著理發師刀剪的舞動,一撮一撮斑白的發須飄然而落,那老者們似乎正如一株老樹,飄然而落的似乎不是發須,而是枯槁的樹葉。
鄉下老者的理發情形迥然不同,小時候常常目睹祖父理發(那時鄉下稱理發為“剃頭”,這與舊時鄉下男人全是光頭有關)。鄉下沒有理發店,老人們理發是相互“幫忙”,那工具也十分簡單,僅一把剃頭刀子而已,即便僅有的刀子,也遠沒有今日的精致,都是請鐵匠打的,鋼火好自不必說,體積碩大,樣子笨拙,似乎不是用來剃頭,而是用來殺頭,刀柄也是自制的,杉木,稍粗的一頭鉆一個眼,一根細鐵絲便將刀子安了,再順著柄鑿一道槽,剃完頭,把刀子折疊起來,刀鋒藏進木槽里,以免弄鈍了刀鋒,也多了一分安全。至于圍布是沒有的,往往是剃頭者自己帶一塊舊布,忘記帶的,幫忙剃頭的人隨便找一塊什么破塑料布什么的對付一下,倘是冬天,那破塑料布總是支楞著,影響著剃頭人近距離作業,人一動,還嘩啦嘩啦地響……祖父是稍講究些的,除弄了一塊破塑料布做圍布之外,還有一塊半圓形的木板,漆得光亮光亮的,剃頭時,本來系了圍布,他還要用手舉著那塊半圓的木板,內圓的一側貼著脖子,頭發大多就落在木板上,剃頭人在哪邊剃,他就把木板舉在哪一邊,剃到后腦勺時,他就只能捏住木板的一邊將木板伸到背后去,那樣子十分滑稽,我一直搞不懂,既有圍布,還要這木板干啥?有一回我忍不住向祖父提出了這個疑問,祖父說:毛發是受之父母,怎忍隨便落地,與他人發須混雜?怪不得祖父剃頭時木板上的頭發落滿了,他就把它倒在鋪好的舊報紙上,剃完頭必定包回來,將其撒到房頂上,頭發未剃時便是頂天之物,即便剃下了也該作頂天之置。
父親成人時,鄉下的光頭依然流行,但念書人或是干部卻已經開始留頭發了,父親二十多歲就開始做村里的干部,自然留了分頭,祖父起先不屑,后來見留分頭的人多了,也就不再貶斥。不過理發卻有困難,舊時剃頭匠全然不會理分頭,他們也沒有理分頭的的推子。過去每種文化的傳播往往會從學校開始,果然,村小里就有了一把推子,好像是學校工會買的,本來是為老師服務的,不過僅有一把推子和一塊圍布,梳子和鏡子是理發的老師自家的,也沒有其它的刀剪,長發要剪短不好用推子,老師就拿了自家的老婆做鞋的剪子來處理,倒也沒有大的問題,一個村就這么一把推子,附近的社員都到學校來理發,過去的學校不像現在同社會有些隔膜,那時一所學校就如當地的一戶人家,校長也是這么看的,就準許大家到學校理發,每每放學后,學校的階沿上就有一些理發的人,也有的等得急了,便尋來乒乓球打上一陣,夕陽將他們的影子投射在土墻上,生動而有韻味。
到了我們這一代,自然極少有人剃光頭了,都是短發,打理簡單且有精神,可在學校卻依然會看到有些學生的頭發留得很長。大哥便是如此,倒不是沒人理,而是他小時候不讓人理發,因為他四歲時,腦袋老癢。祖父請人給他剃過一回光頭,那師傅手重,刀子又鈍,一個頭剃下來,聲音都哭嘶了,頭上還留下三個口子。從此,他就有了“護頭”的毛病,盡管不是剃光頭,一說理發他就跑到很遠的地方,因此他的頭發就留得老長,實在不像樣子了,等他睡著了以后把他抱到板凳上,用繩子縛了,再把板凳豎起來,請人給他理,后來學校來的秦老師手輕,技術好,給大哥理了兩回,再就不用縛在板凳上了,縛在板凳上理發的事,只是為后來增加了一點談資。
留長發多的主要原因還是理發的人少了,我上小學時,同班有個叫朱玉洲的同學,請人理發請了三個周末還是沒排上隊,他父親就用做鞋的剪子給他剪短了,星期一他上學時,頭上一道一道的印子,大家都喊:朱玉洲腦殼上修了梯田,男同學喊,女同學也喊,朱玉洲一邊哭一邊找老師告狀,課外活動時,我們在女班主任寢室里站了一個小時,香皂的香氣彌漫了整個房間,我第一次聞到這么香的氣息,正是這次罰站,使我把這種香氣定格為女老師的香氣,以后有女老師叫我到房間去我總是既激動又緊張。
后來我也做了老師,起初也是在鄉村小學執教,像以前的老師一樣,我也為附近的村民理發,不過我的工具較之過去已經進步了很多,不但有推子,刀子剪子鏡子梳子都是齊全的,還有用來潤滑推子的一小瓶機油,圍布也洗得很干凈,我還專門請人做了一只小木箱,漆了油漆,把理發的工具袋裝在木箱里。我也常常在放學后為村民理發,不過更多的是別人請了我去,目的是請我吃頓飯,經常在放學以后,我拎了那只木箱跟在學生身后到村民家去理發,岔路口時,學生一個一個跟我打招呼,等他們走得看不見了,我才往理發人家走去。
在村小教了兩年,我便調到鎮上去了。鎮上有理發店,理發工具用不著了,我把它送給了新來的老師,許多年以后,我已在市里混飯吃,回到鄉下見到那位老師,他還講起了那套理發工具,他說,雖然早已不能用了,他卻沒舍得丟,買了新的依然裝在那木箱里,我這才記起,我老家的鄉村,依然沒有理發店,理發依然是相互“幫忙”,不過,理發工具已經不單見于學校,每個灣每個沖幾乎都有一套。
我說:“你幾時也來給我理一回發。”
“您不在城里理?”
“喝茶就喝茶,哪來這多話。”我套用了一句民歌的歌詞。
他沉吟了一下說:“我懂了,懂了。”
我不知道他懂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