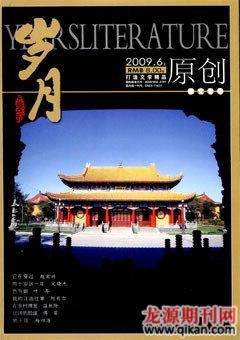蕭紅離我們有多遠
高 艷
如果不是因為一次偶然的機會去呼蘭,我想我是不會專程行三百余公里的路去探訪蕭紅故居的。但終究有了這樣一次機會,我不能錯過。
當汽車駛入小城,我眼前的呼蘭城不再是蕭紅的呼蘭城,它像現(xiàn)在所有的城市一樣,擁塞、逼仄,喧囂、麻木。呼蘭河水稀薄而晦暗,被寬大的河床似是而非地擁著,淺顯得要凝滯。
“七月十五盂蘭會,呼蘭河上放河燈了。河燈有白菜燈、西瓜燈、還有蓮花燈。”
“河燈從幾里路長的上流,流了很久很久才流過來了。再流了很久很久才流過去了。”可是,現(xiàn)在的呼蘭河,還能載得動什么?
還是上中學時,在漫無目的地閱讀中,知道了一個民國女子叫蕭紅。而她流離的生命比她生動的文字更能令我怦然心動。我想走近她,想看到她內(nèi)心真正的容顏。她的憂傷毫不隱晦,她面對感情的勇氣展露無疑。然而又能怎樣,是天道不公,還是命運多舛?及至看到“我將與藍天碧水永處,留得那半部《紅樓》給別人寫了”,“平生盡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我內(nèi)心的疼已漫無邊際,至今讀起來仍絲絲縷縷,為蕭紅,還是為所有和她一樣的女人?
有人說,這是一種心如止水的悲哀。或許,這更是一種對命運無能為力的接受。
愛是女人的宗教,如此,女人的需要便很簡單,不過是個溫暖的去處,一份安全的情致和寄托。雖是這樣的簡單,卻是女人常有的幻想和稚嫩。——因為在人世間,它太不容易讓人得到。上天總要成就一些絕望和悲涼,最昂貴的情感總要經(jīng)受辜負與背離,人間便注定要有人去承受它們。
就是這樣。
蕭紅說,“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邊的累贅又是笨重的!……不錯,我要飛,但同時覺得……我會掉下來。”
“想望得久了的東西,反而不愿意得到。怕的是得到那一刻的顫栗,又怕得到后的空虛。”于是,她在一個問題的結束和另一個問題的開始中,循環(huán)自己的想要和痛苦,驚恐與疲憊。她的一生,便在對愛的追隨中,承受心靈與肉體的顛沛流離與寒涼。
“酷寒把大地凍裂了”。她的筆在男人的世界里蕩出一片耀眼的光采,她的文字卻成為自己生活的讖語。
她的頭發(fā)白了,她貧病交加,——年輕的蕭紅,讓我們心生哀痛。
蕭紅如是,還有誰?
就像我們知道,1932年的蕭紅,在自己21歲的日子里與蕭軍彼此認定終身一樣,1929年的法國巴黎,盧浮宮前,同樣21歲的波伏娃與薩特理性地達成契約婚姻協(xié)議。蕭紅與蕭軍走進的是以忠貞為藍本的約定俗成的婚姻,而波伏娃與薩特相互約定,卻不是終身,給彼此以心靈和身體的自由放飛。眾所周知,前者在追求長久的途中戛然而止。而后者歷經(jīng)時光風塵吹洗,卻相伴一生。這樣與初衷截然相反的結局,至今讓人難以打量,又不可忽略。
關于情感,我想是不應該接受他人品評的,因為它從來都是不能解析的命題,它只應存在于當事者的生命和體悟中。時間的光芒可以將很多事物剝離出塵土的顏色,而情感,依然是一匹光艷的綢緞。晦莫如深地鮮亮。
驚世駭俗的波伏娃與薩特自是常人難以企及,而像蕭紅這樣如玉般溫潤,卻又閃爍著堅硬寒光的女子,在人稠廣眾中,她的柔和與鋒芒同樣異常突顯,她內(nèi)心的情感只遵循她自己。她是一條激流不止的河,那些必須經(jīng)過的人一一涉水而過,而最終流淌的仍是她自己,還有別人的眼神。她對友人,同時也是對自己說,“我總是一個人走路。以前在東北,到了上海以后去日本,又從日本回來,現(xiàn)在到重慶,都是我自己一個人走;我好像命定要一個人走似的。……”
時間清洗著每一條街道,蕭紅所走的路,行人依然絡繹不絕,不回避,不躲閃,也不猶豫。蕭紅終究成為一個走過去的人,她是回到呼蘭河邊那老宅里暖暖的后花園依偎在老祖父的身旁,還是依然在那個叫淺水灣的地方徜徉,或是在她生命里三個男人的夢寐中流連?
在《呼蘭河傳》中,她問,“那河燈,到底是要漂到哪里去呢?”
我們呢,要去哪里?能去哪里?
她淺笑著,無語地看著我們離她很遠。又很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