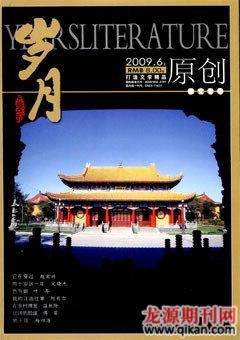親密女友
張 科
我有個親密女友,她比我大四歲。
她的個子比較高,身材長得挺拔、俊美,白皙的臉上,架著一個方框的黑邊近視鏡,鏡子里的一雙清澈的大眼睛,閃著柔和而睿智的光芒。
我們同在一個單位,她是編輯,編散文;我在機關當干事,也喜歡散文,閑暇時裝模做樣、舞文弄墨的。
她可以說是個文化名人。第一次看到她時,她剛從北大畢業。我當時在文化局工作,在她們的樓上。一天傍晚,我下班到樓下走廊取自行車時,順著門縫看到一個女人端坐在一個簡陋的木椅上,正在與什么人交談。她面帶微笑,紅紅的臉龐像一個熟透的蘋果。齊齊的留海,披著濃密的長長的秀發,渾身透著青春的氣息。經打聽,我才知道她是誰。
一年后,文聯與文化局分家,我們工作在一起。在我的想象中,會寫作的名人,特別是名女人,一定會很張揚、很高傲,她卻不,她是謹慎小心的、善解人意的。她說話的語氣是濕潤的、暖暖的,那帶有彈性的哲理性的話語,說得那么貼切、那么恰到好處。聽她講話,就像沐浴了五月的春風,喝了沁人心脾的清茶。不知從什么時候開始,我們的心慢慢在貼近,她成為了我的摯友和文學上的伯樂。
大約在十多年前吧,我在《大慶石油報》上發表了一篇散文,她發現了,如發現了新大陸,眼里閃著驚喜!她高興地說,寫得很好嘛!她毫不猶豫地編輯在當年的《歲月》期刊中。但這篇稿子由于篇幅小,最終被總編拿了下來,我并沒太在意,但她卻很難受、很無奈。
在一個乍暖還寒的季節,她來到我的辦公室,她穿一件紅色的羽絨服。早春的陽光透過窗欞,室內顯得暖洋洋的。她的聲音也充滿了溫暖。她說,你寫文章很有感覺,你應堅持下去。我說,我想寫的素材很多,只是不知怎么寫。她說,你應該先寫你最熟悉的人和事,先寫親情吧!我突然想起了我的母親,想起了母親臨終前想見我沒見到我的情景。我流著淚向她述說了這段讓我難以忘懷的往事和我的真實感受。她顯然受了感染,停頓了一會兒,說,我琢磨琢磨,回去寫個提綱,明天帶來。第二天,她果然在一張稿紙上,為我認認真真地寫了一個提綱。我按著提綱的要求,懷著對母親最真摯的感情,寫下了一篇兩千多字的散文。她看后很滿意,文章的標題是她為我改的叫“等待”,這篇稿子被她編輯在1993年第3期的《歲月》雜志上。就是這篇散文,被當時省文聯來大慶開會的幾位作家看到了,他們很受感動。記得一位叫劉亞洲的作家說,寫得太有真情實感了!我知道,這也包含著對我的鼓勵。從此,我便開始了文學上馬拉松式的奔跑,盡管每天忙工作忙孩子,能用在文學創作上的精力不多,但就像龜兔賽跑中的烏龜,雖然慢,但沒有停止腳步。每當我在文學創作上有什么感受,我就找她談,在她那里我獲得了鼓勵,就動筆寫出來,每年總能發表幾篇。直到今天,我終于積攢下四五十篇散文,并嚴格忠實于生活,生活的原生態,生活的粗糲,生活的辛酸和辛苦中的溫情,這些都得益于我們的交談。
她對我就像對她的親妹妹一樣,對我的寫作要求也是很嚴的。
1995年,一個春意盎然的日子。我寫了一篇散文《舊居八年》,這是根據我自己的真實生活寫的,自己覺得很滿意。當我興高采烈地把稿子交給她,不料她看后,并沒有歡樂的情緒,而是很嚴肅地說,寫得太粗了,你再重寫一遍吧!她見我有些不解和疑惑,就和緩地說,不要嫌煩,重寫一遍總比第一遍強。我聽了她的話,我重新地、細細地又寫了一遍。盡管情節是一樣的,可經過潤色、提煉,文章變得生動、語言流暢,生活色彩濃郁。1997年我參加全國青年作品研討會,就是拿這篇作品參賽的,中國藝術研究院副院長鄭恩波在閉幕式上特別提名稱贊我的文章,他說,張科的散文寫得很漂亮。這篇作品在此次大會上獲全國大賽一等獎。
我像一塊海綿,在她的身上不斷地汲取著營養。我們的友誼也像綠意蔥蘢的植物瘋長著。
我倆常常頂著一把防曬花傘,沿著林蔭小路,邊談邊向著我們經常相聚的地方——一家現代化商場走去。當然話題離不開文學。她跟我談到了茨威格的心理描寫小說,海明威的《老人與海》等一系列文學精品。她說,茨威格的心理描寫小說,語言和意境都很美,你看了對你的寫作會有幫助的。我們在商場的四樓找一個僻靜的地方坐下來,頭上一盞盞黃色的小燈,像黑夜天上的繁星,很溫柔地眨著它的眼睛。在我們不遠處,有一對年輕的情侶在交談,他們的眼里透著柔情蜜意。她要了兩杯熱奶,我倆一人一杯,話題很輕松,居然還談到了愛情。我們一邊笑年過四十歲的女人談愛情令人可笑,一面還忍不住要談愛情。屋內溫度涼爽,熱奶散發著柔柔的、細細的白色霧氣,它們升騰著、依附著、又交織、纏繞在一起。我們的話題無不涉獵,她跟我談到了“已做不失,未做不得”,“不要樹敵……”其思想內涵,就像她的散文那么深刻、那么耐人尋味。我覺得我的靈魂在升騰和飛躍……我們又談到了文學,談到了文學所追求的意境,我感覺我來到春天的大草原,在開滿黃色的蒲公英的草原,我一面采集著花朵,一面大聲地歌唱,突然,幾股山泉從四面八方奔涌而來,瞬間變成了大河,又匯入大海,我投入茫茫的大海中……也就在這里,她告訴她的寫作方法,至少準備兩個大日記本,出差也帶著,每天把自己的所見所聞都記下來,積累多了,重新組織篩選,就成了一篇篇的好散文了……
這天,當我揣著滿滿的“收獲”走出商場,已經是暮色四合、萬家燈火了。
不久,我買了一批外國名著,如饑似渴地讀起來。也許受茨威格心理小說影響,我寫的一篇散文《往事樣板戲》,她看后驚喜萬分,不容分說,馬上拿給主編看,說這篇稿子好得不用改了。可主編是個逆向思維的人,別人說不用改,他偏要改,不過,經主編的手改過的稿子的確很好,每次編散文集她總向我要這篇稿子。
可以說,她對我的幫助是全方位的,什么事情她總是幫我想在前面。
1996年,文聯要舉辦第一屆文學藝術大獎賽,這是大慶有史以來文學藝術界的第一次大賽事,參賽報名的人很多。可我卻沒報,我覺得自己這個無名小輩,哪能和獲獎沾邊呢!在報名截止的前一天,她突然找到我,問我報沒報,我如實說了我的想法。她一副恨鐵不成鋼的樣子,說,你不報名誰會知道你,即使評不上,大家也會對你有印象啊!在她的催促下,我膽戰心驚地報了名。評委們看到了我發表的作品都很驚訝,一位文學界的領導感慨地說,想不到張科還發表過這么多作品呢!
90年代中期,機關人員的工資與職稱掛了鉤,大家這才感到職稱的重要。在評定職稱時期,一群人蜂擁而上,搶那么幾個少得可憐的指標。領導無奈,想出了不是辦法的辦法,讓領導和副高職稱以上的人員投票選舉。在錯綜復雜的人際關系面前,我是個弱者。我沒有任何根基,更沒有領導的呵護,我就像沙灘上陽光下暴曬的一條小魚,孤立無援。我的個性使我沒向任何人張口求情,包括我的好朋友——她。可她卻在關鍵時刻堅定地投了我一票,這一票也許沒有用,可卻說明了她待朋友的真誠。她理直氣壯地說,這是我做人的原則。
她是理性的、嚴謹的,對事物的評價是客觀的,包括她的文學作品都是理性的、深刻的,無不閃爍著智慧的光輝。
她處事從不張揚,很低調,但在不經意間她就會冒出一本書,一本具有一定文學價值的書。她把她的情感和孤獨流露在字里行間,傾訴在文學作品里。
她對事業的追求,從不亞于男人,她沒有女人的瑣碎,不為閑事羈絆,她是大氣的,她的胸襟像大海一樣的遼闊。她的目標只有一個,把文章寫好。她常說,一個人要學會說“不”,一生做好一件事足矣。
十多年了,除了她出差,我們常常相聚在一起。辦公室里、林蔭路上、公園里、大小商場里,到處都有我們的身影和足跡。我們在一起談天說地、談男人和女人,和她在一起是快樂和輕松的,還會使你變得聰明起來……
如今,她去了南方一個美麗的城市,在一個鮮花盛開的地方,與她心愛的人,過著幸福而平靜的生活。我在為她慶幸、為她祝福的同時,常常會感到孤獨和憂傷。我經常眼含淚水,目視南方,心里輕輕地呼喚著她,我的親密女友,一個我生命中至關重要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