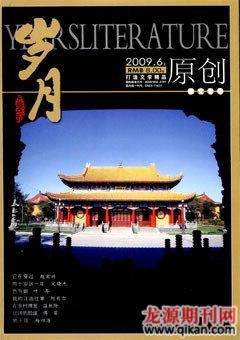關在電梯里的人
李 汀
我平生第一次坐電梯,是在外地一個人聲嘈雜的城市。
那天,我進入那座大樓的時候,我沒有看見電梯。我對電梯有一種天生的恐懼感。小時候,我最愛在農村的木樓梯上爬上爬下,跟現在城里孩子總愛在滑梯上爬上爬下一樣。可是,農村的木樓梯沒有護欄,一次,我爬上去的時候,可能是一絲風,也可能是窗外一朵花開的聲音驚動了我,我從木樓梯上落到地面,摔得我灰頭灰臉,啃了好多的土泥巴。至此,我對樓梯有了一種恐懼。許多時候,在城市我都是選擇爬樓梯,而不乘電梯上樓。這天,我照例沒有去找電梯,準備直接走樓梯上樓。可是,站在樓梯口的女服務員熱情地用手指示:“先生,電梯在那邊!”聲音很甜,我不由看了看她的笑容,那種固定的笑容。我不好拒絕,再說她已經替我按了上樓的電梯。我站在電梯旁,看著電梯顯示的樓層。女服務員站在我身旁,等待我進電梯。
電梯門開了,女服務員很優雅地請我進了電梯。我再次看見了她的笑容,那種花兒一樣的笑容。電梯門一點點關上,她的笑容也一點點變窄,電梯把她的笑容一點點擠碎,最后消失在了電梯外。我站在電梯里,聽著電流聲,看著閃爍的紅色樓層數字。1、2、3……數字在一個個增加,樓層在一層層變化。我的住處在12層。猛地。“哐啷”一聲,電梯停了。數字停在了6,我想樓層也該是6層。停電了,隨之而來的是漆黑一團,先前看見的紅色數字,一晃成為了一團黑。猛地,剛才進電梯的笑容,紅色翻轉的數字,以及美麗的花兒,涌成漆黑一團,把我震呆了。我停在了半空中,進不得進,退不得退。我用手掩護了一下我張大的嘴巴,雖然黑暗看不見,可我感受到了嘴巴已經夸張地張大。就在這時候,我的手,感受到了自己急促的呼吸。很快,我就聽見外面的嘈雜聲,罵娘的聲音。我沒有發聲,我怕我的聲音一下子把電梯震塌了,一下子把我摔在地下,就像小時候從木樓梯上摔到地下。我始終沒有出聲,我在等待電流聲響起。那希望的聲音。
我身邊沒有同伴,沒有同我一起上樓的同伴,獨個兒。只有一個挎包。
我想,總要來電的,電梯還會上上下下跑動。于是,我摸了摸我挎包里的幾疊紙。那上面有我流動的文字,有我的思想。摸著一張紙的時候,我心里踏實了許多。那紙有著羊皮一樣柔軟的質地,有著青草一樣的氣息。
隨后,我又摸到了一支筆,那支陪我說了好多話的筆,它最了解我的心思。此刻,它也了解我的想法,我要說的話,它都替我表達。這支筆陪我好多年了,下鄉,開會我都捏著它。有時候,我也咬咬筆頭,讓它知道我的苦悶。
隨后,我又摸到了一串鑰匙。哦,哪把鑰匙開哪把鎖。這把是家里那把鑰匙,開了四五年了,一扇木門,這是我進出最多的一道門。進門是一幅抽象畫:騎自行車的小伙子,和一個紅蘋果。那個布沙發上擺了許多的書,躺在沙發上隨手可以讀一段溫馨的文字。這把是辦公室的那把鑰匙,一扇鐵門,比家里的門結實多了,打開就是一張辦公桌,桌上啥也沒有,幾張文件躺在上面,沒有生機。倒是辦公桌靠窗,有時候,陽光照進來,讓人感覺生活的許多亮色。我知道,生活中需要某些東西的滋潤,陽光當然不可少了。這把是那個小抽屜的鑰匙,打開會看見那個紅色日記本,那上面我記了好多的日記,天晴天陰,會真實記錄在上面,那是我心靈深處的東西。這是我心靈的一把鑰匙了。這把是放在門外的那輛自行車鑰匙,許多時候,我會“哐啷”一聲打開自行車鎖,騎著自行車去山路上轉悠,當然,那是一輛飛翔的自行車,它載過我的戀人,在土路上飛翔,飛翔。許多時候,她純銀一樣的聲音與我的自行車一起飛翔,在那寂寞的山河間飄蕩回響。這把是父母家里那扇門的鑰匙,我一打開門就能觸到父母的一些氣息,那種家的感覺。其實,我很少回去,也很少打開那扇門。但我知道,那扇門永遠為我敞開著。我回去,母親會高興地拉我進門。
隨后,我又摸到了一張紙。我想把它抽出來,可紙像一把鋒利的小刀一樣把我的手指劃傷。手指有一點點的隱痛,黑暗使我渾身的血一個勁往外涌,在沒有找到出口的時候,終于找到了一個可以奔涌的出口。我用另一個手指,摸了摸受傷的手指,濕漉漉的,血的腥味充滿了小小的電梯空間。我用手指按住出血口。我仍然沒有出聲,我在等待。我在心里說,我不怕等待,哪怕很長很長。
隨后,我聽見女服務員甜甜的聲音響起:“先生,先生,不要緊張,我們正在搶修。”她的聲音有些急促,有些顫抖。她的聲音是貼著電梯縫飄進來的。我依然沒有出聲。她又說話了:“先生,先生,我們正在加緊搶修。”這次,她的語氣里充滿了堅定。我使勁點了點頭,雖然她看不見。我說:“幫我找一張創可貼吧。”她也好像獲救了一樣,激動地說:“好,好,你等著。”
隨后,我聽到她噔噔噔跑下樓的聲音。腳步急促,像她急促的呼吸一樣。這時候,我想到了一篇小說,關于電梯的:一男一女在電梯里相愛了,他們真希望這電梯一直不要停下來,就那么一直升上去,變成云梯更好。世間沒有桃花源,他們相信天上應該有。小說很動人,很激情。我一下子興奮起來,要是那個女服務員和我一起乘電梯上去,在那黑暗的一瞬間,我會不會愛上她?我不知道。但是,我希望電梯變成云梯倒是有可能的,就那么一直升到天空去。
隨后,電梯“哐啷”一聲啟動了,我又看見了跳動的紅色數字,我又聽見了電流的聲音。這時候,我從光潔的電梯平面上看見了落魄的自己。劃傷的手指已經沒有再流血。
12樓到了,電梯停在了12層。我整了整衣衫,走出了電梯。女服務員站在電梯口迎我。我嚇了一跳。同時,也為剛才那點可笑的想法。女服務員溫柔地向我點點頭,我點了一下頭,逃也似地走了。女服務員在身后甜甜地喊:“先生,你的創可貼。”我站在那里,她已經把創可貼遞到了我的手上。“先生,剛才嚇著了嗎?”
我笑笑,可能很難看,但還是不緊不慢地說:“一個夢而已。”
是啊!一個夢。也是一個等待,就像詩人嚴力寫的一樣:甚至像觀光客一樣,在自己的體內等待電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