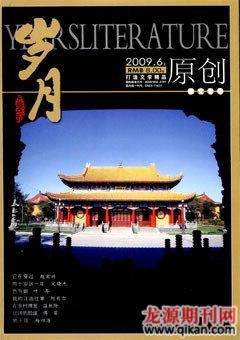心靈的歷程
王靈均
第一次讀到趙宏興的散文《它在穿過——記一次旅行》,頗感詫異。與這位作家接觸雖然不多,還是可以感覺到現實生活中的趙宏興是位爽朗、豁達的人,待人接物總是那么熱情誠懇、彬彬有禮;以前讀過他的散文集《岸邊與案邊》,書中多數作品是敘述性的散文,而《它在穿過——記一次旅行》則為之一變。
趙宏興是一位嚴肅的作家,在《它在穿過——記一次旅行》中,他沒有在具體的火車行程上面展開,而是重點放到自己的內心感受,多采用寓意、象征、變形、自白等手法,基調沉重、文字多義性指向明顯,作品中的“我”也是一個象征化、符號化的意象,可以視為現代人的心靈化身。作品中的火車旅行可以看作人的生命歷程,著力描繪的夜景可以看作擠壓現代人生活空間的社會環境。所有的這些意象描寫,都指向了一個主題:現代社會人類的生存狀態和生活意義。
霍克海默和阿多諾合著的《啟蒙的辯證法》一書指出,進入近代社會以后,知識代替了神話和幻想,把人從中世紀的神學迷信中解放出來,要求從實際上支配自然。它借助于科學知識把事物的整體分解為可以精確計算的要素。與此同時,形式邏輯的發展又為人們提供了計算事物的邏輯格式和進行推理思維的可能性;數學也成了啟蒙的準則,把一切都還原為數。于是,啟蒙精神就以事物的同一性消滅了多種多樣的個性,導致了思維的程式化。數學和邏輯通過科學技術成了人類肢解自然、統治自然的有力工具。但是,啟蒙精神的發展一方面擴大了人對自然的統治,另一方面它也成了奴役人的枷鎖。“文明的發展是在絞刑酷吏的記號下發生的”,“恐怖是和文明分不開的”,科學技術作為啟蒙精神的“物化”,既是人類征服自然的力量,也是一些人奴役另一些人的有力手段。特別是在現代社會,商品拜物教的影響已擴展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人們總是以失去自己的人格自由為代價而獲得文明進步。人類智慧所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最終都變成統治人的異己力量。這對于現代社會人類的異化生活做出了哲學和社會學的闡釋。趙宏興的散文則是對于這一理念的藝術闡釋。
作品只是點名在秋天的旅行,沒有具體時間和地點,也沒有說明旅行的目的,這種缺乏具象的描寫,增強了散文的象征意義,它和充滿著罪惡,謊言,欺詐,惡心的黑夜、火車一起構成一幅荒誕、冗長的畫面。
在文章里,作者很少寫白天,即使提到白天、陽光,也沒有輕松的筆調。“清晨的田野上,飄浮著淡淡的霧氣,有著舞臺上剛要揭開還沒有揭開序幕的樣子。田埂上,到處是被焚燒過的痕跡,黑色的灰燼,一塊塊地,傷疤似的留在地面上”,“太陽的光線是垂直的,深淵的四壁長滿了奇怪的樹木,巖石上的石縫里嵌著古老的時間。這一段時間,應該是黑色的,即使陽光透徹,也是這樣的,眼睛看不透的時間,掩蓋著真實”,可以說,黑夜構成了這篇散文的第一意象,漫漫長夜,充滿了怪誕、詭異,又是那么沉悶乏味,它是如此的頑固,“窗外閃過一片燈光。燈光下是空蕩的,不見一個人影,堆積的光亮被黑暗擠壓成堅硬的一團”,“黑暗連著黑暗,黑暗套著黑暗,喪失了記憶的旅程,在宇宙中膨脹,距離變形成一桶方便面,快捷但沒有營養,飄著一股廉價的味道”,這些晦澀的句子背后我們仿佛聽到現代文明重壓下的整個人類疲憊的喘息聲和無奈的嘆息聲。
李白在《春夜宴桃李園序》說過:“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李白把天地看成萬物的旅店,把時間當作歷史長河的旅客,可以為趙宏興的散文做一生動注腳。趙宏興的這篇散文著力描寫的火車旅程實際上是人生旅程更是心靈旅程的形象化比喻。
“乘務員過來讓我寫旅客意見,年輕的服務員,有著一雙美麗的眼睛,剛剛過去的黑夜就消失在她黑色的眸子里。我問,這火車的吱扭聲是怎么回事?她說,這不是火車問題,是這段路的路基不好。
這就奇怪了,我懷疑我的靈魂是否奔赴在一段危險的旅程上;或者說,這一段旅程還沒有維修好,我的靈魂就開始了一場奔赴。
這個‘路字,是對我的喚醒嗎?
我抬起身來,想看看為什么會有這個‘路字,這時,我才看到了完整的句子:‘中國鐵路”。
本段描寫堪稱生花妙筆,正是現代社會人類精神危機的形象寫照,被后工業文明異化統治的人類社會就像行駛在不牢固的路基上的火車。如同尼采說的“上帝死了”的命題,喪失了心靈家園的人類將如何前進。在這種形勢下,“我”,這一人物、這一意象,可以說是濃縮了人類心靈的意象。
“我提著碩大的旅行包
——它的腹內鼓脹著,它是母性的,當我把那些小日用品一件一件地往里面裝時,它就受孕了,它孕育了我整個游蕩的夢。
但隨后它的重量會慢慢地減輕,它變得空空的時候,便誕下了我的靈魂——那是旅程的盡頭。
逃走——
我在沿著空間的邊緣逃走,我的雙手用力推開這鋼鐵的門扉,慌亂的腳步必須輕輕起來,不要驚動守衛的士兵。這轟隆的聲音,是門扉打開的聲音。
我的身體被禁錮得太久了,肌肉里剩下的最后一點力量,用來尋找自由、幸福、未來……”
這是現代人類的自我救贖和反抗,這是對于異化社會的控訴和抗爭。雖然作品中也出現了警察、乘務員、乘客、民工、美女等人物形象,但是都難以具象化,都是“我”的感受到的富有象征性的意象。這是生命的路程,心靈的旅程。
尋找精神家園的旅程不僅是漫長的,更是孤獨的,痛苦的。
“火車在土地上面奔馳,隆隆的聲音之后,土地又歸于一片沉寂。
沒有人關注這列火車,因為我的存在,這列火車載著的是我一個人。
它在奔馳,它沒有雙腿被束縛時的局促。”
前面說過,作品中出現的警察、乘務員、乘客、民工、美女等人物形象,都難以具象化,與散文中的“我”沒有任何實質性的心靈交流,如此種種突出了現代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隔膜、缺乏心靈的溝通,現實中本來擁擠嘈雜的火車幾乎就“我”一個乘客。與尤涅斯庫的《禿頭歌女》中那兩位感情淡漠到如同陌生人一樣的夫婦的形象有異曲同工之妙。
“山洞,這短暫的黑暗,一個連著一個。
這些洞窟不能久留,必須快速地穿過。
時光在黑暗中凝固,在陽光中融化。
瞬間的黑暗,瞬間的光明。
火車帶著撕裂般的疼痛,一路奔馳,突破。”
人類千百年來的文明就是如同這火車一樣夾雜著光明和黑暗,帶著累累傷痕悲壯地前行,誰也無法知道前面的黑夜意味著什么結局。
真正的心靈探索更是那么可望而不可及。
“我對自己說,這是一個漫長的旅程,火車將載著我橫穿幾個白天和夜晚。——我要去的地方,是一個陌生的地方,時間將像養肥了的豬,被屠殺并發出絕望的嚎叫。——那里沒有多少人到達,但卻是真實的,而我所到達過的地方都是虛擬的。”
現實生活是紛繁蕪雜、真假并陳,只有精神生活是深刻的、真實的,可是被現代文明遮蔽了靈魂的現代人類又有幾人可以進行這種心靈的探詢呢?可以說,“我”這一意象不僅濃縮了現代人的精神世界,更是那種反抗異化社會的知識精英的代表。
阿多諾提出在現代異化社會中知識分子應當在“先鋒派藝術”的審美烏托邦中實現審美救贖,這最終將流于虛幻和脫離實際。趙宏興的心路歷程雖然缺乏一個完滿的結尾,但是最后還是變得有些光明之處。剛說到:
“這是秋天了,冷空氣在北方聚集。
一場火焰會在指尖到達,掐滅的黑暗會重新到來,布滿身后空隙。”
可是隨著民工的下車,車廂也空敞了,作者的筆調也輕松起來了。
“這是一渠洪水,在兩岸間的河谷里流動。
它的奔流像無數大提琴、小提琴、爵士鼓、長號在演奏,奔放,自由,激烈。
我是隨波逐流的一條小魚,在洪大的水流中翻騰,跳躍,游動。
時間的沙灘是白色的,是每次洪流從高處攜帶下來的心靈的積淀。
它越往前走,地勢越平坦,但內里的力量仍沒有減弱。
它推涌著我,這個游蕩的靈魂。
火車奔跑的腳步踏在這秋后的盛典里。
邊緣被它一次次拋在身后,
它要奔跑,它停止不下來,在激烈的鏗鏘聲里。
火車離終點越來越近了,這是最后的晚餐。
也是重新開始。”
應當說民工下車這段內容相對于前面的旅程的描寫現實色彩要濃厚一些。是的,人總歸要回到現實之中,但是這種回到現實是經歷了痛苦、孤獨的心路歷程之后的基礎上的回歸,較之艱難的心靈跋涉之前更加深沉、自信,這一深沉、自信似乎看起來有些突然,可確實是經歷了靈魂煎熬和拷問之后的當下直覺和真實呈現,盡管還沒有到達終點,但是“離終點越來越近了,這是最后的晚餐”,“也是重新開始”。
人類的生命歷程還要走下去,不過步伐更穩健、果毅了,雖然前方不知道還有什么艱險,終歸還要邁步走過去。我相信讀完《它在穿過——記一次旅行》后的人,會有類似的信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