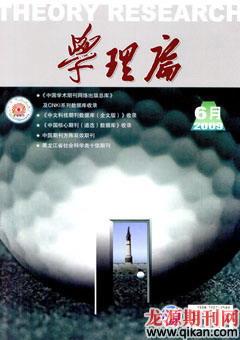非國有單位委派人員非法占有財物行為的司法認定
曾 軍,師亮亮
摘要:非國有單位委派人員為其他單位從事工作的情形日趨增多。委派人員在工作過程中,非法占有財物的行為,可能構成盜竊罪、職務侵占罪和侵占罪。在具體認定委派人員非法占有財物行為的性質時,應當根據“財物占有的歸屬”、“委派人員的權限”和“契約內容”等方面綜合分析。
關鍵詞:委派人員;財物占有的歸屬;權限;契約內容
中圖分類號:D918.95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09)14—0089—02
一、問題的提出
重慶某超市是上海某食品公司(非國有單位)的奶粉經銷商,陳某系該食品公司的員工。根據雙方協議,食品公司委派陳某到超市從事奶粉促銷工作。陳某在超市從事促銷工作期間,對所促銷奶粉采取違規贈送、私下買賣等方式,造成超市損失40余萬元,其中陳某私下買賣的奶粉價值3萬余元,私下買賣所得均為陳某非法占有。關于陳某的行為是構成盜竊罪,還是職務侵占罪,爭議較大。
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和社會分工的逐步精細,在我國的社會生活中,由非國有單位委派人員為其他單位從事某項工作的情形也日趨增多。許多單位不再專門聘用人員從事某項工作,而是通過與其他單位簽訂協議等方式,由其他單位委派該單位的人員到本單位來從事某項工作。例如,許多單位的衛生和保衛工作,就是由專門的保潔公司和保安公司委派的人員完成的。委派人員在工作過程中,非法占有財物的行為,是構成盜竊罪,還是職務侵占罪,抑或侵占罪,不能一概而論,而應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具體而言,應當根據“財物占有的歸屬”、“委派人員的權限”和“契約內容”三個因素來認定委派人員非法占有財物行為的性質。
二、財物占有的歸屬
所謂財物占有的歸屬,就是財物的占有屬于誰的問題。①財物占有的歸屬,是認定委派人員非法占有財物行為的基本標準,也是盜竊罪與職務侵占罪(包括侵占罪)的區別所在。從刑法規定看,盜竊罪法的定刑之所以比職務侵占罪(包括侵占罪)重,是因為盜竊罪是對他人占有的積極侵犯,而職務侵占罪(包括侵占罪)則是對本人占有的濫用。也就是說,當財物的占有不屬于委派人時,委派人非法占有財物的行為應當認定為盜竊罪。反之,當財物的占有屬于委派人時,委派人非法占有財物的行為則應當認定為職務侵占罪或侵占罪。
按照刑法通則說,判斷占有的歸屬應當從主觀和客觀兩方面來展開。具體而言,主觀方面要求占有人有占有的意思。所謂占有意思,就是占有人意識到自己正在占有某物。客觀方面要求占有人實際支配或控制某物。這里的支配或控制,不僅包括物理上的支配或控制,還包括規范上的支配或控制。②例如,甲公司的員工A被委派至乙公司從事保潔工作,A在從事保潔工作過程中,將乙公司的產品非法占為己有的行為,應當認定為盜竊罪。從占有的主觀方面分析,乙公司當然意識到自己正在占有本公司的產品;從占有的客觀方面分析,無論是基于物理角度,還是基于規范角度,乙公司都對其產品具有實際的支配或控制。因此,A的非法占有行為,侵犯的是乙公司的占有權,而不是對自己占有權的濫用,構成盜竊罪。
三、委派人員的權限
根據占有歸屬的判斷標準,委派人員在工作過程中,僅僅是可以接觸到財物,或是可以經手財物,而未能對財物實際支配或控制的,不能認為財物的占有屬于委派人員。財物的占有是否歸屬于委派人,委派人是否對財物有實際的支配或控制,應當從委派人員的權限來分析。也就是說,委派人員對財物支配力或控制力的強弱是與委派人員的權限大小成正比例關系的。委派人員對財物的權限越大,則說明委派人員對財物的支配力或控制力越強,反之亦然。當委派人員對財物不具有權限時,則說明委派人員對財物無支配力或控制力。當委派人員對財物不具有權限或權限未達到可以實際支配或控制財物的程度時,委派人員非法占有財物的行為,應當認定為盜竊罪。反之,委派人員非法占有財物的行為,應當認定為職務侵占罪。
關于委派人員的權限大小,應當從兩個方面來綜合認定。一是雙方單位關于委派人員權限的約定;二是委派單位對委派人員的信賴程度。當雙方單位未約定委派人員對財物的權限或約定的權限僅是委派人員可接觸或經手財物,而不能對財物實際支配或控制的,即便委派單位對其委派人員的信賴程度再高,也不能認為委派人員可對財物實際支配或控制。據此,本文開頭提及的案例中,陳某的行為應當構成盜竊罪。因為,根據超市與食品公司的協議,陳某作為奶粉促銷員,盡管可以接觸和經手奶粉,但雙方的協議并未賦予陳某實際支配或控制奶粉的權限,此時,奶粉的占有歸屬于超市,而不是陳某。因此,陳某非法占有奶粉的行為實質上是對超市奶粉占有權的侵犯,而不存在對自己占有權的濫用。根據對他人占有權的侵犯和本人占有權濫用的本質區別,陳某的行為應當構成盜竊罪,而不是職務侵占罪。
當雙方單位約定委派人員可對財物實際支配或控制,但委派單位對委派人員信賴程度較低的,也不能認為該委派人員可實際支配或控制財物。例如,甲公司與乙公司約定,委派人員可對乙公司財物實際支配或控制,但甲公司基于其內部的信賴關系,只賦予該公司的委派人員A對乙公司財物的實際支配或控制權,而對該公司的委派人員B則未賦予該項權限。那么,委派人員B非法占有乙公司財物的行為構成盜竊罪,而A非法占有乙公司財物的行為則構成職務侵占罪。A與B共同非法占有乙公司財物的,當共同非法占有行為利用A的權限時,則A與B共同構成職務侵占罪;當非法共同占有行為未利用A的權限時,則A與B共同構成盜竊罪。
需要注意的是,在對委派人員非法占有行為進行認定時,不能對職務侵占罪構成要件中的“本單位財物”作機械的解釋。如果對“本單位財物”作機械的字面解釋,則委派人員非法占有財物的行為,應一概認定為盜竊罪,而不會存在認定為職務侵占罪的可能。如前所述,盜竊罪的法定刑重于職務侵占罪,是因為盜竊罪侵犯的是財物的占有,而職務侵占則是對財物占有的濫用。在委派人員對財物實際支配或控制而濫用財物占有權的場合,將其認定為盜竊罪,則會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罪刑失衡。實際情況是,盡管財物不屬于委派人員所屬單位,但基于委派單位與被委派單位之間的契約約定的權限以及委派單位與委派人員的信賴關系,在委派人員對被委派單位的財物可實際支配或控制的情況下,按照權利義務對等原則,委派單位對被委派單位的經委派人員支配或控制的財物,也應承擔一定的擔保義務。基于委派單位的這種擔保義務以及委派單位與委派人員的信賴關系,與其說委派人員支配或控制的是被委派單位的財物,還不如說委派人員支配或控制的財物就是委派單位的財物。而且,委派人員支配或控制被委派單位財物的行為,從根本上看,是在對委派單位履行職責,而不是對被委派單位履行職責。因此,在委派人員基于支配或控制被委派單位財物的權限而非法占有被委派單位財物的場合,應當對“本單位財物”作適當的擴大解釋,認定其構成職務侵占罪,而不是盜竊罪。
而且,在實踐中,也存在委派人員支配或控制的財產屬于委派單位與被委派單位共同所有的情形。如果將“本單位財物”作機械的解釋,那么,委派人員的一個非占有財物的行為,就會因財物的共有性質,而部分構成職務侵占罪,部分構成盜竊罪。當財物共有的性質為按份共有時,如果嚴格按照比例區分“本單位財物”與“外單位財物”,則可能會出現委派人員非法占有財物的行為既不構成職務侵占罪,也不構成盜竊罪,從而不構成犯罪的情形。例如,委派人員A利用職務之便,在被委派單位從事工作期間,將委派單位與被委派單位按份共有的價值5000元的財物非法占有,如果委派單位與被委派單位對該財物的所有權份額分別為95%和5%,那么嚴格按照“本單位的財物”進行區分的話,則委派人員A職務侵占“本單位財物”4750元,盜竊“外單位財物”250元,可見無論是職務罪,還是盜竊罪,A的行為均未達到成立犯罪的標準。
四、契約內容
一般情況下,根據“財物占有的歸屬”和“委派人員的權限”即可認定委派人員非法占有財物行為的性質。但在某些特殊情況下,委派單位與被委派單位的契約內容,也是影響認定委派人員非法占有財物行為性質的一個重要因素。例如,甲乙兩公司約定,乙公司將某大型設備租給甲公司,但由于該大型設備不易搬移,故甲公司委派A到乙公司的所在地對該設備進行經營管理。盡管該大型設備還處在乙公司所在地的范圍之內,但基于甲乙兩公司的約定,該大型設備在法律上已屬于甲公司占有。在這種情況下,委派人員A非法占有該設備上價值較高的零件的行為應當如何認定則比較復雜。根據具體情形,A的行為可分別認定為盜竊罪、職務侵占罪和侵占罪。
由于該大型設備的占有在法律上已屬于甲公司,根據甲公司與委派人員A的信賴關系,當A具有可支配或控制該大型設備的權限時,A非法占有零件的行為,實質是濫用了其占有權,應當構成職務侵占罪,侵占的對象為本單位甲公司的財物;當A不具有支配或控制該大型設備的權限時,A非法占有零件的行為,侵犯了甲公司的占有權,應當構成盜竊罪,盜竊的對象為本單位的財物。
需要注意的是,當委派人員A根據甲公司的授意,在租賃期限屆滿后,仍非法占有該大型設備的零件,經乙公司要求,拒不退還的,委派人員A的行為可能構成侵占罪。按照甲乙兩公司的契約約定,在租賃期限內,乙公司的大型設備應為甲公司代為保管,當租賃期限屆滿,乙公司有權要求甲公司返還該大型設備。由于單位不是刑法規定的侵占罪主體,因此,甲公司拒不退還乙公司零件的行為不構成侵占罪,但是在這種情形下,并不排除自然人構成侵占罪的情況。如果是甲公司的主管人員授意A完成上述行為的,則甲公司的主管人員構成侵占罪,A是否構成侵占罪也要具體分析。如果A本身就是甲公司的主管人員,A自己決意拒不退還乙公司零件的行為,A單獨構成侵占罪;如果A是甲公司的主管人員,經與甲公司其他主管人員合謀,拒不退還乙公司零件的行為,A與甲公司的其他主管人員共同構成侵占罪;如果A只是甲公司的普通員工,A拒不退還乙公司零件的行為,是基于甲公司主管人員的命令而完成的,此時,根據期待可能性理論,甲公司主管人員的命令行為構成侵占罪,而A的行為不構成犯罪。
注釋:
①②黎宏:“論財產犯中的占有”,載于《中國法學》2009第1期,第115、112~113頁。
(責任編輯/王麗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