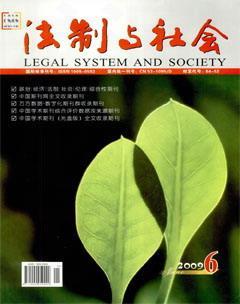論魏晉時代的美學(xué)風(fēng)氣及其社會背景
魏 飛 方晨曦
摘要“人生到此,天道寧哉!”除了黑暗,確實不好有別的色彩來描述魏晉的歲月。然而恰恰是在這黑暗之中,崇尚清談思辨的玄學(xué)蔚然成風(fēng)。也許是為了逃避現(xiàn)實和養(yǎng)尊處優(yōu),但這中國哲學(xué)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并能夠引起不少對美學(xué)和人生、社會等問題的思考。
關(guān)鍵詞魏晉玄學(xué)社會美學(xué)風(fēng)氣
中圖分類號:B83文獻(xiàn)標(biāo)識碼:A文章編號:1009-0592(2009)06-244-01
一、焦尾與無弦——有和無的美學(xué)判斷
漢末紛亂,蔡邕卻有心情從火中救出良木,成就焦尾之琴,好讓自己在琴聲中暫時忘卻世事的艱辛和窒息。時至東晉,陶潛彈操起無弦的樂器。雖然無弦無聲,自得其樂卻不亞于前代,甚至與天地已然渾然一體。
燒飯用的柴火是實用的,恰恰是在其日常的使用價值之外,蔡邕賦予這段幸運的桐木以審美的價值。美是超脫功利的,而發(fā)現(xiàn)美麗的眼睛也必然會將焦點放在超越上。誠然,對音樂的修養(yǎng)使他能夠知道何種木材可以成就完美的樂器,但在純技術(shù)性的修養(yǎng)之外,如果沒有擺脫的功利的眼光,是不可能去火中搶救一段桐木的。此時的蔡邕搶救的是一個即將離去的美麗。在美面前,人可以忘卻火燒的疼痛而奮不顧身,這是對美的執(zhí)著。然而執(zhí)著與現(xiàn)實交鋒時,它卻往往導(dǎo)致悲慘的結(jié)局,這樣結(jié)局下的人生是凄美的。
陶潛的無弦琴則是另一種美麗了。它對美麗的發(fā)現(xiàn)像焦尾琴般并不追求完美的外表,甚至它忘卻掉藝術(shù)的存在。無弦琴是一個沒有格式的美,也正是這沒有格式使其沒有了羈絆,可以自由的在想象中馳騁縱橫。無弦琴沒有殘缺,它不是一個扣人心弦的悲劇;它亦不是完美,因為它深切的知曉完美只是個遙不可及的神話。
焦尾琴是浴火重生的火鳳凰,無弦琴是藐姑射之山的綽約仙子。焦尾琴代表了犧牲與追求永恒的士人精神,無弦琴則是隱逸之人的心靈寄托。犧牲的美麗是殘缺的,其人生是拯救與壯麗的;隱逸的美麗則是逍遙的,其人生是自然與優(yōu)美的。然而焦尾也罷,無弦也好,人生對美的追求正是在這兩者之間不斷地徘徊。久而久之,在廟堂與竹林之間便有了一條彎折曲延的小路。
二、廟堂與竹林——功利與純粹之美的選擇
曹植的七步詩總能讓人潸然落淚。他道出廟堂之險惡,權(quán)利紛爭,疑心重重,使得兄弟相殘,骨肉反目。可即便如此,廟堂卻仍是一個充滿誘惑之美的地方。無論是君主還是臣仆,雖時刻都有丟掉性命的擔(dān)憂,卻始終對權(quán)謀的游戲樂此不疲。
無論何種時代,年少的心總是希望能夠成就一番事業(yè)。所謂“棄身鋒刃端。性命安可懷”,曹植的另一首詩正是如此的張揚(yáng)輕狂。真正的鋒刃不在匈奴鮮卑,而在于失去綱常倫理的人心。
從高高的廟堂走下,曹植失意地流浪在洛水之濱。他也許在想,屈原那飛濺的水花正是反抗黑暗的至美。可魏晉距離戰(zhàn)國已然遙遠(yuǎn),子建不同于三閭大夫在失意遭遇衰老的漁夫,他可以望見一個美人。她的美是動人心魄的。她不摻雜胭脂的粉飾,不追捧金玉的雕琢,只是默默地將自然流露。所謂“秾纖得中,修短合度”,她是一個平衡的美。于是曹植所勾勒的她,正是心中寄托的完美。這完美中沒有骨肉相殘,沒有爾虞我詐,然而世事艱辛,他的人生不得不與這完美的洛神擦肩而去。這樣看來,他骨子里與屈原還是一樣的。所謂完美僅僅是桃園之境、竹林之地。
曹植不是竹林七賢,他的洛神只是靈光乍現(xiàn)。因為他有著無法割舍的廟堂情懷。竹林的美的確動人心魄,可把美當(dāng)做人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這需要太大的勇氣。《老子》有曰:“勇于敢則殺,勇于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勇氣在人生的不同時刻扮演著不同的角色。生活于竹林之中的勇氣也是如此,此時的勇氣不是與黑暗針鋒相對,而是在黑暗面前我行我素。所謂“圣人之道,為而不爭”即是此意。廟堂的人生當(dāng)有著每日三省其身的覺悟和勞神苦思的付出。而付出是辛苦的,是來不得半點疏漏的,也是被他人所尊重的。于是,人們把敬意授予有所付出的英雄們,使其榮耀如繁星璀璨,而人類的歷史就是熠熠生輝的星空。
然而,我們所見的星空只是宇宙的某個角落,英雄們的崇高感在歲月面前有些黯淡,在光輝背后則是英雄們獨自品嘗的孤獨。孤獨激活靈感,靈感孕育詩人。這類詩人是幸運的,他們把廟堂和竹林融合到歲月之中。
三、歲月與朝露——魏晉美學(xué)所體現(xiàn)的時代主題與永恒價值
藝術(shù)品有其所屬的時代,但其承載的美則是超越時代的。人亦被時代所局限,個體的人只能生活在屬于自己的空間內(nèi);但人是不甘于局限的,其心靈可以與過去未來的一切美麗相互交融。
魏晉士人多愛寄情山水,并取其人生短促,山水常在之意。人在崇山峻嶺之間尋覓著永恒,放佛在對自然的審美之中人生得到了不朽。然而,人生畢竟是短促的,不朽只是一個無何有之鄉(xiāng)般的夢幻。王羲之感慨自己與古人同覺到“死生亦大矣”的痛苦。并且也清醒地知道后人思考起歲月的問題時,也會如他那般。所謂“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致一不二,滄桑的美感油然而生。
歲月如江水,江水拍岸,不經(jīng)意間就把腳印從江灘上抹去。然而人類畢竟是不甘于局限的,后來的人們依舊會踩在江灘之上,留下一排新的足跡。雖然越往后的人越明白足跡會被沖刷的事實,但如同西西里斯的寓言,人類正是在這反反復(fù)復(fù)的循環(huán)往復(fù)中實現(xiàn)著超越。這超越首先是審美的,是不計功利的。
人生仿佛一出悲劇,在有限的歲月中無論是逍遙竹林還是勞頓廟堂,都逃不脫自然的法則。天地又是無情的,天不為人之惡寒也輟冬,地不為人之惡遼遠(yuǎn)也輟廣,然而人類并不會因此而退出悲劇的舞臺。所謂君子不為小人之匈匈也輟行,亦不為天地之無情而輟生,因為人生的美麗正在于悲劇之中。
“對酒當(dāng)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江上,橫槊賦詩,將人生比作朝露。朝露的美在于其晶瑩剔透的純潔,更在于轉(zhuǎn)瞬即逝的珍貴。人生的美麗在于其心靈可以有超越形體的自由,更在于能夠通達(dá)歲月,穿越分別的能力。孟德雖有半壁天下,亦有感于人生如夢。但既然如夢,就把夢想完成。也正在這個角度看來,魏晉玄學(xué)表達(dá)了當(dāng)時士人對美與人生的態(tài)度。黑暗時代的人們尚不放棄對美與人生的積極追求,今人亦應(yīng)寫下濃墨重彩美的樂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