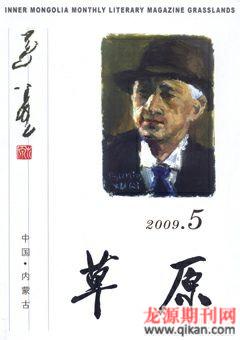我的寫字臺
宋生貴
我不知道“寫字臺”這個概念從何時起被普遍運用的,而我自己最早見識其物已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大學畢業之后。當時在我看來,它與早已叫熟了的書桌或辦公桌并無多大異處,只是換個名目而已。可后來我卻覺出“寫字臺”這個名稱的確切與親切之處,即名實相符,確指它主要是供寫字之用的平臺。這樣想來便認為自己其實與“寫字臺”結緣已久,且歷經多變但卻始終相隨相伴,故而感到親切。
我所說的我的“寫字臺”是指自家所有,不包括學校讀書時用的書桌和工作后所用單位的辦公桌。我用過的第一個“寫字臺”,是我家那間土窯內的小窗臺。這小窗臺是窗洞內側下的一段臺子。它用土坯砌成,再以紙精泥抹面,外沿鑲一條木板,高約盈尺,寬僅容書,與熱炕連為一體。從讀小學開始,這個小窗臺便成了我的寫字臺,因為那時家里沒有桌凳或其它更適合書寫的地方。每天放學回家,我便把課本、作業本等擺在小窗臺上,認真完成老師布置的每一份作業。因臺面窄小,書寫時書與本須斜著置放;因臺高所限,我常常是側身半跪的姿勢,但它已滿足了我學習的需要。我從來沒有小視過它,而是為擁有屋內這一光線最好的地方感到格外快樂。從最初的一筆一畫開始,數年間我在這小窗臺上寫過了許多字,包括小學四年級時發表在學校墻報上的一首兒歌式的小詩,也是在此寫出的。小窗臺——我的第一個“寫字臺”,助我邁上求學的第一個臺階,也供我進行了第一次運用文字的“創作”。
上初中后,我又換了一個“寫字臺”。因為這時我的個頭長高了,坐在小窗臺前曲腿彎腰都覺得很困難,況且書籍增多已無法擺放。這第二個“寫字臺”即是我家鍋臺邊的風箱板。那時家里用的是木制手拉風箱。風箱本身長近一米,寬不足一尺,架在其上的風箱板長寬均大于此,完全可以視為桌面。不過,這需要配有一個凳子。家里沒有現成的凳子,所以先找了一個樹根墩子坐著,不久媽媽特意請來本村一位木匠師傅做了一個凳子為我用。坐著合適的凳子,在平展展的風箱板上書寫,可以伸腿直腰,舒適極了!因為這風箱板畢竟是兼而用之,所以只有當不做飯時歸我做寫字臺用,實際上主要是晚飯之后。晚飯后父母在炕上休息,我便坐在風箱板前,借著火苗閃耀的油燈做功課,或閱讀一些借來的課外書籍,感到格外寧靜與愜意。
我讀高中時是離家寄宿,三年內只有假期用家里的“寫字臺”。高中畢業后我回到家鄉當上中學代課教師。這時,我產生了高漲的寫作熱情,但這不是自己工作職責中的正業,所以絕不在學校里輕舉妄動,而只有晚上在家里神思運翰。這樣,風箱板便繼續大派其用場。這時家鄉已通電照明。我坐在風箱板前思索或寫作,往往不覺便已進入深夜。父親或母親常常半夜醒來看我還在寫作或讀書,便關切地催我上炕睡覺。而我則感到那只屋頂上的燈亮著會影響父母入睡,心中不安,便動手自制了一盞臺燈放在風箱板上。熱情與淺薄相結合滋生著異乎尋常的沖動與膽量,我在這風箱板上寫過詩歌、小說、劇本,以及大量通訊報道。就在這一時期,我右手的中指的捉筆處磨出了硬硬的繭子。我把寫出的東西有選擇地寄往全國各地的報社與雜志社的編輯部,同時寄去了自己殷切的期盼與熱望,可是,除偶有少數得以發表之外,絕大多數如泥牛入海,杳無消息。但就是那變成了鉛字的極少數便給我以極大的鼓舞和信心,使我一直未曾擱筆。
一九七六年,我家買了一臺臥頭式縫紉機,平時不用時可以將機頭收回,工作臺即成為了光滑的平面。自此,我的寫作與讀書便由風箱板轉換到縫紉機上,這自然就成為了我的第三個“寫字臺”。這“寫字臺”一直用到七十年代末恢復高考之后我考上大學。其間,除了繼續熱情不減的創作外,考前的準備、特別是大量數學題的解答,都在此進行。
上述三個“寫字臺”均屬就地選擇,兼而用之,而真正擁有專供書寫與閱讀所用的寫字臺,則是一九八三年結婚成家之后的事。當時有幸分到單位里的一套46平方米的單元樓,我與愛人皆歡欣鼓舞,于是設法托親友找關系買到0.6立方米木料和幾張三合板,精打細算做家具。首先考慮的就是寫字臺(當時已興叫此名了),此外還有兩個書櫥,一張雙人床,一個衣柜,一個多用高低柜。樣式是我自己設計的。因考慮房子空間較小,且木料也并不充足,各樣家具都屬于小巧而實用型的。寫字臺長1.2米,寬60厘米,當時我已覺得很有氣派了。住進了新房,坐在可供自己專用的乳白色的寫字臺前,其心怡然,難以盡言。我在大學任教不需要坐班,講課以外的多數時間都在寫字臺前度過,讀書、寫作均我所樂,漸漸邁進了學術的門坎。這個寫字臺伴我在學業與創作的路途間攀行整整二十年,兩臂常接觸的臺面棱被明顯地磨成了凹型,這使我更加真切地明白了滴水穿石與柔能克剛的道理。
我家現在擺放的寫字臺是2002年搬家時新買的。新房子的面積增大并進行了較為講究的裝修裝飾,舊家具明顯與其不相適了,所以便將其全部送予了鄉下親戚。當時,我撫摩著留下自己手臂磨痕的寫字臺,心里很矛盾,確有一種告別益友的不忍與不舍。我家現在的寫字臺是歐式風格的,很寬大并顯得豪華,與室內裝修以及其它家具協調一致。寫字臺上配以漂亮的臺燈,還有舒適的旋轉椅。可是,真正的使用卻很少了。因為自我擔任行政事務工作以來,坐在自家寫字臺前的時間明顯減少,所以,這個講究的寫字臺更多的時候作為室內的裝飾而存在著。我曾多次因此而生出過莫可名狀的感慨。
我的“寫字臺”猶如我曾相識相交過的朋友,既相伴而行,又從一個方面印證我的經歷,且別具意味。回想這些經歷使我明白:書寫是需要寫字臺等必要的條件的,但是,如何書寫,以及書寫的投入與成果如何,關鍵還在書寫者自身,而并不在于寫字臺的大小或考究與否。
〔責任編輯 任 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