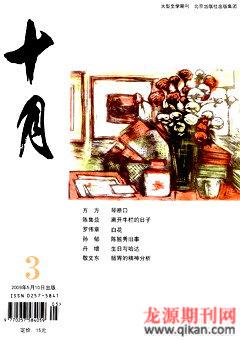陳獨秀舊事
2009-05-13 08:09:56孫郁
十月
2009年3期
孫 郁
1
時間在1917年,當陳獨秀應邀來北大的時候,敏感的錢玄同便在1月6日的日記中寫下了這樣一段話:
“陳獨秀已任文科學長矣,足慶得人,第陳君不久將往上海專辦新青年雜志及經營群益書社事業,至多不過擔任三月,頗聞陳君之后蔡君擬自兼文科學長,此亦可慰之事。”
此后的日記不斷有對陳獨秀的記載:
“日前獨秀謂我,近人中如吳趼人、李伯元二君,其文學價值實遠在吳摯甫之上。吾謂就文學美文之價值而言陳獨秀此論誠當矣。”(1917.1.23)
“檢閱獨秀所撰梅特尼廓甫之科學思想篇(新青年二之一),覺其立論精美絕倫。其論道德尤屬顛撲不破之論。”(1917.1.25)
錢玄同向來狂放孤傲,很少如此佩服別人,這能看出陳獨秀當年的誘力。我有時翻看五四前后文人的日記、尺牘,深味那一代人的氣象。其卓絕之態為先前所罕有。自然,沒有陳獨秀創辦的《新青年》雜志,新文化運動也許還要推遲許久也未可知。在那些有趣的人中,陳獨秀扮演的角色,是別人不能代替的。
1917年的陳獨秀正血氣方剛,事業上正如日中天,成了中國耀眼的明星。他到北大,是北京醫專校長湯爾和以及在北大任教的沈尹默所薦。湯爾和與沈尹默頗為賞識陳獨秀的才華,以為欲振興北大,非陳獨秀這樣的智者不可。蔡元培信以為然,便很快將陳氏召來。陳獨秀來京后,頗感同人甚少,覺得需有新人加入進來,遂向蔡元培力薦胡適,以此擴大人馬。那一年元月他致信遠在美國的胡適。透露了心曲:
“蔡孑民先生已接北京總長之任,為約弟為文科學長,北薦兄下以代。……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