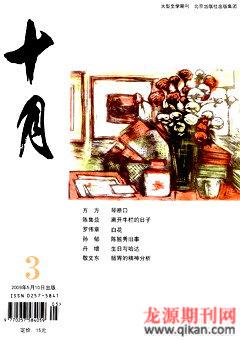穿過夜的帷幕
2009-05-13 08:09:56楊帆
十月
2009年3期
關鍵詞:小說
楊 帆
“猶如誤上了一節晚點的火車,廊燈昏黃,窗口漆黑,來路被搖晃著模糊了本來面目,而前程正被一格子一格子碾碎。丟在黑涼的風中。在所有事物中,只有這個人是色澤鮮明,情緒亢奮的,也許因為鮮明才愈發孤獨,因為亢奮才有了痛苦。在火車巨大的歡唱中她正竭力保持著心底的安靜。”
這段發表在《星火》上的文字是我在那些深夜寫作時的一個剪影。奇妙的夜行。滾燙的激情,烏黑的眼圈。我有些抑郁的心情由此而更加抑郁,抑郁得接近甜蜜。
去年父親去世了,留給我整整一面墻的書和無數黑夜。書桌上臺燈還亮,唯不見父親身影。每當寫出一篇小說,我的下一個動作就是捧給父親。他總是坐在這桌前,邊喝茶邊讀它們。除第一篇外,其他的都得不到他的贊許。由此我得出結論,我再也寫不出比第一篇更好的小說。
呆在書的蠟黃的含有灰塵的氣息里,我看到年幼的自己,站在父親身后的門邊,怯怯仰望燈影里的他。燈光下,伏案寫作的父親因為咳嗽而益發嶙峋的背影,他的長頭發,以及他那根不時敲落在我和弟弟腦袋上的筆桿,是我童年里的一道難以解答的算術題。父親是農民的兒子,身體里流著泥土般固執的血液,做派卻很有點魏晉遺風,畫畫,寫字,寫劇本,自導自演樣板戲,喝酒,娶廠花為妻。買肉的錢用來買書,常年瘦削得像一頭狼。相對于他的勤奮,父親運氣不算特別好。20世紀80年代初,他的兩個劇本分別被湖北電視臺和《萌芽》看中,后都不了了之。……
登錄APP查看全文
猜你喜歡
紅豆(2022年9期)2022-11-04 03:14:42
紅豆(2022年9期)2022-11-04 03:14:40
紅豆(2022年3期)2022-06-28 07:03:42
英語文摘(2021年2期)2021-07-22 07:57:06
文苑(2020年11期)2020-11-19 11:45:11
意林·全彩Color(2019年9期)2019-10-17 02:25:50
作品(2017年4期)2017-05-17 01:14:32
中學語文(2015年18期)2015-03-01 03:51:29
西南學林(2014年0期)2014-11-12 13:09:28
小說月刊(2014年8期)2014-04-19 02:3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