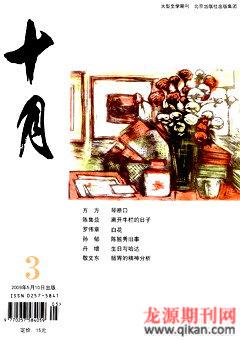白花
2009-05-13 08:09:56羅偉章
十月
2009年3期
羅偉章
整個冬天沒下過雪,可在冬春之交的時候,鳳凰山上卻落滿白花。那天清早,空氣干冷而透明,我站在清溪河北岸的廠房門口,朝南岸的鳳凰山望。天地間什么也不剩了,只剩下觸目驚心的白。我想那要是雪花就好了,如果是雪花,我會等天色再亮一些,領著妹妹,從晃晃悠悠的吊橋越過河流,去把雪花收集在干凈的玻璃瓶里,帶回家給母親熬藥。我母親半年前得了一種怪病,鎮上一個老中醫說,用新鮮的雪花熬當歸,喝上十天半月,病自然見好。然而雪一直不下,母親的病也就一直長在她的身體里,吸她的血氣,讓她一天天枯萎。
那片白要是雪花就好了!
可我知道那不是雪花,而是普光鎮洗選廠的幾百號職工遺下的白瓷盆。
我父親就在這家廠里上班。昨天晚上,他一夜沒回家,母親讓我來看看。
廠房門沒開。等了好長時間還是不開。
我大聲喊父親。
綠銹斑駁的鐵門把我的聲音堵在外面。
我又喊父親的名字王建吉。
寒風吹來,把王建吉三個字帶走,在遠遠的地方隨手丟棄,像這三個字很不值錢。
王建吉是鍋爐工,既燒開水,也燒洗澡水。他的上班時間分成兩截兒,凌晨五點到上午九點,下午三點到晚上七點。話雖如此,上午九點到下午三點的這段時間,他也有忙不完的活,他要負責把開水送到各個辦公室門前的木桶里,負責把平板車拉來的煤鏟成堆,之后又在鍋爐房周圍轉悠,清掃掉任何一絲入眼的垃圾;實在沒什么可清掃的,就用鐵锨在煤堆上拍。……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