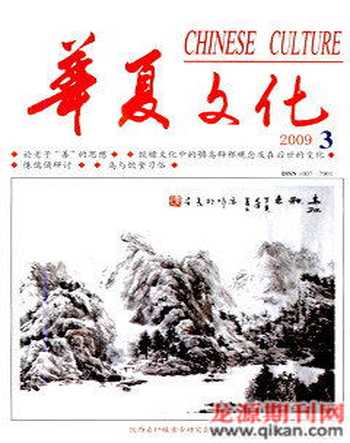韓愈性情論及其現代啟示探析
侯步云
韓愈(768—824年),字退之,鄧州南陽(今河南南陽)人,唐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學家,性情論是其儒學思想的重要一環。
一、性情論的理論前提
性情論的理論依據是儒家之道,性情論是儒家仁義之道在人性上的落實。《原道》:“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于外之謂德。”“仁”的內涵為博愛,“義”是一定情境下的行為準則,“道”為實踐仁義的動態過程,“德”又為行道的切身所得。“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之言也,天下之公畝也。”儒家之道為仁義之道,道統是對儒家之道的歷史傳承,體現了“道”的連續性。
“公言”是社會共同體普遍的價值規范,代表了群體利益。“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私言”與個體主觀價值相連。在儒家“仁”“義”面前,老子之道德概念的仁義是“小仁義”,表現為“彼以煦煦為仁,孑孑為義”,其本質為私。可見,儒家仁義之道有整體性、規范性的特點。韓愈所解讀的儒家之道,多是綱領性的操作程式。
性情論是順應現實要求的產物。佛教在韓愈所處時代達到鼎盛,尤其是在本體論、心性論等方面。這一時期“中心議題已轉向心性論,只有在心性方面取得發言權,才可以在哲學上有地位”。在這一歷史境域中,韓愈注意到佛教的治心,并以《禮記·大學》的修齊治平與之對抗,“傳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誠意者。將以有為也。”即儒家的心性修養是在現實倫理關系中完成道德生命,這是涵養心性的一般模式。佛教“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試圖取消人在社會生活中的各種角色而達到修身養性。這種以滅情見性而治心的方式,造成“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的社會局面,勢必有礙國家整體的有序運轉。
二、性情論的歷史性建構
韓愈性情論是對前人人性論的歷史總結與進一步發展,由兩大部分組成:一為理想之性情,一為現實之性情。
(一)理想之性情,包括性、情的基本界定、涵蓋內容以及實質意義。道由仁義至,仁義的踐行最終落在人性上。《原性》:“性也者,與生俱生也。”“與生俱生”語言形式近于告子所謂“生之謂性”,即指所有生命個體的自然屬性,取消人本身的特性,因此性無善無惡。荀子說:“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就人而言,“性”為“不可學不可事”,指明了人的一部分特性,但否定了人自我完善的可能性。韓愈雖取前人模式,但并沒有得出人性非善的結論。“其所以為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此五種德性是儒家仁義之道在人性上的突顯。“性”所包含的德性內容直接源于孟子的性善論,孟子論人之為人的特性,人皆有側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擴充為仁義禮智之善端。韓愈承接孟子性善理論,雖然這種承接的表層解讀多于實質性的把握。
實際上,“與生俱生”之性可以是抽象之性依生命有機體的外化,也可以是具體之性的直接表現。從韓愈對儒家之道的重新解釋以及基于現實批判佛老的需要而對孟子理論的部分吸收來看,韓愈對“性”的認識偏于后者,對“性”的內容概括合乎人性的要求,但這種認識缺少源頭處的追問與深度思考。宋人評論韓愈對“性”的五種道德規范論斷是:“想只是才高,偶然見得如此。及至說到精微處,又卻差了。”
何謂“情”?《原性》:“情也者,接于物而生也。”“其所以為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同生而具有之性為個體靜態表達不一樣,與物相接之情為個體的動態反應。“情”概念界定直接源于漢代劉向,“情接于物而然者也,出形于外”,“形外則謂之陽”肯定情的外向展開,但與天地陰陽簡單比附。情的七種表現近于荀子:“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荀子因性而講情的多樣化特征。韓愈在前人的基礎上,舍情釣陰陽比附,取情的合理性內容,直接就物言情。從“物”的最廣泛意義分析,韓愈講情是要求生命個體徑直參與“物”,如政治制度、倫理秩序等現實性、公眾性的物質或精神。
在邏輯上,“情”的理論發展與“性”的進展密不可分,并將進一步呈現形而上的性情一體。而實際歷史境況和個人自身條件使韓愈更關注現實的理論斗爭。宋人評價韓愈“離性以為情,而合才以為性,其論終莫能通”。這并非沒有道理。由上可知,韓愈對性、情的理解雖然在形上建設不足,但在指導方向上不離儒家之道,也適應了當時社會的要求。理性之性情即為本質上為善、功能上導人向善之性情。
(二)現實之性情。理性之性情是普遍的共存狀態,落實到具體個體,則有現實之性情的差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種,上品者于性之五德“主于一而行于四”為善,中品者“一不少焉,則少反焉,其于四也混”,故“可導而上下”,下品者“反于一而悖于四”為惡。
可具體概括為:
第一,“性”三分在漢代董仲舒“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中已見端倪。王充則以“可推移”的中人為標準,明確提出“中人以上”、“中人”、“中人以下”三等。韓愈拋開“中人”標尺,作上、中、下三分。
第二,三分的標準是五德,即現實個體對五德的或有效(如上品之人)或無效(如下品之人)或處中(如中品之人)的行為狀態。“一”為仁德,“四”為其他四種操作規范,但“一”與“四”的內在關系不明確。
第三,三品直接與善、惡、中發生聯系,其中“中品”可導而善惡,可理解為中品之人具備或善或惡的因素,外在的善意引導(如政策、法規等)不容忽視,但重要的是個體內在自覺向善,向善的途徑主要為個體的主動行為,從師學習,在道德實踐中責己寬人(《師說》、《原人》)。
韓愈立足現實社會,就個體彰顯性情的差異、表現個體的特性,理論上繼承前人而有所發揮,實踐中對抗佛教的“滅情”說。宋人從形上理論建設角度認為:韓愈“性分三品,正是氣質之性”,“退之所論卻缺少了一‘氣字”。
理想之善的性情指導現實三分之性情。為道德修養的可塑性提供理論保證;現實之性情是理想之善的性情在個體的具體呈現,驗證人在社會生活中的非同一性。
三、評價與反思
性情論,理論上分為理想之性情與現實之性情,運用到實踐中則有益于社會的有序發展,其意義在于:
第一,性情論在韓愈整個儒學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韓愈倡言儒家仁義之道,其在人性論上的表現即為性情論。先秦儒學為“人學”,在人性論上有德性論與氣性論的早期劃分。韓愈在文化重建過程中,復興先秦德性論,并以此為批判工具,與佛教滅情見性理論相抗衡。
第二,性情論對后世的影響作用。韓愈性情論雖然缺乏形而上的理論建構,但卻為后人在人性論上的新突破提供了致思方向。韓愈弟子李翱《復性書》認為“性無不善”,同時主張“情有善有惡”,以“性靜情動”“性清情渾”的鮮明對比得出性善情惡。宋人在性情三品的基礎上進一步主張天命之性善,氣質之性有善惡不同。
韓愈性情論既承繼前人,又有所發揮。在面對傳統與創新問題時韓愈的理論創建值得我們深思:
首先,韓愈性情論是在前人理論基礎上所做出的進展,但這種進展形式的描摹大于精神實質的把握;對傳統人性論的批判(孟子、荀子、揚雄言性“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流于氣盛而理不足,并不是在理解、體悟前人整個學術思想體系的基礎上進行反駁,現實的需要戰勝了新理論的建設。所以,對待傳統文化,既要有整體思維的審視,又要與社會實踐相結合,實現二者的動態平衡。
其次,唐時期,儒、釋、道三家并立,韓愈高揚儒家大旗,人性論上以理想之性情、現實之性情的劃分抵制佛老“無情”。應該說,人性的正面倡導有利于社會穩定,韓愈功不可沒,但面對佛老精深的本體論、心性說等理論,韓愈制度性、倫理性的性情論規模頗顯微渺,言論氣盛而理虛。所以,對待“新鮮”文化,既要人其里,又要出其外,“入其里”即吸收他者文化有益的理論給養,“出其外”即要在自身文化的基礎上,進行更深層的理論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