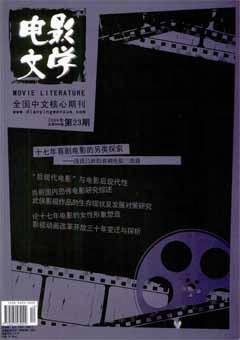《生死朗讀》的文學隱喻探究
杜云云 徐曉艷
電影《生死朗讀》改編自德國作家本哈德·施林克的同名小說。原著不僅獲得了多項文學獎項,而且其譯作還暢銷25個國度,是德國當代最為走紅的小說之一,也是第一本登上《紐約時報》排行榜冠軍的德語書。電影以獨特新異的視角關注二戰納粹政權下普通人的遭遇和命運,影片由男主角邁克·伯格作為旁白講述了發生在他與年長其21歲的漢娜·施密茨之間的故事。在愛情與歷史罪責的糾結中,深度發問善與惡、罪與罰、道德與法律、良心與責任、人性與存在之間的糾葛,使讀者在沉浸于人物故事的同時,經歷不間斷的、嚴密的內心質詢和對主流觀念的拷問。認知隱喻理論認為,隱喻不僅是一種語言現象。還是認知現象,它是一種思維方式,是理解抽象概念最重要的手段。為了便于表達和理解文學作品的深層含義,人們經常將其隱喻化。文學隱喻也是概念性的,它是作者進行人物塑造的認知工具,作者對小說人物的塑造和描寫是基于其創造的文學隱喻進行的。如法國影評人安德烈·巴贊在《電影是什么》中所言,“……通過隱喻或聯想來提示概念,就像插入了一個附加物、一個美學的變壓器。含義不在影像之中,而是猶如影像的投影,借助蒙太奇射人觀眾的意識。”《生死朗讀》影片中大量運用了文學隱喻的手法來塑造角色,通過對這些文學隱喻的探究可以挖掘出豐富的文學象征手段和意象,更好地解讀影片。
一、情感隱喻
影片的開場首先呈現的是男女主人公的情愛素描:由最初單純的性交流,慢慢發展并升華為朦朧的愛情。對這段只持續了一個夏天的愛情,影片卻用了近一半的畫卷和影像來渲染。而男主人公邁克也用了將近一生來回味;這是一段穿越了年齡和文化階層等世俗偏見的愛情,但卻無法穿越二戰中對猶太人屠殺的夢魘。
1情感隱喻
影片中15歲的邁克與年長其2l歲的漢娜的夾雜著愛情和歷史罪責的感情隱喻了德國戰后成長起來的第二代青年對待父輩在第三帝國時期的所作所為的復雜情感。如果說,漢娜是二戰中參與戰爭和屠殺的德國普通公民的代表,那么邁克則是這些人的子女的代表。戰后成長起來的年青一代德國人,沒有親身參與罪行,但卻成為一個罪行累累的民族中的一員。一個人當然會愛生養自己的民族和父母,但這個他們所深愛的民族和他們的父母卻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他們為此不得不背負起父母犯罪的十字架,這影響了他們的成長、生活乃至一生的幸福。因此,對于德國戰后的第二代青年人而言“他們的成年史也許就是他們與納粹的暖昧史”(詹春花,2007)。
2裸體的隱喻
影片前半部分采取了自然主義風格來展現男女主人公的性愛鏡頭,沒有特別去渲染任何情緒或者氣氛,更沒有刻意風格化,只是“真實”地記錄了當時情境下的赤裸的身體,用身體敘事,演繹了影片展現故事的非凡魅力。赤裸的身體在影片中是作為一個巨大的隱喻象征體出現的,是承載和貫穿這個性愛故事主軸的核心道具,是邁克“裸聲”朗讀的主體。影片之初邁克與漢娜的性愛是沒有語言描述和鋪墊的,他們的交流完全是通過身體,身體就是他們的語言;漢娜在集中營的工作也是沒有自覺的思維意識的盲從,她并沒有因法庭的審判和終身監禁而喪失生存的勇氣,讓她生命之舟傾覆的,是代表著愛與性的“身體(手)”的遠離。影片中漢娜作為一個文盲,用身體對抗思想,用身體言語,用身體思維。身體赤裸只是電影的一個牽引,深刻地表達赤裸的內心才是電影的真正內涵。
3水的隱喻
淋浴是漢娜和邁克做愛的前奏曲之一(另一前奏曲是朗讀)。每次漢娜和邁克在做愛之前,他們都會用水潔凈自己的身體。水的功能是清洗,洗凈污垢,洗掉不潔。基督教的洗禮儀式象征人的罪惡可以被“洗”掉,通過水的洗滌可以減輕心里對于“不潔”的負罪感。對于漢娜而言,水表達了洗刷罪責的潛在愿望;對于邁克而言,和漢娜一起沐浴既是他的“成年儀式”,同時也暗示他作為第二代人必須承擔的歷史責任(馮亞琳,2002)。
圣經中說“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馬可福音16:16)但猶太女作家并沒有原諒漢娜過去的罪行,漢娜通過水的洗禮進行的只是自我心理的救贖。
二、角色隱喻
影片的第二部分呈現了男女主人公的角色關系的轉變:從水乳交融的情欲關系,轉而變成法庭上的被審判者和聽審判的學法的大學生之間似乎是水火不容的關系。
1邁克的角色
邁克多次為漢娜讀到“告訴我,繆斯,那位聰穎敏銳的凡人的經歷,在攻破神圣的特洛伊城堡后,浪跡四方。”這段話節選自《奧德賽》,即古代希臘盲詩人荷馬所編輯整理的著名史詩,講述的是希臘英雄奧德修斯在特洛伊戰爭中取勝以及返航途中的歷險故事,英雄奧德修斯因為激怒了海王波塞冬導致他找不到回家的航線而在大海里漂流。
《奧德賽》隱喻了邁克漂泊的心路歷程,經歷了性與愛、道德與法律洗滌的邁克在面對漢娜的罪責時徘徊矛盾的心靈旅程。是應詛咒她的過錯,使自己陷入一生都無法擺脫的感情泥潭,還是應理解她作為文盲的罪過;是應將漢娜文盲的事實公之于眾,以減輕她的處罰并駁斥共犯的指控,還是尊重漢娜的抉擇維護她那可憐的自尊。邁克在善與惡、道德與法律、人性與存在中徘徊著,在復雜情感糾結中備受煎熬。即便是父親的葬禮也無法使他趕回去正視那個充滿兩人情感回憶的城市。他向所有人隱瞞這段情感經歷,直到漢娜自殺后才向猶太人女作家瑪瑟公開漢娜文盲的事實,希望能為漢娜減輕在受害幸存者心中的罪責。而直到漢娜自殺多年以后,他才解開心結向女兒坦率說出了自己和漢娜那段不為人知的故事,釋放了這個隱藏多年的秘密,釋放了那段糾葛,也釋放了對自我的執拗和對逝者的哀怨。在奧德賽經歷的所有困境當中,最大、最危險的莫過于忘憂果之鄉(洛托法根人的海岸):在那里,路人若吃了忘憂果就會樂不思鄉。因此,像奧德修斯一樣,抵制遺忘是邁克面臨的最大挑戰。同樣如奧德修斯一樣,把自己的故事講述出來才是抵制遺忘的最好辦法。而這一點,恰恰是戰后德國一批有良知的作家所做的,也是邁克講述自己故事的初衷(馮亞琳,2002)。同時邁克向女兒解開心結的原因之一是相信自己能夠被女兒所理解,也就是重新拾起了對于人性的信仰。
2漢娜的角色
“牢騷,凈是些牢騷,看在上帝的份兒上,除了工作就什么也不剩嗎……。”節選自德國啟蒙運動時期的代表人之一萊辛的劇本《艾米莉雅·迦洛蒂》。這段話隱喻了漢娜到集中營的心理:集中營只是自己隱藏文盲身份而謀生的一份工作。漢娜并非主觀意識上想要當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而是因為一份無需認字的工作而無意間充當了納粹機器的工具,不自覺地參與到罪惡當中。漢娜是特定的歷史時代的受害者,對政治和現實既沒有判斷力也不感興趣,在責任與良心的矛盾中,選擇了庸人的工作帶來的所謂責任感。如果她不執行納粹的命令,那些可憐的猶太人就可以免去一死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如美國人類學之父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