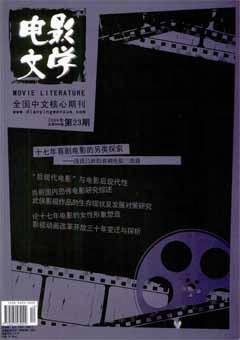淺析電影中的精神病敘事
何李新
[摘要]關于精神病的影像敘事與其說是精神病現象的客觀再現,毋庸說是對其含混身份的一次意識形態整編。電影或將精神病想象為難以馴服的“他者”的化身,在獵奇的注視中完成娛樂消費;或把精神病視為文明的毒瘤,通過欲望的妄想指涉當代社會精神分裂的個體;或從邊緣的處境開掘精神病所具有的價值批判意義,最終展示了當代意識形態中的主體生成之路。它是一種對社會的徹底拒絕。
[關鍵詞]獵奇的景觀;文明的毒瘤;邊緣的抵抗
當心理學、醫學將精神病限于病理范疇之內時,弗洛伊德所開創的精神分析學卻將精神病視為一種社會壓抑的癥候。作為現代社會自身除不盡的余數,它是快感的源泉,也是恐怖的化身。因此關于精神病的影像敘事與其說是精神病現象的客觀再現,毋庸說是對其含混身份的一次意識形態整編。
當代電影中的精神病元素不一而足,本文試圖歸納出三種典型的敘事類型。
一、獵奇的景觀
自19世紀末電影誕生以來,各種病態行為就成為人們獵奇的對象。《一條安達魯狗》(1928)中剃刀劃過眼球的影像曾刺激無數人的神經。在當代商業媒介的催化下,精神病人種種不容于世的生存方式更發酵成一部部驚世駭俗的影片。精神病在銀幕上的大量出場折射出電影的最初訴求——獵奇。在此,精神病成為一種單純被看的景觀。他們固然也可以作為故事中無力的弱勢群體而引起觀眾的同情,但本文更關注其主動訴求行為在影片中所產生的驚悚結果。
在當代多數商業電影中,精神病往往以血腥、殘暴的行為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中。較典型的有《德州電鋸殺人狂》系列和《驚聲尖叫》系列。其基本的敘事模式是圍繞一個幕后幽靈般的人物展開。他們通過一系列暴力行為不斷制造恐慌與懸念,并在最后被揭示為精神病加以消滅。這里很少有對精神病的成因探詢或社會申訴,而僅僅將之視為一種變異的入侵者。他們是一種突然闖入日常平靜生活的他者,其行為懸置了現實的邏輯,而呈現出一派赤裸裸的瘋狂。
這種恐怖片、驚悚片中精神病形象的類型化,通常源于制片方與觀眾的意識形態合謀。就制片方而言,精神病不過是暴力行為的有效借口,以求得更多恐怖奇觀來給予觀眾最大刺激,從而獲得更高的投資回報。就觀眾而言,精神病最直接地保證了敘事的完整性。他們是一切殘暴行為的最初禍根以及最終解決。在一驚一嚇的觀影過程中,觀眾獲得超出日常平庸的恐懼、希望、期待等高峰體驗。當人們走出電影院后,一切又恢復正常。精神病影像在這里僅僅是娛樂消費的廉價催化劑。
同時我們也不能忽視這種妖魔化的精神病影像所具有的真實意義。拉康對著名的“燒著的孩子”的夢的分析給予我們重要啟示。與通常解釋父親為了逃避兒子死去的現實而遁人夢境相反,拉康認為父親恰恰是在夢中遭遇了自身欲望的實在界——對兒子死去事實的無能為力,并從夢中醒來逃回到現實。觀影的結束表面上意味著經過一場影夢而回到現實。背后更重要的意義在于從與欲望實在界的遭遇中避回到熟悉安全的日常世界。因此對個體心理來說,真實的恰恰是這種在影像中遭遇的欲望實在界。
作為獵奇景觀的精神病,此時癥候性地折射出創作者和接受者的欲望實在界——對難以捉摸的他者的恐懼。由此我們不難理解飽受驚嚇的人們對此類恐怖、驚悚片依然甘之如飴。因為真正令人恐懼的并非是精神病的血腥殘忍,而是無以名之的他者。當這種威脅性的他者揭開非人的面具,而作為一個精神病被定名的時候,恐怖被消除了。他者的實體化使其最終可以被消除。但悖論的是,他者又在不斷抗拒這種社會的馴化。正如影片中的精神病殺手并不會完全消失,他們將會繼續尋找下一個獵物,引發新的恐怖事件。
在排斥與馴化的邏輯中,精神病被建構為一個必不可少的他者,使我們獲得一種生存的安全感,哪怕只是暫時。
二、文明的毒瘤
如果說作為他者的精神病只是電影單純的獵奇產物,那么當代電影中更典型的精神病則行走在大眾社會中。諸如《本能》(1992)中的凱瑟琳·特拉梅爾,《美國精神病人》(2000)中的帕特里克·貝特曼,《沉默的羔羊》(1991)中的漢尼拔·萊克特博士。他們不約而同具有精神分裂的癥狀。外表優雅美麗,思維超然于世,但內心卻潛藏著噬血的沖動,在殺戮中實現自我意志。這種精神病其實是后工業社會的典型產物。我們不能簡單地將之歸于殘忍的獸性。文明的過度進化導致人們的精神扭曲,在物欲橫流中個體內心卻極度空虛。他們的瘋狂是運用最嚴格邏輯的理智產物。這類精神病不是源于本能的殺戮快感,而是對于無法完滿的欲望的妄想。
用拉康的話來說,“匱乏之匱乏就是一種精神病的特征”。這并非具體物質的匱乏,而恰恰是觸發了符號化過程的距離之匱乏,是一種空位匱乏。不同于常識上的現實觀,支撐我們社會正常運轉的其實是一套符號象征秩序,即世界——語言的關系。它僅僅通過與現實保持一種最小距離來發揮作用。這種距離暗示了作為欲望原因對象的對象a是一種無法獲得的根本性的缺失。“對象a恰恰代表了不可能的對象,它使永遠不能成為一個實際對象的東西具體化。”但恰恰也是它啟動了欲望能指的循環。
但在當代景觀社會中,想象性表象的蔓生給這種象征虛構留下的空間越來越少。當虛空被填滿時,把對象a同現實分離開來的距離也將喪失——對象a直接注入現實。這種過分親近最終會窒息象征虛構的活力,引起現實自身的非現實化。現實不再被象征秩序所結構,幻想直接控制了現實。個體面臨被虛無化的危險。
正是面對這種僵局,精神病以暴力的行為出場了。其行為可以被視為一種絕望的企圖,即主體通過暴力從現實中驅逐對象a,并因此獲得進駐現實的通道。這里的對象a作為欲望對象原因是永遠不可能被現實化的,例如烏托邦、信仰、理想、愛情等。一旦現實化為某物,它就不再是對象a,只有保持與對象a的距離,我們才可能在現實世界中繼續生活下去。
所以當代社會的癥狀在于,我們不是缺乏物質,而是缺乏空無。凱瑟琳·特拉梅爾、帕特里克·貝特曼和漢尼拔·萊克特博士,雖然都具有超乎常人的美貌、智慧、財富,卻淪為可怕的精神病者。他們缺少的不是具體的欲望客體,而是欲望本身。雖然一次次在瘋狂暴力行為中體驗欲望,卻又一次次失望。在殺戮中,他們驅趕欲望對象,得到的永遠都不是真正想要的,從而陷入新一輪的精神病發作。這樣的循環導致了人格的分裂。在美麗光鮮的表皮下是病態的暴力行為的間歇性發作。通過殺掉具體的人,而證明對象a不在現實中,從而保持對于對象a的欲望,進而獲得一種堅固的存在感。用德勒茲的話來說,精神分裂是一種將撕裂的自我拼合起來的語言運動。
這類精神病是文明無法割除的毒瘤,象征著社會進步對人自身的反噬。我們可以消化作為他者的精神病,卻無法否認自身也會有相同的暴力與妄想。
三、邊緣的抵抗
還有一種精神病既不是外在的他者,也不是內在的毒瘤,而是身處邊緣的抵抗。我們很難將他們定義為一種病理性的精神病。哪怕舉止怪癖癲狂,更多時候他們的思維行為與常人無異,只是無法納入主流價值的接受范圍內。福柯說瘋癲不過是被人們不斷界定的文明產物。從某種程度上來說,精神病恰恰是一種對病態社會現實的自然反應。他們更像是這個社會的正常人。
從東西方兩部刻畫精神病人的影片中,我們可以一窺對現實主流的無形顛覆。巖井俊二的《夢旅人》(1996)和米洛斯·福爾曼的《飛躍瘋人院》(1975),兩者敘事都建立在精神病院與精神病患者的對立邏輯之上。在視、聽語言的刻意處理下,那些所謂正常的醫生、護士顯得陰森可恐。他們作為病人的看護者實際上體現了主流對邊緣的監禁。相反,不論是《夢旅人》中的精神病人卷毛、可可和小悟,還是《飛躍瘋人院》中的麥克·墨菲,都原為正常。
前者秉有純真浪漫。燦爛的陽光下,三個人行走在高高的圍墻上。這里既不屬于精神病院也不屬于外面更大的社會,而僅僅是三個天真小孩的世界。正因為這份邊緣的脆弱,我們才能體會小悟摔下高墻的恐懼,才能遭遇可可為拯救卷毛而開槍自殺的震撼。在生命的破碎中見證了現實的殘酷齷齪。與他們的柔弱不同,《飛躍瘋人院》中的麥克更加具有攻擊性。他教病友們用香煙賭博,逃出瘋人院和女友幽會并把女人和酒帶進醫院禁地。這一切違反醫院秩序的行為在他蔑視的笑聲中化為對權威的挑釁。他更像是一個以頭撞墻的斗士。悖論的是,他被社會收編的方式是最后被徹底電成白癡。只有如此,邊緣才被主流納入自己的意義系統內。
這類精神病敘事形成了一塊意識形態的抵抗飛地。在高墻上或醫院外,他們能夠重獲自由。問題在于這種想象另一個世界的行為本身恰恰是意識形態的。對秩序的僭越早已包含于秩序的范圍內,并進一步鞏固其統治的合法性。所以精神病抵抗的更激進行為其實是完全甚至過分地認同主流。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導演謝晉的作品《芙蓉鎮》(1986)結尾的瘋子王秋赦具有更大的顛覆意義,他在片尾打著鑼,叫嚷著:“運動了,運動了。”這種對意識形態國家機器過分認同的姿態恰恰暴露其邏輯的荒謬。
同時就觀眾而言,在對英雄式的抵抗行為的注視中潛藏著欲望的分裂。觀眾與電影是一種凝視的關系,而凝視是欲望的投射,在想象中獲得欲望的滿足。但凝視本身所印證的只能是欲望對象的缺席。因此對抵抗的注視并不能帶來一種真正的抵抗行為。當注目于此類精神病人對社會的顛覆并為之歡呼時,我們正經歷自身凝視的無力。反抗永遠是充滿激情、快感的,但是結局卻是毀滅、死亡或者更深的壓抑。我們可以體驗那種快感,但將失去社會存身之地。所以邊緣與主流的對抗中,我們已不再是遵循啟蒙的現代模式做一個以鮮血反抗壓迫的斗士,更多的是犬儒主義地蜷縮于影像中,借由邊緣的英雄個舉而生活在他處。
四、結語
以上論述涉及基于不同立場對精神病的敘事處理。或將精神病想象為難以馴服的他者的化身,在獵奇的注視中完成娛樂消費;或把精神病視為文明的毒瘤。通過欲望的妄想指涉當代社會精神分裂的主體;或從邊緣的處境開掘精神病所具有的價值批判意義。凡此種種無疑揭示了“瘋狂”在當代思想文化中的核心地位。杰姆遜指出,“當代理論對中產階級價值觀進行批判的同時,暗暗她有一個自己崇拜的英雄——瘋人。”因此電影中的精神病敘事最終展示了當代意識形態中的主體生成之路,它是一種對社會的徹底拒絕。